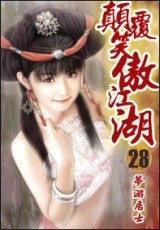酒色江湖-第12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楚濯漓的手腕抬了起来,信号飞舞在天边,是绿色的。
树影摇曳,暗器破空,间或夹杂着人声的闷哼,黑夜中,他们看不清楚,只能靠声音去判断。
“这一轮,能抗住一炷香。”楚濯漓开口了,平静无波。
只能一炷香吗,又不知有多少无名的人,将倒在这一次的进攻中,单解衣叹息。
单凤翩将这么多无辜的人卷入斗争中,那些倒下的人,多少也曾是笑谈江湖风云,来去不留名的豪侠。
可单凤翩又有错吗?皇家的命令,他能违抗吗?
所有的一切,从楚濯霄选择与他对立的那刻起,就种下了因果,或许说从许风初死的那一天起,江湖就再没有了制衡的能力。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人的地方就有争斗,这是千古不变的定律,人命如蝼蚁草芥,不由自己。
一盏盏绿色的灯笼从树林间升起,在山腰中摇晃。
生命流逝的倒数,又一次开始。
一炷香,多么短的时间,如果可以再长一点,该多好。可是长下去,又能坚持多久?那不可能是终点。
人影渐近,可以看到一道道身影扑入树林中,寻找着隐藏在树影间的黑道高手们,兵刃的纠缠划入风中,是血肉围堵着信仰的坚持。
黑白不两立,暗潮一直都在;只因这一次,尽情发泄着所有的愤恨。
刀身入人体,能在力量间判断对方的结局,可是他们不能动,不能营救,不能扑出这山头,只能握紧拳头。
绿色的灯笼,慢慢少了,似被这秋夜冰冷吹灭了,黑暗又一次侵袭了大地山中,掩盖了所有逝去的人。
“漓,为什么不突围一条路,保存最大的实力。”单解衣为这种拼杀的牺牲而叹息,“军队的支援不可能太长,只要突围出数日,他们必然撤兵,那时黑白两道再争,胜负尚未定论。”
“你忘了我们是什么身份吗?”楚濯漓回首凝望她,那火把在他眼底跳跃,战斗的光芒一阵阵的闪烁,“我们是‘佘翎族’的后人。”
“你!”
单解衣恍然明白了什么,心头憋闷着。
“佘翎族”是皇家最讨厌的血脉,因为他们身上有着颠覆朝堂的传说,楚濯漓本就知道这是一场打不赢的战斗,他和楚濯霄要的,就是以一己之力拖住朝廷的军队。
因为北地军队的延误不归,单凤翩这一次调动朝廷兵马,京城防御早空,若此刻有义军揭竿而起,京城必定失防。
可是他们不知道……
局面已不容单解衣再想什么,再说什么,当绿色的灯笼全部熄灭之后,一盏盏红色的灯笼飘飘了起来,空气中飘起了古怪的烟雾。
“他们放毒,快上。”此刻,近的人声如此清晰,清晰到不仅能听到声音,还能看到飞掠在空中的人影,看到每一次刀锋扬起时反射着月光的冰冷。
“含解毒丹,以最快的速度上去,抓到首脑逼问解药。”
山腰间人群推进的速度更近了,单解衣甚至在其中看到了一些熟悉的容颜,在追寻“桃花琴”时,在武林大会时,那些人群中的面容。
昔日也算一面之缘,今日刀剑相向。
有人被陷阱绊住,转眼中树林中就是一片片的暗器飞出,射上身体。一个人倒下,引数个跟随在后的人扑入树林间,刹那间,红色的灯笼灭了一盏。
僵持,在临近山顶的地方;真正的厮杀拉锯,就在他们的眼前。
单解衣眼前的黑道豪杰们,不再是武林单打独斗各使招数,他们面前竖着偌大的盾,为山头铸造起最后一道铁壁铜墙。
没有了擅长的武器,这种防守能够□几时?只有防守,没有进攻的下场又是什么,山头上的人更清楚。
刀剑砍在厚重的盾上,火星四溅。身体抵住盾牌,身后的人扬起手中的粉末,散开在空中。
进攻,第一次遇到了阻碍,但也紧紧是延缓了对方上山的速度。
大汉再也忍不住,在一人倒下的瞬间,大声怒吼,掠入林中;接住同伴身体的同时,硬生生扛住了那厚重的盾牌,掌心力道飞出,将来者击飞。
风吹开云层,月光照在大地。
血色飞舞,在这场战斗中,没有武功高低,只有血性。
僵持,也只维持了三柱香的时间,中间的盾阵防守刹那被撕开一道防线,人影向两边倒去,红衣在月下翻飞,无可抵抗。
她的目光看着来者乘风而来,两人眼神在空中交汇。
俊美端庄的人,即便在出手取命间,依然是如此的完美,他纠缠着她的身影,朝着她的方向靠近,他的身后,是各门高手,在一番厮杀下,除却他几乎都是狼狈难看。
“单凤翩。”她耳边,听到了一阵轻笑,是看到了希望的笑。
楚濯漓的手扬起,一道火光冲天而起,在天空中炸开,黄色的信号飘荡在头顶上空。
山脚下,沉闷的响声一阵阵炸开,原本平坦的地面顿时崩裂无数,地面塌陷,深深的沟壑出现,山腰间山石滚落,将所有上山的道路封堵。
官兵,没有武林高手的身手,不能飞纵跳跃,他们要上山,只怕先要开山搬石。
这些被炸药引爆的石头,凌乱没有层次,只怕要费上几日功夫了。
楚濯霄扬起脸,“江湖事江湖了,黑白两道的事,注定是要自己解决的。”
单凤翩的人在空中,朗然声音悠扬空中,“即便没有后盾,如今的你,还能与我一战吗?”
是啊,山头这些黑道英雄,是否能与面前这众多白道高手抗衡?
人数上,已是劣势了。
楚濯霄虽能与单凤翩对峙,可楚濯漓的武功,绝没有到炉火纯青的地步,谁,还能与楚濯霄并肩,护卫他们的性命?
楚濯漓的手,牵上她的掌心,另外一只手按上她的肩头,“解衣,你给我的我还给你,你是否愿意?”
一句是否愿意,问的不仅仅是她是否狠得下心让他回到当初文弱的书生,更问的是,她是否愿意与单凤翩对阵,是否舍得下夫妻情分。
从战斗开始,她就一直冷静的看着,看着人群从山脚而上,看着一盏盏的灯光被灭,看着人倒下。
慢慢的抬起脸,她重重点了下头,“好。”
作者有话要说:今天我偷偷去打三国杀,结果看到了一个ID用着十二宫里某个男主的名字,于是很兴奋的扑上去打招呼,然后,然后……然后我就被T回来写字鸟,呜呜呜……
正文 传功(一)
山头,两方人马对峙着,明月冷清,压不住漫山杀气,柔不下血腥扑鼻。
她与单凤翩交缠着目光,与其说是叙旧,不如说是较量,心神上的较量,压制对方的气势勃然。
这么多年,她从未如此的面对他,她对他,是崇拜而敬畏的,这种心思从小到大,就连挚爱着他的时候,也不敢多问多言,被他压制的死死,就是这种心思在作祟。
现在的她,忘却了曾经的惧怕,更强烈的想要与他一战。
脚下,慢慢的后退,她的身后是楚濯漓温暖的怀抱,就在这暗战隐隐中,她与单凤翩的目光渐远,直到被别人的身影打断。
退入了厅中,楚濯漓扬手,红木的大门在袖风中阖上。
外面吵嚷声、争斗声、对战声,甚至连呼喊中的敌意,都能透过门缝飘进耳朵里,只能给两人暂时的独立空间。
“要看看传功的方式吗?”他苦笑着,手指从怀中掏出一个书卷,伸到她的面前,等待着。
她的表情也是同样,无奈中苦笑,“不用,其实我知道。”
“你知道?”就连一向平和的他,脸上也有了意外的神情,“我以为……”
“你以为单凤翩会瞒的死死的,什么也不让我知道。”她长长的透了口气,似要透尽心头的浊闷,“其实,他的确什么都没有告诉我,瞒我死死的。”
“但是他永远瞒不了一点,就是心法,一旦我看到了我需要使用的心法,以我十几年的练武判断,我还能不知道是什么方法吗?”
所以,她不必再看,当单凤翩当初以基础心法的口诀传授给她之后,如今想来已是心知肚明。
“他不告诉你,有他的道理。”楚濯漓轻叹,“在我看过这种心法后。”
“那是他一厢情愿。”她冷冷静静的声音说出内心的想法,“我不是孩童可以随便哄骗,只要我能看穿这心法是吸取功力的,永远都不可能做到他想象中的全部吸取,内心不愿,结局只能只功亏一篑。”
“那现在的你,又愿意吗?”一如既往的温柔,那恬淡的神情,仿佛小楼初见面的刹那,他带给她的震撼。
“不愿。”她的回答并没有让他更多的意外,“习惯了平静的生活,我更喜欢这种没有武功却逍遥的生活。”
这是她的心底话,这些日子,带给她的快乐,是以往沉重背负下不曾有的。她不需要再冷静权衡,不需要去压抑自己的情感,更不需要将所有心思隐藏。
“为了他,你又愿不愿呢?”一个他字,彼此都知说的是谁?
她下意识的举目看向门外,厚重的门阻挡了目光,阻挡不了她的心。
那个身影,就站在不远的地方,带着他的属下,不屈抵抗着对手。
“不仅为他,还有其他人。”她的这个回答没有指名谁,也没有让楚濯漓的表情更高兴,反之,那双眸的和暖间,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失落。
不论她口中的那个他人是谁,都不可能是他,她能如此笃定如此成竹在胸,也就意味着,自己在她心中永远都不曾拥有他想要的地位。
双臂,从身后环上她的腰身,温热的唇贴上她秀丽的颈项,声音呢喃在她的耳边,“那只好委屈你了,或者你觉得后院会比这里更好,如果你想去后院的话……”
“不用。”现在的她,更想呆在这里,即便看不到能够听到,也会让心灵有暂时的安慰。
但是在这里……
环顾四周,除了偌大的几案就是椅子,这个决定似乎有些过于大胆了。
她,依稀听到了他的轻笑声,暖暖的气息撩拨着她的发丝,暧昧十足,密闭的大厅里,两个人亲密贴合。
他的手指从身后抚摸着她的脸颊,看不到她的容颜,手指尖的触觉更加敏锐;她也看不到他的神情,只能从他手指尖的微颤中体会他的悸动,正也是因为看不到,身体的感觉才会如此清晰。
只有情人间,才会有这么亲昵的姿态。
只有爱人间,才会有这般耳鬓厮磨的缠绵。
只有倾心交予中,才会有这样的呢喃低诉,才会有这种郑重捧在手心的在意。
他们是情人吗?是爱人吗?是倾心交予的人吗?
无论她怎么看他,至少他是这么看她的,从与她第一次见面,看穿她心思替下落那枚棋子的时候;从她状似无心为他递上一盏热茶的时候;从她与他桃林下相谈,默默的为别人削着桃木簪的时候;那眼神中的柔情就这么无声无息的撞入了他的心底,从此难忘。
更忘不了,她为兄长付出的一切,那么轻描淡写的神态中,却是性命的交付,不求对方知道,哪怕对方只有恨。
这女子骨子里的坚决,让他油然而生的是怜惜。
敬她坚韧,怜她孤单。只有寂寞的人,才会习惯坚强,只有形单影只的人,才会如此渴望爱情而如此付出。
那时候的他,是笃定了主意要护她的;不把她交给单家,是因为他认为单凤翩若真的爱惜她,又怎会让她如此孤单。
他楚濯漓前半生,始终在隐忍中度过,不能动气不能起好胜心,面对万物永远都是云淡风轻。她,是他唯一一个想要真正留下,用尽所有哪怕负尽天下也要保护的人。
他曾想,若她就这么去了,他便身随相伴,他不忍这灵秀的女子最后一程,还是独身上路。
即便……她永远不知道他的心思。
这身武功,本就是她的,还给她是应该,更何况若是以这种方法传功,于他早已是满足。
他的手指,拉开她衣衫的系带,那紧束在腰间的衣带飘落,松散的衣裙更显她的纤细,腰身不盈一握。
掌心拢着她的腰,双手交扣,将她环在怀中,掌心的温暖一寸寸的上移,手心里微微的颤抖糅合着她的呼吸,都是不稳。
如今的他,早不复当年的孱弱,如今的她,也不是昔日的意气风发。
这样的姿势,更像是一种保护,将她全然保护在臂弯下的爱惜。
那手,停在她的胸口,无声的烙下他的印记,在她的呼吸间,让他的热度,侵入她的心跳里。
她的心跳,一下下,感受在心头是最美的律动。
第一次,如此真实的拥抱住他,让她存在于自己的掌心中,独属于他一个人的解衣。
“你最适合的,还是紫色,若是那颜色,只怕我都没有勇气脱下。”鹅黄色的裙装从肩头滑下,他的唇颤颤的吻上,当温暖与细腻相贴的刹那,她的肌肤轻窒了下。
紧绷,因为他。
很快,就舒展了,无声的接纳。
丝绸滑落,堆拥在他弯起的臂膀间,线条完美的肩膀下,她的肌肤散发着珍珠色泽,黑暗中晕开。
他感谢这没有烛光的夜色,可以让他仔细的端详她,没有武功的她,是无法捕捉他的目光看穿他心思的。
即便如此,他也只敢这么从身后拥着她,将身影永远的藏在她背后的地方。
薄薄的一层亵衣,是亲近,也是距离。
他的唇,一下下啄着她的颈项,那肌肤的细腻,永远也抚不够。
齿间,咬上细细的系带,轻微的动作间,那最后一层的距离就此消失,他的手,再没有任何阻挡。
这刹那的动作,哪有大战临头的危机感,哪有生死悬线的紧迫,有的只是他郑重的探索,轻柔缓慢。
她没有问他能不能全然投入,因为她从来都是信他的。
他也没问她能不能全然情形,因为他不敢问,怕答案伤人。
香案边的花瓶里,一朵白玫瑰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