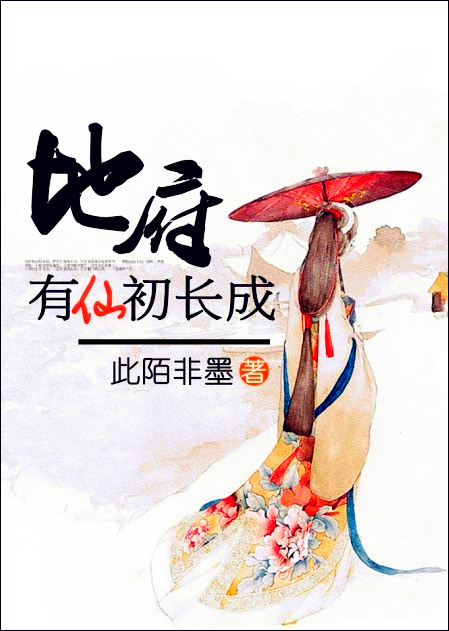迟迟钟鼓初长夜-第4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那日晚宴极为成功。菜色丰盛精致,席间灯笼摆放巧妙,分不出是月光还是烛光,明亮柔和,恰如桂花香气,令人醺然欲醉,又只是薄醉,不致失了赏心悦目的情致。米政连声赞叹,赵易微笑,情不自禁的看向红若。红若却低头谦道:“大人过奖了。我素闻悠州平阳景物极佳,一步一景,悠菜亦是天下一绝。大人连日奔波劳顿,我这家常菜才讨了巧去。”米政捻须微笑:“萧姑娘兰心慧质,单单这宴席摆设就非常人能布置出来,更不用说猜中老夫心事,每菜必合口味,就算在平阳,老夫也未必有此待遇。”红若一笑,皓腕轻抬敬酒:“饮食享乐这等小事怎会放在大人心中。这杯酒,就祝大人得展平生抱负。”米政仰头哈哈大笑,将杯中酒一饮而尽,显然这番话说得他极为满意。然而满意是满意,心中忧虑更甚。
此次到追风堡,他早已知道赵易与一女子纠缠之事,却再没想到这女子是萧红若。初见之下极为愕然,却只不动声色的任人介绍。那红若何其聪明,一举一动都顺着他的心意,当作两人从未认识。越是这样,米政倒越觉得心头不安。
“男子三妻四妾本是正常,何况易公子何等身份,必定不会只有明霜小姐一人。不过这红若美得不似凡人,所谓红颜祸水,就是此等女子。将来易公子专宠,置明霜小姐于何地?”再想到红若与赵靖旧年纠缠,愈发不悦。
这晚红若出场,大方清朗,在他眼中越觉此女心机深沉,想到她曾经处心积虑算计马原展现的那份狠劲与坚忍,放到平阳城中不知又要掀起多少风波。
他面上笑着,眼中精光一闪即逝,仍落入旁边萧南鹰眼中,心头咯噔一声。红若相貌太美,他原就担心,此刻也能把米政的心思猜个七七八八,眼瞧着红若进退有度大方雍容,萧南鹰脸色反而沉了下来。米政含笑瞥他一眼,他神情不变,眼神中却有隐约笑意。米政心头一宽,转过头去。
回到房中,红若睡不着,心下总觉得有些不对,有说不出哪里不对。却听到窗棂上喀喇一声轻响,她推开窗,见赵易懒洋洋的斜靠在树下,一双眼睛似笑非笑的望着自己,不由脸一红,低声道:“这么晚不睡?做飞贼么?”赵易立刻接口:“我这个飞贼专偷人的心。”红若顿足:“你现在可什么当真学的油腔滑调。”赵易低笑,手在窗台上一撑,跃进屋来,双臂只一合,就将红若纤细的身体拢在怀中,在她耳边低声道:“我舍不得你。”这五个字重重击在红若心中,她怔怔的把脸靠在赵易胸前,半晌才流下泪来。
一切条件已经谈妥,米政与萧南鹰约定十日之后上路。红若反而镇定,列了单子,叫下人细细准备一应用品,连赵易爱喝的茶都没忘记。她自己则整日在房中替赵易缝制衣服。“悠州在北方,冬天可不知要比这里冷上多少。”她低着头微笑,姿势婉转温柔,赵易自身后抱住她,将下巴放在她肩上:“你自己呢?再过三个月我就叫他们来接你,刚好是冬天,你身子又不好,要多缝些衣裳。”红若停下手中针线,出了片刻神,才轻轻笑道:“你走了之后我有的是时间,操这么多心做什么?”
赵易陪了她许久,见她屋里堆满了各式物品,心中有所感触,松开双手坐在一边,头枕在手臂上,看着窗外天际。红若侧头,见他神色中有少见的肃穆,不由柔声问:“怎么啦?”赵易微微一笑:“我堂堂一个大好男儿,竟好像要嫁到悠州去似的。”红若正色道:“你怎可如此想?你去找自己的叔叔,同亲人团聚,有什么不对?”赵易挑眉:“当今皇帝也是我的亲人,我怎不同他团聚?”
红若将手放在他肩上:“能屈能伸方是大丈夫本色,你莫要想太多。”赵易伸了个懒腰,长长的腿交叠起来,回头看着红若:“放心,你说的这些我都明白。我既做了这许多牺牲,自不会让无谓小节困扰于我。”红若见他说的笃定,心中反而惴惴,也不说话,只是用深黑的眸子定定的瞧住他。赵易将她揽到身边,在她发间一吻,千言万语,尽在不言之中。
赵易离开之前那夜,下了第一场秋雨。红若夜间受了风寒,竟未曾起身送行。待到中午时分仍未起床,躺在床上听雨滴有节奏的敲打树叶和窗台。迟迟悄无声息的进来,坐在床边,也不吭气。红若转头一笑:“我没事。”迟迟仍是沉默。红若纳罕:“我以为你是来劝说我的。”
迟迟方抬头:“你做什么事情都一定有你的理由。你既已经下定了决心,我就不再劝你。你若觉得值得,我只替你高兴,你若是伤心想反悔了,还是那句话,我替你杀到平阳去,任它龙潭虎穴我也把赵易给抢回来。”
红若听她清脆的声音里有种斩钉截铁的纯真,一时怔住,许久之后才发觉,颊边湿了一大片。迟迟伸手来擦,她反握住迟迟的手,将脸埋下,滚烫的泪灼在迟迟掌心。只听她低声断断续续的道:“我总觉得自己无怨无悔,可是到他走的这一刻,我才知道我很难受。我,我没有力气去面对他走的样子,我怕自己会不舍得放手。”迟迟心下大痛,俯身抱住她:“我知道,我都明白。”“他走的好么?”红若低声问。“很好。易哥哥走的时候,不苟言笑,同往日大不相同,喜怒都看不出来,已经,已经象个殿下的样子了。”红若听见这话,却又心酸:“他没见到我,难道不失望么?”迟迟低声哄道:“傻红若。他自然知道你为什么不去送他。他是男子,自当体谅于你,若是露在脸上,倒叫米大人看了去,小瞧了他,也对你不利。”
红若抬头:“还有三个月才能再见到他。”神色凄楚茫然,象个无助的孩子,再不是那个迟迟熟悉的红若。迟迟抚着她的头发,不敢多说。红若却镇定下来,自嘲的一笑:“也是,他新婚燕尔,一两个月就娶妾室,置悠王的面子于何地。”
想开了这一层,红若再不伤悲。在心里细细盘算了一番,也有了计较,人也安详起来,若无其事的行事,开始给自己添置冬装,又忙着刺绣。迟迟不解:“你素来不喜这些太过招摇的衣裳,又何必绣如此隆重的图样?”红若打量那湖蓝的裙幅,上面的百鸟已经绣了大半,栩栩如生,绣工之精细绝妙,连自己都不由赞叹。她的指尖抚过冰凉的缎面:“这个不是给我的。是给明霜小姐,不,赵夫人的。”她自己都没有料到,说出这个称谓,心头除了淡淡悲凉,并无不甘与痛心。迟迟却红了眼眶,立刻转过头去:“你何必。。。。。”“当然有必要。”红若截断她的话,嘴角挂着若有若无的笑意,“她与我,尊卑已定,身份悬殊。我若以后想好好的过日子呢,就得认清形势,安守本分。礼多人不怪,只怕将来我讨好她,要比让易哥哥高兴还要多用心呢。”迟迟再也忍耐不住,拍案而起,见红若翦水双瞳平静无波的凝视自己,拳头握了又握,终是松开。
不知不觉已是半夜,红若推开窗,院子里空无一人,再没有那个少年漫不经心的靠在树上望着自己,冰凉的针从手边滑落,她无力的靠在窗边。
迟迟也醒了,坐起身来看着月光下她的剪影。
中亭地白树栖鸦,冷霜无声湿桂花。形容的,原来正是此刻情景。
迟迟极低的叹了口气,拿了件披风走过去:“你最近一直说身子乏,不舒服,怎的还吹风?”红若笑道:“不碍事。我已经喝过药了。”迟迟道:“你要是这么不爱惜自己,身子垮了,可怎么去见易哥哥。好歹两个月都过去了,你莫非想功亏一篑。”红若笑道:“你教训的是。”说着正要转身,脚下却是一软,迟迟伸手扶住她,跌足抱怨:“瞧瞧,才说着。”一面将她搀到床上躺下,又替她脱了鞋。忽觉掌心温热,抬起手借着月光一看,倒没有立刻魂飞魄散,只觉得寒意从心底慢慢的渗出来,散到四肢百骸去。
折腾了整整一宿。陈祝川焦急的在屋外踱步,那大夫走出来,不敢看他,只是低着头走近了:“莫说那胎儿,就是萧姑娘自己,只怕也是不成了。”晴空里乍然劈下一个响雷来,陈祝川一把抓住大夫,一字一句的问:“你确定?”大夫吓得手抖脚软,再说不出半句话来。骆何在旁边咳嗽一声,他方松开了手,面上尽是苦笑:“我,我如何同他交代?”骆何脸上悲悯苦痛之色更深,走了两步,立在窗下。
他耳力极好,听见红若的声音低低传来:“迟迟,你怪不怪我,没有告诉你我已经有了孩子?”迟迟似在哽咽,却仍用欢快的语调答道:“我怎会怪你?我知道,你想给我一个惊喜。”红若幽幽叹气:“不是。我还未成亲有了孩子,到底也不是件体面的事情。”迟迟沉默片刻,方柔声道:“体面很重要么?就算你做了再惊世骇俗的事情,也休想和我相比。我比你更加的不听话,不懂体面为何物。”悉悉梭梭的声音响起,好像是红若挣扎着要坐起来:“大夫怎么说?我流了这么多血,这孩子没事么?”声音轻轻颤抖着,里面有太多软弱的期盼与自欺。迟迟深深的吸了一口气,笑道:“当然没事。易哥哥的孩子,跟他一般强壮。”骆何再也听不下去,转身走了几步,坐在院中,垂首望着自己的双手,想到十多年前旧事,愈觉悲凉。
红若听了迟迟的话放下心来,乖巧的靠在她怀中,忽然想起什么,拉着迟迟的手道:“我突然好像唱曲,却没有力气。”迟迟问:“你想唱什么,我帮你唱好了。”红若脸上绽放一个飘忽而美丽的微笑:“你记得娘爱的那只曲子么?”迟迟听见自己心中喀喇数声,再无力挽狂澜的坚定,只是那样兵败如山倒的碎裂,碎裂成千片万片。嘴上却已经不由自主的轻轻唱起:“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红若的身体在她怀中轻轻颤抖,她停下来,红若却焦急的抓住她:“一直唱下去,莫要停。我和你说着话,你只管唱给我听。”
迟迟微笑,大声应道:“你说什么我都听你的。”
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
红若轻轻的道:“怎么好像就到冬天了,竟已经这样冷了。冷得我都快看不清楚。”迟迟将她抱的更紧,歌声却未停止。
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
那叹息自身体最底处发出,无奈到极处,反而有种释然。红若微微的笑:“我却不甘心啊。我什么都准备好了,我愿意委屈了,为什么,还是老天还是不放过我。”
泪珠终于倾泻下来。红若努力的伸手替迟迟去擦:“好妹妹,别哭。既然我这辈子,注定不能得到完整的一个心爱之人,这样收梢倒也不坏。”她的艳色在晨光中惊人的显现出来,眸子也如深潭一般流转生光。
“我还想再见他一面。我从未怪过他,真的。”
迟迟低下头,那句话想问却问不出口,只是看着她:“你想见谁?赵靖,还是赵易?”
红若合上眼睛:“迟迟,你允诺我,无论如何都要听从自己的心意,不管多不可思议,也要让自己幸福。”
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
歌声终于渐渐低了下去。迟迟把脸贴在红若冰冷的颊上:“姐姐,我带你去见他好不好?”
行草深(十二)
(十二)余音又是淅淅沥沥的小雨。一庭的落叶被雨水浸软,耷拉在阶前,花盆边和青砖上。
陈祝川看了看阴暗的天色,叹了口气:“这个天气下葬,真真是。。。。。”陈家二公子陈铁站在一旁,接口道:“今日未必能下葬。”陈祝川眉头微皱,更深的叹息:“骆姑娘还在那里?”陈铁点头:“也不哭,就抱着萧姑娘的尸体一直坐着,不许旁人去碰。”陈祝川苦笑:“她如此反应,不知易公子将来知道了,又会怎样。”陈铁沉吟:“这却难说。他毕竟刚有了新妇,纵是难受,也不至于悲痛过度。”陈祝川摇了摇头:“你不知道他的脾气。他看着大大咧咧,什么事情都不放在心上,可是性子激烈倔强。”陈铁忙说:“萧先生的信里说了,悠王得到了消息,下了死令,若是有人胆敢通知殿下,杀无赦。”陈祝川哦了一声,神情中有些疲倦,半晌才道:“这又能瞒多久?”陈铁不敢出声,却听陈祝川又道:“萧先生的信里还说什么了?”陈铁自袖中掏出信来,陈祝川接过,匆匆看毕,眉头锁得更深。
陈铁见他犹豫,咳嗽一声道:“爹,我知道你在想什么。这纯属意外,红若的孩子无论如何留不得,可谁知道她身子这么弱。。。。”陈祝川眉头一跳,显然被戳到了痛处,喃喃道:“是我害了她。”
陈铁硬下心继续道:“可是萧先生的话也不是没有道理。咱们部署多年,总不能坏在这个节骨眼上。不怕一万,只怕万一。”陈祝川默然,许久之后淡淡一笑:“你放心,爹不会不明事理。我已经叫你大哥去布置了,萧姑娘一入土就动手。弓箭手都已经埋伏妥当。”
过了不多久,陈家大公子陈坚匆匆走进来,也不多话,只是点了点头。陈祝川负手又看看天色:“差不多了。我亲自去劝劝骆姑娘。”想了想又停下脚步,“我叫你们看紧他们,没有差错罢。”陈坚垂手道:“爹你放心,从昨天晚上起我就叫他们守住那屋子,连个苍蝇都逃不出去。骆老爷的房间也是一样。”陈铁已经撑了伞,陈祝川举步前行。
红若的屋门紧闭。陈祝川敲门,无人应声,他朗声道:“骆姑娘,已经三日了。还是让萧姑娘入土为安罢。”等了半晌,依旧没有动静。他皱眉,旁边已经有家丁凑上来:“骆姑娘哭了一宿,想来是累了。早上他们进去送饭,见她趴在床边睡着,都不敢惊醒她。”陈祝川顿足:“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扬声道:“骆姑娘,我进来了。”说着推门而入。
帘幕低垂,红若挑了素净的淡紫与浅白,在此刻显得格外惨淡。隐约可见床边有个少女抱住个人靠在床边。秋风穿过屋子,吹的帘子啪啪乱响,陈祝川长叹:“骆姑娘,你这样抱着萧姑娘不吃不喝,也不让她下葬,萧姑娘在天之灵情何以堪?”迟迟还是不动。陈祝川无奈,挑帘而入。眼前情景让他愣在当地,只觉一阵胸闷气短,过了片刻才勉强定住心神,厉声喝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