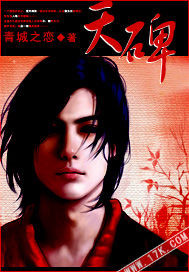土家血魂碑-第2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等我终于看清那两个怪人确实是满鸟鸟和寄爷时,悬着的心放了下来,心脏的跳动也慢慢变得轻快而有节奏。
而此时,那两个“怪人”又是另一番情形。
只见他们像练相扑一样,互抱着对方的肩膀,脑袋交替在对方的身体上胡乱擦拭。稍壮的那个人自然是满鸟鸟,他仅穿着一条花里胡哨地三角短裤——这条短裤我当然见过——本来就肌肉隆起的各个部件布满了血红色的条棱,象套着一件补丁盖补丁的紧身服。寄爷也裸着身体——相比而言,他老人家的肌肉就不叫“肌肉”而应该叫“肥肉”了——同样是红色条棱满身,随着身体的不断晃动,肚皮也跟着波澜起伏,就象腰上套着一个充气不足的红色游泳圈。
满鸟鸟边忙碌着,边侧头裂嘴朝我笑了一下,露出白森森的牙齿,吃力地说:“你龟儿子跑个铲铲啊?快把你脑壳拿来帮我止痒!”
我愣了下,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了!
估计这两个伙计也是从那藿麻林中钻过来,但是没我走运,除了衣服,没有可以裹住身体的棕绳,才导致他们穿了这一身旷古奇闻的红“衣服”,那本来的衣服,肯定粘满了藿麻草的绒毛,如果坚持穿在身上,那与慢性自杀何异?
我在好笑的同时,心里唉叹一声,满鸟鸟是个猪脑壳,未必连寄爷这等高人也脑子搭铁,仿照我的方法,用头发去解满身的藿麻草毒?
“你杵在那里搓卵啊?你的良心被花儿吃了是不?老子们冒死来追你,你竟然见死不救?”满鸟鸟见我似笑非笑,站着不动,急了,嘴里开始冒“粪渣渣”。
我醒过神,见他们的神情痛苦不堪,忘了刚在心里骂满鸟鸟是猪脑壳,跑过去伸着脑袋准备去他们身上擦拭。
“等等,我有办法解你们身上的毒。”我及时刹住车,扯开那两个正在“练相扑”的人。
“你龟儿子有铲铲办法,快点,老子痒得直差刮皮了!”满鸟鸟高声叫嚷,嘴里的脏话就像涓涓细流连绵不绝。
我正准备反攻,想起他和寄爷最终还是没有抛下我,忍着如此大的痛苦追我而来,心里有点感动有点愧疚,所以,隐忍着满腔的“枪弹”不发。
寄爷在此过程中一直没有说话,被我扯开后,他丑陋的脸对着我,让我吓了一跳,那哪还是一张人脸啊,嘴歪鼻斜,额肥眼肿,胡子象被野火扫过一般凌乱不堪,与画中的钟魁兄还要丑上N个档次,N大于等于五。
我也急了,拖起寄爷和满鸟鸟,就往水竹林中钻,刚靠近水竹林边缘,突然想起那莫名其妙的环境,这么冒冒失失让他们进去,他们会不会在里面迷路?
想到这里,我迅速解下腰上的棕绳,两头分别捆住寄爷和满鸟鸟的一只手,折成对折,再把对折形成的绳头牢牢捆在离水竹林边缘一米远的一棵青岗树上,“好了,你们进水竹林吧,等下就可以解去藿麻草毒。”
满鸟鸟狐疑地看了我一眼,“你这是么子波依办法?”
“杀猪杀屁股,各有各的搞法!”我阴笑着看了他一眼,“快进去吧!少里鸡拉巴啰嗦!”
满鸟鸟和寄爷对视一眼,又看了我一眼,双双哈着腰钻进水竹林中。
我的想法是,既然我身上的藿麻草毒可以在这诡异的水竹林中解除,让他们到里面去滚一转,兴许也可以解去他们身上的毒呢?既免了我脑袋辛劳,又可以让他们尽快免除痛苦,这是屙尿擤鼻涕——两拿的事,何乐而不为呢?他们早点解毒,我们就可以早点去搜救覃瓶儿,时间早一分,覃瓶儿的危 3ǔωω。cōm险就少一分。人多力量大,撞鬼也不怕。通常说,钱是男人胆,这话不一定放之四海而皆准,比如在现在这个场合,钱有毛用啊。依我说,朋友才是男人胆,人在困难时有友情支撑,那胆色自然壮大许多。
想是这样想,心里其实也难免十五个吊桶打水。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我身上的藿麻草毒是水竹林中的雾气所解还是那只竹荪的香气所解,如果是后者,那就惨了,如果不能解毒,寄爷倒没什么,满鸟鸟那张破潲缸嘴还不把我“日绝”得一佛升天,二佛出世?
算了,不想了。如果真像满鸟鸟所说,命中该吃卵,称肉搭猪茎,在没办法的情况下,猪茎也要吃下去,总比没肉吃要强。
我给满鸟鸟和寄爷捆上绳子,目的就是怕他们和我一样在里面迷路,如果他们也遇到我那样的情形,我拉着绳子一扯,牵着他们出来就是了。我暗暗为自己的聪明得意。
不知何故,我此时心态很平和。藿麻林中那种因覃瓶儿生死不明而产生的绝望、伤悲、焦燥竟消失得无影无踪,潜意识里覃瓶儿没有任何危 3ǔωω。cōm险,仅仅是在前面等我们。这种感觉很奇怪,我曾多次经历过,心中想到亲人没事,事后就真的没事。
我抬眼去搜寻水竹林中的满鸟鸟和寄爷。因为我站在稍高的位置,加上能见度大大提高,又有手电光,虽然水竹林中雾气蒸腾,我还是很快就找到了他们俩的身影。满鸟鸟紧贴着寄爷,脑袋左摇右晃,不晓得在跟寄爷说些什么。我暗暗好笑,满鸟鸟恐怕被所谓的“半傀”吓得想唱“你让我依靠,让我靠……”了!
见他们并不像我先前那样水竹林中乱蹿,想必他们并无大碍,我才晃着手电,打量周围的环境……
这是一个类似圆形鼎罐的洞厅,只不过这“鼎罐”好像被谁砸得瘪头扁脑,内壁一些石头不规则的突出来,头上的“鼎罐盖”破了几丝缝,有几缕不太明显的天光漏下来。洞厅不大,直径大约二十米,洞壁上挂满了厚厚的、嫩黄色的猴儿草,象蒸苞谷饭留下的一大块锅巴。水竹林在洞厅的底部,七八十株低矮的水竹林疏落有致。
我十分纳闷,就这么小的一个毫不起眼的小地方,怎么会把我困在里面差不多一个小时呢?难道我竟遇到了传说中的什么法阵?
现在想起在水竹林中的遭遇,还心有余悸,怪事年年有,今年特别多。最奇怪的是,那熟悉的拐杖杵在地上的声音真是我爷爷显灵了?如果真显灵,为什么我又看不见他老人家?那诡异的竹荪究竟是何来历,为何那般巨大?我为什么差点定被“嫁血”所害?是谁施展了“嫁血”妖术?为什么三声声音过后,胀满血的竹荪突然爆裂?我历来是不信神,不信鬼,全靠自己胳膊腿,但这几天遇到的事情却一次又一次摧残着我心中的信念。
船到桥头自然直,我叹了口气,摇摇头,不打算再细想下去,拿着手电,在水竹林中仔仔细细地扫了几圈。
噫?我忽然大惊!
先前没注意,此时细看之下,我惊奇地发现那些看似杂乱无章的水竹丛似乎排列成了一个奇异的图形。
水竹丛形成了两只犬一样的图形,它们的位置排列很奇特,以其中一只作为参照的话,另一只就是它的镜像再水平旋转180度,就像并排的6跟9一样。两只犬形图相距不远,中间形成了一条笔直的通道,犬形图中某些地方也是空白的区域,除了地面上的猴儿草没有一根其它的植物或岩石之类的东西。
怪了,中间这条笔直的通道正好从我脚下延伸到对面我初进水竹林中时所站的位置,我怎么会在里面迷路呢?打死我也不相信,这两只犬形图是天然形成的,那么,肯定是人为布置的,那又是谁布置成如此形状?这形状究竟为何物?有何目的?难道真是一座迷惑人的法阵?
我眼光痴迷,头乱如麻,无意一瞥,隐约发现寄爷和满鸟鸟不知何时已经分开了,都半勾着腰,在水竹林中似动非动,像在找什么东西。
我吓了一跳,心中大急,难道他们也遇到我先前的情形被迷住了?也遇到“嫁血”了?本以为有绳子作为保险,没想到还是出现这种状况。这真是通黄鳝来水蛇——算路不跟算路来啊,覃瓶儿现在下落不明,这两个伙计又遭遇不测,这可真叫我喊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
我几步蹦到青岗树边,不管三七二十一,握着绳子使劲往后拉了一下,瞥见寄爷和满鸟鸟被拉得一趔趄,身体晃了两晃,又撅着屁股回到他们各自前面的水竹丛中旁。
我更急了,紧握着绳子像拔河一样几下就把满鸟鸟和寄爷从水竹林中拉了出来。
满鸟鸟一出来,就气急败坏地冲我狂骂:“你个龟儿子,火石落脚背了是不?老子撒泡尿都不得安逸,你个小里鸡拉巴娃儿哟!”
我一愣,敢情他和寄爷是在水竹前撒尿?难怪他们要分开哟!
“你也是,你撒尿要摆好姿势嘛,要把一只脚翘起来嘛!”我对满鸟鸟笑骂一声,见他们身上的红色“补丁”果然已消失得干干净净,恢复出正常的皮色来,只是都裸着身子,那情形实在不很雅观。
满鸟鸟骂骂咧咧去把他和寄爷的衣服找来,站在边上放入水竹林中绕了几转,和寄爷胡乱套在身上。我苦笑一下,水竹林中能解藿麻草毒,难道还能化去粘在衣服上的藿麻草绒毛吗?见寄爷和满鸟并未异状,我略略放心的同时,心中又多填了一个疑问。
不过,我现在大部分的注意力在那个奇异的图形上。寄爷还没穿戴停当,我就拉着他指着水竹林说:“您家看看这是么子怪图形哟?”寄爷听我问得急,接过手电,脖子一伸一缩,仔细看了水竹林一遍,脸色突然就变了。
“天爷爷,这不是土家族的图腾吗?”寄爷嘶着嗓子嚎了一声。
“图腾?这两只狗就是土家族的图腾?”我疑惑地问。
“小胆胆儿莫乱说,这哪是狗呢?那是两只虎啊!”
“虎?这哪象老虎的样子?”我又仔细看了几眼,没看出哪一点象虎的样子。
“你还记不记得文书老汉说的那句话,‘向王廪君死,魂魄化白虎’,据说我们土家人就是白虎的后裔,还有句谚语叫‘三梦白虎当堂坐,当堂坐的是家神’,所以我们土家族的图腾就是白虎,这水竹丛形成的图形正是老班子流传下来的图腾画。”
我正欲再问,却不防满鸟鸟又开始乍呼。“么子图腾?我看是头疼,鹰鹰你还啰嗦个卵啊,还不赶紧去把瓶儿找回来?”满鸟鸟穿好衣服,瞪着眼不满地看着我说,“我和安哥忍着脚痛,冒险跳进藿麻林找你们,就怕你和瓶儿有危 3ǔωω。cōm险,现在却又不急了?”这伙计,没有覃瓶儿在场,顾忌少了许多,满嘴都是雄性动物那特有的柱状玩意儿。
我当然不甘示弱,吃人三餐,也要还人一席嘛,“满鸟鸟,那东西挂在你嘴上的是不?你把那玩意儿当成你的图腾了嗦?回去抓几把石灰好生把你那潲缸嘴洗洗!消消毒!”
寄爷见和满鸟鸟又要开始打嘴仗,赶紧阻止:“行哒行哒,鸟鸟说得有道理,我们还是先把覃姑娘找回来再说吧!现在不是三言两语就说得利糊(清楚)的!”说完到草旮旯去找出他的背篓背了,仰头看着花儿消失的那个岩隙,说:“这个石洞啷格这么古怪?”
第二十五章 痒痒石
本来我肚子里沤着一大堆疑问,但想想当务之急还是先找到覃瓶儿,至于满肚子的疑问,多沤一会儿又不会发酵蒸发,还是稍后再说吧。
自我从水竹林中脱困以来,我心里就已经没有了担忧焦虑,反而心态平和,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似乎觉得覃瓶儿根本没有一丝危 3ǔωω。cōm险。尽管如此,我想只有覃瓶儿活生生站在面前我才会彻底放心。
听寄爷说石洞古怪,我才想起被我忽略了的岩隙,才想起花儿。那伙计跑到哪里去了呢?怎么没有一丝声响?是不是找到覃瓶儿了?按道理说,花儿如果真的找到了覃瓶儿,如果覃瓶儿出现危 3ǔωω。cōm险,它肯定会跑回来示警,现在踪影不见,只有两个结果:一是它还没找到覃瓶儿,二是覃瓶儿安全,我当然宁愿相信是第二个结果。
眼前这个山洞,严格来说并不是通常意义的石洞,而是由一堆巨大青石相互支撑而形成的一个三四米高的岩隙。那些青石大的估计有四五吨重,小的也有磨盘般大小;青石们并不规则,形态各异,有的青石边缘甚至象刀锋般锐利;青石之间很松散,大部分的支撑点都非常狭小,更触目惊心的是,基本上是小块青石在下,大块青石在上,眼晕目眩之时,上部的巨大青石仿佛摇摇欲坠;手电光从那个约一米宽的缝隙照进去,目之所及,最宽的地方能容三人并排通行,而最窄的地方仅能一人匍匐通过;缝隙里面更是乱石穿空,仿佛犬牙交错;地上铺满了或大或小边缘锋利的碎石,寸草不生。
青石堆向洞壁两侧绵延,不知有多远,受视线所限,更远处我们就根本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情形。
我和寄爷互看一眼,都不屑地笑笑,这种情形对我们俩来说,早已司空见惯。我大学毕业那年,为了挣钱买生活用品,曾跟着寄爷在“一碗水”所在的岩山上打炮眼,抡二锤。那岩山下部已被采石工人掏进去一个凹洞,当我们在里面挥汗如雨时,头顶上就是一块块像菜刀一般的石头,我刚去时很害怕,担心那些石头会不会突然梭下来把人切成一段段的“年肉”,时间一长,见并无事故发生,我的心也慢慢变得麻木了。
“走吧!”寄爷说,“莫怕,这堆乱石不晓得是么时候堆在这里的,只要我们小心点,应该不会垮下来!”说完当先上前,小心翼翼向里面侦察了一下,随即钻了进去。
我和满鸟鸟鱼贯而入。当然,满鸟鸟走在我前面,我当断后官,嘿嘿!原因不言自明。
我刚钻进岩隙,背上的竹弓不经意在一块青石上轻轻一刮,头顶周围的青石随即轰轰乱响乱动,喀啦啦声不绝于耳,好像随时会垮塌下来一般,粗细不一的岩沙洒了我们满头。
我胯下的两个蛋蛋也像被吓着了,直往上缩,一股热气从小腹间直冲而下,引得平时并不抛头露面的毛发也似乎要炸开,更不用说浑身的汗毛了。
满鸟鸟和寄爷也大惊失色,“快退!快退!这里要垮了!”寄爷急得屁股往后一拱,引起多诺米骨牌效应,把我挤得一屁股坐在岩隙外的地上。我不及细想,翻身连爬了几步,回头见寄爷和满鸟鸟也已吓瘫在地上。
那堆乱石轰隆隆乱响了一阵,竟渐渐停了,石堆也并未垮下来,连那岩隙也没发生任何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