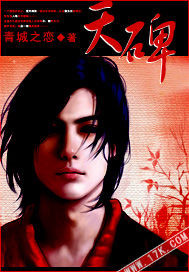土家血魂碑-第1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黑项琏的东西也显现出萎靡不振的态势,不像先前那样劲鼓鼓气宇轩昂了。
见此情形,我心中大喜,顾不得疼痛,甩开寄爷的手,用力地在覃瓶儿脸上、脖子上仔仔细细涂抹起来。见拇指不再流血,我用右手两根手指使力一挤,鲜血再次涌出来。我双手搓了几把,见两只手掌上都是鲜血,捧着覃瓶儿的脸卖力地抚摸起来,直到我感觉到她脸皮变得光滑,不再硌手,而且感觉到她的脸有了温度,我才摊开两手,看见满手的乌红。
覃瓶儿嘴唇抖了抖,开始微弱地呻吟起来。一屋人长长出了口气。寄爷吩咐我妈打来热水,用毛巾给覃瓶儿洗去脸上和脖子的污秽。那盆洗脸水很快就变成一盆乌红的脏水。
我们再看覃瓶儿的脸,发现她脸上出现了几丝血色,不再像先前那样一片惨白,那些蚯蚓状的东西也消失得无影无踪,只留下额头上那个硕大的伤疤和脸上星星点点的伤疤,真正成为一张芝麻饼了!
没过多久,覃瓶儿“嘤咛”一声睁开眼睛,虚弱地看着围在她身边的人,眼神很迷茫。看样子,她还不知道自己已到鬼门关闯荡了一圈。
“不要说话,妹娃儿!休息好了再说!——嫂子,你带她去睡觉吧!”寄爷先温柔地对覃瓶儿说了声,接着吩咐我妈道。
我妈答应一声,扶着覃瓶儿进了内屋。
我妈从内屋出来,寄爷又说:“嫂子,你把哥的猫子(斧头)和墨斗放在那姑娘的枕头边吧!”我妈虽然不知寄爷的用意,但历来对寄爷说的话很信从,急忙找来我父亲的斧头和墨斗,拿着进内屋去了。我父亲是木匠,所以这些东西并不难找。
我见覃瓶儿安顿下来,才叫满鸟鸟给我打来一盆热水,洗了手。刚想坐下来抽支烟,又隐约听见覃瓶儿在内屋呻吟起来。我妈急慌慌跑出来,向寄爷喊道:“他寄爷,那姑娘背上是不是也有‘转蛇疸’哟?啷格她按着背上连声叫唤呢?”寄爷听了脸色变了几变,抬脚就往内屋走。走到门口,他迟疑了一下,对我妈说:“嫂子,你去看看她背上有没有那些鬼东西?”我妈听了转身就想进屋。
我突然醒过神,急忙叫住我妈:“妈,她背上没有那些东西!”我明白覃瓶儿手按着背部呻吟的原因,担心我妈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被覃瓶儿背上那幅绿毛图吓到。我赶紧倒了满满一杯酒,递到我妈手上,“妈,你莫去看她的背,她背上应该没有‘转蛇疸’,您家把这杯酒给她喝了就没事了!”
我妈疑惑地看我一眼,又用眼光请示了一下同样满脸不解的寄爷,寄爷点点头,“那你去试试吧!”我妈端着酒杯再次走进内屋。
覃瓶儿喝了酒,呻吟弱了些。我站在内屋门口,见我妈拿着空杯子出来,又在杯子里倒了满满一杯酒,“妈,你再让她喝几杯吧!”如此几个往返,覃瓶儿安静下来。我妈见覃瓶儿睡着了,走到屋外,奇怪地说:“这姑娘真是怪哟,喝酒就像喝白开水一样,到底是啷格回事哩?”
我赶紧转移话题,“妈,你给我找一张创可贴吧!”我妈到抽屉里翻了一阵,没找到创可贴,只好拿着手电到外面找了一块小蜘蛛网,贴在我拇指的伤口上,鲜血才渐渐止住。
第十一章 同梦。令牌碑
覃瓶儿安顿下来,众人才长长舒口气。
屋里的草烟味和桐油味还没完全散尽,丝丝缕缕钻入鼻孔,搅得我的脑子发胀发昏。我走到窗户边,长长吸了口气,吹吹手指,平定一下纷乱的思绪,重新坐回椅子,准备请教寄爷这位高人。
可是话到嘴边,我又犹豫了。寄爷来我家之前,文书老汉提到“白虎”是土家祖先廪君,我惊恐悚之下失态摔碎酒杯,当时就被一屋人探询的眼光追讨得左右为难,差点逼上梁山和盘托出覃瓶儿的事情,幸好寄爷到来才将这个话题岔开。当时我还暗自庆幸暂时保住了覃瓶儿的秘密,哪知刚刚发生的事情将整个事件渲染得更加扑朔迷离,又被一屋人亲眼所见,要想用纸包住火恐怕是不容易了。
问题是,如果我直接告诉他们覃瓶儿背上有幅绿毛图,会不会对覃瓶儿的生活造成什么影响,会不会让她感觉难堪?其他人我还不担心,我最怕文书老汉那张嘴,不客气地讲,他那张嘴纯属一“破潲缸”。他长期生活在山旮旯,没见过什么世面,针鼻子大点事情,从他嘴里过一转,转眼就变成簸箕大的新闻。
但是,看目前的形势,又不得不说。我叹了口气,沉吟着刚想开口,满鸟鸟及时救了驾,“安哥,你啷格想到用鹰鹰的血来救瓶儿?难道鹰鹰的血是良药?那他要发大财了!”当然,他什么时候都不忘揶揄“日绝”我。
寄爷还没回答满鸟鸟的问题,文书老汉果然急不可耐,“安人,据我老人家所知,‘转蛇疸’一般是长在腰上,对吧?而且需要用麻线浸冷水在身上刮过才会现出来,啷格会平白无故长在那姑娘的脖子上和脸上呢?”
“……应该不是‘转蛇疸’吧?”寄爷迟疑着说。
“不是‘转蛇疸’?那是啥子东西?”我顺坎脱背系,决定先搞清这个问题再说。
“所谓‘转蛇疸’,在医学上叫‘带状疱疹’,其症状确实和覃姑娘脸上的东西差不多,以前治‘转蛇疸’也确实需要用浸过水的麻线刮过皮肤后,带状疱疹才会现出来。”寄爷说,“刚才看见覃姑娘脸上的东西,我起初也以为是‘转蛇疸’,看见那几条疱疹正在向她额头集中,形势危急,来不及细想,也来不及找灯草和桐油,才点燃草烟,用烟头代替灯草。我看她呼吸微弱,所以就喷一口浓烟刺激她一下,看她有啥子反应……”
我心说,您家那个草烟,不但能把将死之人熏活,还能把活生生的人熏死啊。寄爷继续说道:“用烟头烧了她的额头后,我才叫嫂子去找灯草和桐油,打算用治‘转蛇疸’的方法来治那些东西。后来发现灯草根本不起作用,才想起她可能中了那只蛤蟆的阴毒,而解阴毒最好药物当然是阳血,所以才叫嫂子找来刷把戳破覃姑娘的脸,并咬破鹰鹰的左手拇指,用他的阳血来中和阴毒。没想到,居然起到了奇效……天意,天意啊!”
“瓶儿中了阴毒?我们怎么没事?”我奇道,“您家为什么偏偏要用我的血呢?而不是您家自己的或其他人的?”
“嘿嘿,”寄爷阴笑一声,“为啥子要用你的血而不用我各人的血,原因很简单,咬各人的手指,还真下不去口啊,而咬你的,又不是我痛,我才不管那么多。至于为啥子不咬其他人的,原因也很简单,一是你离得最近,二是……嘿嘿,我估计只有你才是龟男娃儿(处男),阳气最足嘛!”听了寄爷的话,我真想找块豆腐撞死算了!在这个高度发展的时代,二十郎当还是个处男实在不是一件光荣的事。
“你……”我的脸开始发烧,吹吹还在隐隐作痛的拇指,悻悻地说,“您家厉害,这事儿就算了……您家还没回答我前两个问题呢。”
“要弄清那两个问题,恐怕……你先得老老实实告诉我覃姑娘的真实来历吧?”寄爷眼睛亮亮地盯着我说,藏在烟雾背后的脸讳莫如深。
我一呆,暗叹该来的还是来了。踌躇半天,在寄爷炯炯有神的眼光逼视下,我狠狠心,将覃瓶儿背上的绿毛图、清和大师的偈语、我额头上的“土”字这一系列事情原原本本详细说了一遍。话音未落,满鸟鸟从椅子上弹起来,“瓶儿背上长了一幅图?是我见过的那幅?你昨天晚上去她房间就是去看那幅图?——妈那个‘波依’,怪不得会出现盐井坳那里的‘日古子’事情了,怪不得你一定要找安哥……”(波依:某个字的拼音。日古子:古怪)
我万没想到满鸟鸟在气氛如此压抑的场合,居然爆出一句粗口,狠狠剜他一眼,气恼地说:“你以为我去她房间做啥子?——你简直……满脑壳牛粪!”
满鸟鸟并不接招,一屁股塌得椅子高声抗议。“……我说呢,你眼巴巴盼安哥来就为这事儿……安哥,你说说,这到底是啷格回事儿?”
寄爷并不直接回答满鸟鸟的问题,反问道:“盐井坳出啥子‘日古子’事情了?”满鸟鸟振奋精神,口水横飞将我们在盐井坳看见的“云妖”绘声绘色描述了一遍。
寄爷听了不吱声,皱着眉头闷头抽烟。寄爷抽草烟很有个性,就是他必须把火机拿着手里反复点那忽燃忽熄的草烟,不晓得是草烟的质量问题还是寄爷的习惯问题。火机在他手里,简直就是倒八辈子血霉。
沉默了半天,直到寄爷被一屋人盯得不好意思了,他才字斟句酌地说:“从你讲的情况来看,覃姑娘背上那幅绿毛图,包括你们在盐井坳看到的,以及今晚上出现的癞壳包,都似乎和土家族失传已久的觋术有关。”
“觋术?啥子是觋术?”满鸟鸟抢在前面问。
“这个……我也只是猜测,是不是觋术我也说不准。对觋术的了解,我也是从经常打交道的道师先生那里听到一些。那些道师先生和我摆龙阵时,曾经提到过早年间的觋术。据他们说,觋术其实就是闻名天下的巫术,但是与常人眼中的巫术又有区别,学习觋术的人只能是男性。古书上也有记载,女巫为巫,男巫为觋。你们晓得不?其实觋师就是我们熟知的道师先生,以前也叫‘土老师’或‘端公’,据说他们都是通神灵的人……当然,现在还有没有会觋术的人,不得而知。毕竟时代不同了嘛!”
寄爷看着我,继续说道:“那个清和大师确实让人捉摸不透,那四句偈语我也暂时无法解释……”寄爷转头问我父亲:“哥,你有没有亲叔叔或亲伯伯?”我父亲愣了一下,“这个……应该没有啊!”
寄爷没问出结果,回头对我说:“至于你额头上的‘土’字,我一时也无法说清楚……”寄爷见我有垂头丧气的意思,语气一转,“不过,既然清和大师这么说,肯定有他的道理……高人就爱搞这些捉摸不透的东西。”
“废话,没道理,捉摸得透,我来找你这个高人搓鸟啊?”我心里嘀咕,内心的不满情绪不自觉地从脸上流露出来。寄爷何等老辣,早从我脸上的表情看出我的心思,讪然一笑,无话找话转移话题,“我啷格觉得覃姑娘非常面熟呢?好像在哪里见过……”
我撇撇嘴,强颜一笑,“我第一次见她也觉得面熟,后来得知我曾经在梦中见过她……”
“梦中?”寄爷一拍大腿,“对哒,我也是在梦中见过她。”
寄爷突如其来的举动惊得一屋人齐齐看着他。“安哥,满鹰鹰是看见任何女的都说面熟,想不到你恁大把年纪也有这个爱好……”满鸟鸟痞笑着对寄爷说。
“你们以为我在日白?我真的在梦中见过她……我想想,对了,是六月初六那个怪梦,我被鬼压床了……”
“六月初六?鬼压床?”我猛地站起来,带动椅背翻在地上摔成两半。
“你再说一遍……”我不理会满屋刀子般的目光,声嘶力竭向寄爷喊道。
寄爷奇怪地看我一眼,“六月初六那天中午,我麻了二两苞谷酒,躺在板凳上睡着了,没想到居然遭遇‘鬼压床’。梦中居然出现了我爷爷、一条蟒蛇、一头白虎和一个黄衣少女,那黄衣少女……还拿个啥子东西在我眼前晃来晃去。现在想起来,那黄衣少女确实和覃姑娘长得很相像……噫!鹰鹰,你啷格了?脸色这么难看?”
寄爷在讲述他的梦境时,我眼前发黑,寄爷嘴里吐出的每一个字,象一颗颗子弹射向我的心脏,使我的心脏狂跳如雷。我估计,此时此刻,如果有人拿个听诊器放在我胸口,就可以跟着我心脏跳动的节奏跳踢踏舞!!
过了半晌,我双手撑住椅子,稳定心神,抖抖索索掏出一支烟,点燃长吸几口,才嗫嚅着说:“寄爷,我……我也做了一个同样的梦,也是在六月初六那天……你说稀奇不?”“啊?”一屋人同时瞪大眼睛看着我。
我一口把烟抽得只剩半支,狠狠弹掉烟灰,把我六月初六做的那个怪梦一五一十说了出来。寄爷听完没说话,我看见他手一抖,一大砣灰黑的烟灰直直掉进他面前的酒杯。
寄爷皱着眉,沉默半天,才自言自语地说:“怪了……两个人居然在同一天做了一个同样的梦?”不等其人有所反应,寄爷抬头问我:“你看清那个戳在你腰上的东西是啥子了吗?”
“没有。我觉得那东西很熟悉,但是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
“是不是象……令牌碑?”
“对!就是令牌碑!就是令牌碑!”我大叫一声。梦中那黄衣少女戳在我腰上的东西,经寄爷提醒,终于清晰地从我脑海浮现出来——那不分明就是一块微型的令牌碑吗?
令牌碑,是我们当地一种很常见的立在坟前的石碑,上面一般刻着“故显考某公讳某老大人之墓”之类的阴文,阴文的右边镌刻着死者的生卒年月,而左边则是孝子贤孙的名字。不过,普通人家才会在已逝老人坟前立令牌碑,稍微富裕的人家会立五厢碑或七厢碑。不管是令牌碑还是多厢碑,除了起着“勉阳人之意”的作用,同时还蕴含着土家人对先辈的敬畏和崇拜。
“还有人做过这个梦吗?”寄爷问道。其他人醒过神,纷纷摇头表示没有。
“那就怪了,为啥子只有我和鹰鹰做这样一个梦呢?连时间和内容都相同……那块令牌碑到底是啥子东西……”寄爷自言自语,翘着二郎腿,坐在椅子上利用椅子后腿一前一后晃荡;右手拿着打火机,凑近衔在嘴里的早已熄灭的草烟,将点未点;满脸困惑,眼神空洞。
其他人大气不敢出,摒住呼吸,害怕打断寄爷冥思苦想。五双眼睛却牢牢盯着他的嘴,眼光在大雨磅礴的夜晚象几把利剑,在空中交织穿插,似乎可以听见它们相互碰撞的铿锵声……
“鹰鹰,覃姑娘还给你说过别的啥子没?”寄爷突然开口,吓得我一激灵,双肩一耸,眼神收拢,呆呆看着寄爷的嘴好几秒钟,才(炫)恍(书)然(网)大悟,“这个……好像除了我跟你们说过的,再没说别的吧?”我在脑海翻了一遍,隐隐记得昨晚我在硒都宾馆追问覃瓶儿的来历时,覃瓶儿的神态不太自然,可惜当时我全部心思都放在清和大师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