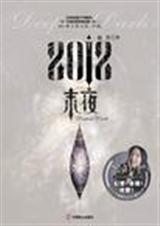1238公里的忧伤-第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把她压倒在床上,此刻我已经欲望高涨,手忙脚乱地解她的牛仔裤,可她躺着,这显得挺困难。
她在床上站起来,挺了挺臀部,把牛仔裤脱了。她躺下来,对我说:“小凡你轻点儿,我妈在外头。”
我点点头,两个人紧紧拥抱在一起。
由于过于激动,她帮我脱下内裤后,我就已经感觉酸涨难忍。
尔后我压在她身上,瞎忙一气。
一会儿她用中央台播音员似的严肃语调说:“进去了。”
我再奋力几下,就知道自己射在里面了。
她笑着摸摸我的脑袋,说:“小凡,我觉得挺对不起你女朋友的。”
“第一次,太紧张了,不好意思。”我坦诚笑道。
两人又搂着待了一会儿,其实这情形颇为好笑,两个小孩儿躺在窄小的床上互相拥着对方,上身衣服都还穿得颇为齐整,下边却是光溜溜的赤诚相见。
少年若只如初见6
又一会儿,天色已经黑下来,房间里光线黯淡。我们也没有开灯,莫安的形象逐渐模糊起来,仿佛沉浸在了这开始弥漫起来的夜雾里面。
外面传来高声的呼唤:“安安,挑好衣服没有?”
“快了!”她回了一喊,故意大声对我说,“徐迟,你觉得是这粉红色的好还是那淡蓝 色的好?”
我低低地回了句:“什么都不穿最好。”
她拧了一下我的腿,随后严肃地低声说道:“快起来!”
我起身整理一下,她又提高声音对门外说:“我挑好了,得换衣服了,还要洗澡,徐迟你出去一会儿。”
我便又回到客厅。
金毛狮王妇人仍在看电视,似乎连位置都没有挪动过。但我坐到她侧面的沙发上的时候,尽管离得她挺远,可还是清楚地觉察到她的鼻孔的每一下抽动。尽管她没有什么举动或言语,甚至可能连神情也没有变化过,我还是觉得她感觉出了什么,她应该是闻出了米青。液的味道。
过会儿莫安房间里哗哗的流水声响起来,金毛狮王妇女换了一下姿势,把翘着的左腿换成右腿。
她开口了:“吴凡,你好。”
我一下子就愣在当场,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我呆滞地重复了一遍:“我是徐迟。”
“甭说了,我的女儿我还不知道啊。”
她掐了正抽着的烟,才吸了一半,随即又纯熟地点了一根,抽烟的姿态恶俗不堪。
我问:“那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她瞥了瞥我说:“这也就巧了,上礼拜开家长会议,我和安安的班主任聊了聊,他是你语文老师吧,那天你还和他打招呼了呢,他告诉我说,瞧这个家伙,旷课旷得比安安还过分。”
我眼前浮现出我那热情洋溢极富表现欲有点儿文化的语文老师,私底下我们都觉得这人还挺不错的,虽然拿北京话来说是二了点儿。
我现在想立刻拔刀子捅了丫的。
她转换了语气说:“安安我也不知道该拿她怎么办,又老在外面混些不三不四的人。那个徐迟,说来真是麻烦,安安她那么不自重!”
我只得说:“也未必是不三不四了,也不一定找不到好的。”
我不知道此刻我在她眼里是什么形象,这番话说得实在是自己听了都脸红。
“你们玩的那些花招我还不知道,我是过来人了。”她懒洋洋地笑了笑,接着说,“现在没什么,大家开心,好聚好散,痛苦一阵子也就完了,可你是男孩儿,安安她是女孩子。”
“那又怎么了?”我说。
“两码事。”她有些急促地打断我说,“你还好,玩过几年,找个安分的人就过日子了吧,可女孩儿呢?”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从未和父母谈论过这类话题,而眼前这个恶俗不堪的中年妇人,这番话说来却如此动情入理。
“我也不拿你当外人。”她说,“甭管你跟安安是怎么回事儿,你将来也会和很多别的女孩儿在一起,不过有句话我想说。”
她顿了顿,狠狠抽了几口烟,也许是用力过猛吧,我感觉她粗糙皮肤上搽着的脂粉也要皲裂下来。
她说,“对别人好一点,记住,女孩儿是没有几年可以浪费的。”
这时门铃响,妇人碎步赶着去开门,满身肥肉乱颤,一阵香风几乎要把我刮晕过去。
来人估计就是莫安所说的“男的”了,瘦,精瘦,年纪应该不到40,样貌也绝对是英俊的,打扮得着实颇为出众。我差点儿被他那笔挺地往两边划出去的英式衬衫的小尖领戳破了镇定冷漠的表情,那线条,简直跟F22的机翼一样。
我知道自己应该告辞了,我笑着同妇人辞别,她礼貌地说:“安安还没出来呢,多没道理啊,让你干坐了那么久,真不去吃饭了吗?”
我说:“算了,家里有事儿呢。”
她殷勤地送我到门口,我听到她的粗重的呼吸,感觉到她的沉重的躯体,心里的感觉难以名状。
走出门来,我打车回到学校,取了车库里的自行车骑回家去,当时建国北路和庆春路交叉的那一大段还在修路,一路上坑坑洼洼,颠颠簸簸,我的心思,也不知所踪。
少年若只如初见7
好吧,我承认,那妇人的最后一句话实在是令我难以忘怀。
她象一块巨大的墓碑,悲凉地立在一片废墟之上,身体的废墟,感情的垃圾场,那个颓败的灵魂之中某种东西深深打动了我。可我,对这种感受又实在是难以名状。
那时的我,多少过于年少,虽然一时感动,事后多半也忘得干干净净,就象没有发生过 的梦幻。可没想到,这种悲凉,居然象个定时炸弹,在多年以后爆炸。
多年以后,回想遥远的那个午后和傍晚莫安的母亲对我说的那最后一句话,不禁眼眶湿润,一滴泪水居然流下来,是潮湿的,是咸的,是冰凉的。
第二章 现场直播的悲剧
现场直播的悲剧1
说说我的安安。
离开杭州以后我是在一个法语文化沙龙上认出了莫安,就那种场合通常会出现的那号女孩儿而言,她显得有些特立独行,与众不同。当时我坐在靠窗的一张藤椅上,没心思和谁说话,只是把目光漂来漂去,出现的无非是那些人,不是学成一脸呆样的全国外语院校法语水平联合测试的前几名,就是打扮得妖冶动人或者自以为妖冶动人和外教们腻在一起的女孩儿 。
我申明,那天是程禾硬拖着我去的。他带了几个北大法语系的几个家伙过来的,据说是因为他最近打算磕的一个女孩儿是外经贸大学法语系的,又据说今天她会过来。
自然,他想磕的那女孩儿就是莫安。
程禾在那次聚会上表现得有些夸张,但也还不失为得体。他对那个莫安殷勤备至,换了我要是个女孩儿,也会被他的甜言蜜语和比金城武还稍微英俊一点儿的外形打动,程禾的确称得上风度翩翩。
那女孩儿却似乎不为所动,她一手夹烟,一手居然从包里掏出一个超长的罐儿啤。她一边笑着听程禾说话,一边不时小小地抿上一口。
程禾很快就邀请莫安去一个他经常驻场的club跳舞,我只看见莫安连连点头。
后来等我和她好上了以后,我曾就此事向她求证:“第一次见你那晚上程禾邀你去club你一直点头答应来着。”
她说:“没有,我一直在摇头,因为第二天那个考试我考了全系第二,所以我记得特别清楚。”
我说:“你点头来着,我记得清楚。”
她坚持说:“没有,我后来跟你们一块儿去玩儿了的确,可我就是没点头。”
我说:“不对,你点了。”
她朝我瞪眼睛:“吴凡,再跟我抬杠我就掐你!”
我对她一直朝程禾点头这个情景,至今耿耿于怀。
那晚上,程禾,那个女孩儿,捎带上我,还有几个之前来了但一直在外头溜达的几个广院的经常和我们在一块儿混的家伙,一起去了一个club。
只有莫安一个女孩儿,所以气氛多少显得怪异,焦点都集中在她一个人身上,可她却坦然自若。她就跟一个人没事儿待家里似的,还盘起腿来坐在沙发上,谁说话要是爱听了就搭理几句,不爱听了就自己一个人坐着眯着眼睛喝酒,看着楼下的人群发呆。
程禾大概想在莫安面前表现表现,早早地就下场去换下了那个DJ,开始使出浑身解数调动人群,气氛也确实为之热烈不少。
不过,那女孩儿似乎并不关心,她只是把头枕在挂在不锈钢栏杆的胳膊上看舞动的人群,眼神漠然。
另外几个家伙呢,一则是觉得这女孩儿本来就是程禾想磕的,没必要搁这儿上劲儿,再则莫安又采取如此非暴力不合作的无懈可击态度,都觉得有些无趣,不一会儿都各自下场去跳舞了。
这桌上就剩下我和莫安了,我俩的位置正好对着,一副面面相觑的尴尬模样。
我并不喜欢club里的气氛,无奈被程禾拖来,心里还在担心明天的考试。我点着了根烟,抽了几口,没觉出什么味道。
而club里的家伙们此时的体力和心理状态都正达到高潮,更有个女孩儿已经把衣服脱了仅着运动款的文胸,也不知是有意为之还是药力作用所致。
我一点儿兴趣都没有,同时也无话可说,自从和现任女友不冷不热之后,我就一直那么死样怪气的。
我把才抽了一半的“沙龙”烟掐了,然后拿出烟盒挑出一根大麻烟点着了。
我看到程禾在向这里挥手,分明是要引起这女孩儿的注意。她也对程禾笑笑,然后便特意转过头来,如此就是直直地望着了我。
我觉得尴尬。
莫安后来坦白,当时第一次见我,以为我是性冷淡或者同性恋。
我把身子扭向正在打碟的程禾,朝他竖了竖大拇指以示鼓励,然后就保持了那个方向坐着,尽量不去瞧对面的那个姑娘。
莫安后来再一次对我坦白,就是因为我对她爱理不理,她突然对我产生了兴趣,因为她突然记得了某个她从小就认识的流氓。
我突然觉得这碟打得有些不太正常,仔细听了一会儿,似乎觉得其中节拍的频率和长度有些古怪。再用心分辨了一会儿,不禁哑然失笑:程禾这家伙用节拍的长度和音色在模拟摩尔斯电码。
我之所以能反应过来因为类似行为早有先例。那次我和程禾都在青岛,程禾和一个女孩儿在里屋,事先他就说要用那女孩儿的叫床声来发电报给我,我当时确实觉得这点子很精彩。
后来,我坐在外边算是会客厅的房间里的沙发上,搂着另外一个女孩儿看电视,就听见里面的声音。
那天程禾发的是:fuck,接着发了个perfect,后来该是个marvelous,不过在那个s尚未完成的时候程禾就已经完蛋了。
现在程禾只是不断地在重复一个词:shit。
看样子他不是不明白那女孩儿对他根本没意思。
“能给我一根儿吗?”坐在对面的女孩儿主动开口跟我说话。
我转过头来,嘴角带着笑,犹豫了一下,给了她根“沙龙”烟,她接过去了,但又指指我嘴上刁着的。
我只好打开烟盒,给了她一根大麻烟。
她点火的姿势还算熟练,可居然呛了一点儿出来,她又似乎是赌气似的猛闷了几口,随后很快她就晕了,靠在沙发上眯着眼睛享受。
过会儿我出于礼貌地问:“还行吧?”
她居然说:“这什么烟,怎么这么股味道,还让我直犯恶心。”
我不知道她是装蒜还是别的什么,若是前者可也太不地道了点儿,后者又显得此人愈发扑朔迷离。
我打不定主意是否该告诉她刚才抽的是大麻,我踌躇了一会儿,然后说:“你可能抽不惯吧。”
对面的女孩儿干脆脱掉了靴子,娇小的两脚缩进裙子里,她低头不语。
就是这个姿势,我脑中突然闪过一道白光。
我一阵激动,立刻站了起来,膝盖磕在了茶几上,撞得上面的杯子噼里啪啦地翻倒。
她抬起头来,有点儿迷惑地抬头望着我。
我轻轻说:“安安,安安,你太像莫安了!”
她猛地站起来,连靴子都没顾得上穿。
我颤抖着喉咙说:“我是吴凡。”
她身子一阵摇晃,忙用胳膊撑在了茶几上,不敢相信似的盯着我,目不转睛。
我更确信了,操,我怎么没认出是她呢。
不过也难怪,大晚上的我还一直装逼,戴着大大的墨镜。程禾看我今晚一副驴脸,知道我的脾气,肯定是都没告诉她我的名字。
莫安怎么会是这样子?她三年前,短短的头发已经蓄成披肩长发,而我正好相反,长发变成了短发。
我激动地问:“安安,你不是在新西兰吗?”
那女孩儿突然低下头去,随即很快高傲地扬起头来。
她拿腔拿调地说:“谁是安安啊,本小姐叫莫安!”
后来我和她互相留了手机号码,当然是瞒着程禾的。
两周后,我告诉了程禾,那晚上我和莫安瞒着他互相留下号码了。程禾没说什么,此人在这方面一贯不与人计较。而我之所以可以放心告诉程禾的原因也在于,我已经和安安坚不可摧地好上了。
而且,在莫安的强烈反对下,愚不可及地试图作为新生活的征兆之一,我从此再也没有碰过大麻。
现场直播的悲剧2
我把被子往莫安身子下面掖了掖,她往我这边缩了缩。
她把骨节分明的手指覆盖在我的肚子上,使劲按了按,然后睁大了眼睛看我的反应。我被这个动作给逗笑了,她那样子仿佛是个淘气的小松鼠的模样。
我喜欢莫安这样子机智的,灵巧的,狡猾的女孩儿,她们偶然流露出来的一点儿自嘲则 更令人心动。
“嗯,那你是怎么认出我来的?”她扬起她的下巴,显得咄咄逼人。
我说:“就是你抽大麻烟之后晕在那儿的时候。”
她那时候已经把外衣脱了,穿着白色的薄纱似的贵族娃娃气的小上衣,下面是不长不短的裙子,她还脱掉了靴子,把脚缩进了裙子里。这个动作,我之前并没见莫安做过,不过我却一下子觉得,只有莫安才会这么干。
她转转眼睛:“那么,吴凡,你爱我吗?”
“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