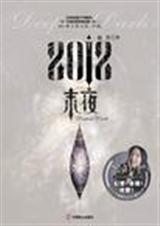1238公里的忧伤-第1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同时我们系被开除了一个大三的,原因是帮他北理工的一哥们儿代考四级,北理工只把 那人劝退,北外反而把他给开除了,哪怕他爸是驻芬兰副大使也没用。此人据说十分了得,当年是全国滑板大赛少年组冠军,以及他的德语系前女友和我一起做过电影社团,其人倒也有些品位,同我关系尚可。我倒多少替那家伙惋惜,于是在某饭局上甩了一句:是倒霉还是幸运,过10年后再来看什么的豪言壮语。
无聊,深刻的无聊,一切都简直是死水一潭,没有任何努力的必要,没有任何值得努力的目标。我现在真这么觉得,哪怕你定性我是无病呻吟也好。
我开始考虑,就已经列举过应对空虚的三种方式而言,目前我过于浮躁,必定没有足够的毅力写作,而社会活动显然在这时候也不合时宜,于是只能选择混姑娘。
我难得去上了一次中国文化概况课,理由是沈寒声称有他觊觎已久的美女出没,虽然只看了丫走路的架势我便对她兴趣全消。
或许是感到内疚,沈寒又向我介绍了一个日语系的,一个北医的,以及一个我先前已经见过的我们学校话剧社的某姑娘。
我在进一步了解了详细资料之后对这三人都丧失了厮混的决心,之一是按照沈寒的说法是一良家妇女配我可惜了,倘若我做出什么负心之举他不知道以后怎么面对人家。之二则是太能玩儿折腾了怕我承受不了,最后一个是我提出先缓缓的,原因是我直觉此人过于事事儿的,事业心过强。
他最后建议说:“有一有钱的哎,我高中同学,她爸是一大学校长,她开一捷达,就快换帕萨特了,就是长得特难看。”
此种近似于拉皮条的举动,最后总是落得自我厌弃,无非是再一次确认自己的无聊和恶俗而已。
我这么想着,我睁开眼睛,听到宿舍外头沈寒,孙左什么的几个人在聊天的动静,几个人扎堆儿在走廊抽烟。我撑起身体,懒洋洋地爬下床。我边拆开一包沙龙烟,一边打着哈欠,打开门,迎着烟雾,恶心,戏谑,真诚,苦闷,怀抱着自我消沉之心,向前,向前。
第二天是周三,中国文化概况考试。
我忘带了学生证,被勒令回去取,无奈之下慢悠悠地再晃下楼道,结果突然听到耳熟的声音,我几乎一下子就辨认了出来,是曲明明。
她站在逆光里,只能看到轮廓,跟一个男的站一块儿,似乎在找考场。
我抬头看了一眼,由于逆光,我没看到她脸上的表情,加之她随即就扭过头去。
在回宿舍拿准考证的路上,想起一年前的轻薄举动。我当时试图磕上曲明明,一度对此人穷追猛打。
结果后来才知道,一哥们告诉了我错误的电话号码,导致我把所有哀婉动人的离骚之情都倾注到了另外一姑娘的身上,这一盲打误撞的严重后果至今玷污了我一向清白的声誉。
我一想起这事儿就觉得够郁闷的。
后来我跟沈寒打赌,两人约了谁要是先能通过短信跟曲明明搭上,对方就在“雕刻时光”请小番茄鞠肉酱意面一盆,附赠Espresso一杯。
后来我和沈寒两头开工,还是我这边进展较快。
等到我约了曲明明去韩国餐厅吃饭之后,不知怎么的,我又失约作罢了。
虽然我一直未曾承认过,我确实挺中意曲明明的。
我第一次见到曲明明是刚进北外在新生注册交费的时候,当时两人都大汗淋漓颇为狼狈。恰巧在排队窗口前挨着。她当时引起我注意的是耳朵上一连串扎着的三四个耳钉,在北京夏末耀眼的阳光下晃得我眼晕。我就多看了几眼,或许是因为其时她心情也正烦躁,没好气地瞪我一眼,甚是凶狠。
也许,我不太情愿地坦白,是几个闪亮的耳钉,立刻就让我想起了莫安。
后来,我总是能在北外校园里轻松地认出她来,她脸庞轮廓鲜明刚硬,总令我想起迎风而上的硬帆。她的发色在阳光呈现酒红色,恍若燃烧的火焰,双眸明亮,总在上课的时候对着镜子模拟着种种表情搔首弄姿。她那年穿彩色镂空毛线小背心露出里面的白色抹胸,修长的两侧以皮绳衔接的牛仔裤,把男生们都快勾引疯了。
这天晚上,我又生发出自轻自贱之心,然而再跟曲明明聊短信令我更为郁闷,而且莫名其妙,举例说明如下:
我说:“我搬家了,就在学校后头的魏公村小区,这两天忙着买家具和装饰。不知道以后能否见到你。”
她回复:“你是谁?”
当晚,其后我在毫不掩饰的狂躁不安中套了件亚麻衬衫便出了门,跟几个同学去吃了烧烤,冰天寒地地回来,然后百无聊赖地看宿舍里头一伙人对练CS和星际争霸。
过了一会儿,她回一条短信:“想你了。”
我顿时如坠入五里云雾,心想这是哪儿跟哪儿啊。
无奈当时我心地已经恢复到比较淳良的状态,装傻充愣地回了一句“发错了吧?”
第二天晚上,我正乖乖爬上床准备安眠,突发奇想,还是给她发了条短信道声晚安。
早上,我接到短信说,“都这么久了,其实有时我也挺想你的。”
其后我又发过她几次短信,都如石沉大海,了无音讯。
老实说,我确实没搞明白曲明明的逻辑,或者说这其中产生的误会,这段心血来潮也就暂时告一段落。
现在出于无聊,想起曲明明来,我没拿好主意,是否要再约一次她。
每当身处写作的低潮时期,整个小时整个小时地枯坐对着电脑屏幕仍然憋不出一个字的时候,我总是萌生出见曲明明的念头。
我联系问她:“说你在干吗呢?”
她说:“在深圳。”
这不是还没最后放假吗?我心里纳闷,我在这头听得电话里人声嘈杂,便问:“是在逛街吗?”
她说:“是啊,我一个人逛呢,待会儿他来陪我吃晚饭,可我已经饿得快吐了。”
我被这个说法给逗乐了,接着她告诉我说她刚才进了西武百货。
“那又如何?”我问道。
“我算是知道什么是名牌了,”她谄媚地说道,我似乎看到曲明明两眼放光无限神往的模样,“我居然有胆子进去,真了不起。”她补充道。
我笑起来说,“你将来傍个巨款不就什么都有了?”
她说,“好。”
我又补充到,“然后再发我个富婆,咱也傍一傍,我好少奋斗10年。”
“必然,”肯定道,我仿佛见到她颔首赞许的动作,“我一定把他女儿介绍给你,估计年纪比你就稍微大点儿而已。”
我开始没反应过来,后来才开口骂了一句:“操,瞧你这辈分排的,咱们都能演一21世纪版本的《雷雨》。”
“哈哈,好。”曲明明笑起来,随即说,“他来了,挂了,回头再联系。”
后来,又聊过一次。
“生活老是在弓虽。女干我!”她可怜兮兮地说。
“不能反抗就享受。”我说。
“它太丑了。”
我慨然道:“那就蒙上眼睛吧。”
“性生活不协调,他满足不了我。”
“那就不妨偶尔自慰,或者搞搞外遇。”我建议道。
“不和你聊了,我会怀孕的。”她笑道,挂了电话。
我会一直在你身边3
“这日子没法过了。”
我跟程禾大倒苦水,说:“哥们儿现在荒得都不成体统了,谁有漂亮姑娘,发我一个吧。”
程禾说,“别啊,不是我不照顾你,可是,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啊!”
鉴于程禾的各方面条件,说丫是地主我信,至于没有余粮,我有理由怀疑他是在蒙我。
我撂下一句:“这话摆出去谁要信了,丫脑子就是被开水烫过了。再说了,我也不跟你高标准,你不发大白米,也掰点儿高梁面儿吧,哥们儿这儿都断顿了。”
“哎呦,谁让你有了莫安就甩了顾婕,也不留着备用?”程禾抱怨道,“哥们儿最近心酸着呢,一姑娘正跟我这儿闹着呢,待会儿再联系你。”说着就闭了电话。
我倒确实听到有女孩儿高声说话的动静,似乎是不怎么和睦,程禾这人在勾引姑娘方面实在是令我感到自卑。
关于他的段子颇多,简直令人叹为观止。
其人的一大特点也是他能勾到姑娘的一大原因是,无耻。奇妙之处在于,别人无耻让人觉得丑恶,程禾无耻起来就偏偏令人觉得饶有趣味。
就说最近首都高校配音比赛那次,本来该是广院的实力最强,可我们的段落从《海底总动员》里面选,比较出彩,就拿了个意外的第一。
后来在后街搓饭局庆贺,大家都挺高兴,喝得过火了一点儿,都有些醉了。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大家开始交流有意思的手机短信,一个女孩儿念了一条是,小猪听说幸福就在自己的尾巴上,于是就拼命去咬自己的尾巴却总是抓不住,然后又有人骂丫傻,告诉丫说只要一直往前走,幸福就会永远地跟着你。
那女孩儿大概是觉得这段子编得还挺高明的,程禾跟她原本关系就挺不错的,而且最近似乎颇有跟她上劲儿的念头。
程禾就接腔道:“那找两只猪,互相对咬不就行啦?所以,这日子还得两个人一块儿过,是不是?”
结果那女孩儿可能将这个视为某种暗示,朝程禾投去颇为甜蜜的一瞥。我见状,朝程禾偷乐,他也报以会心一笑。后来那姑娘去了洗手间。程禾也过去了,我估计有戏发生,便找个理由偷跟过去,果然在过道的一个小凹门边上瞧见他俩。
几句打情骂俏之后,程禾把手摸向那姑娘背后,腰部,接着是牛仔裤臀部的位置。
那姑娘似乎觉得尴尬,扭捏地问程禾一句:“你干吗呢?”
程禾大言不惭:“按你说的啊,我这不是正努力摸索着,寻找幸福嘛。”
我在外头听了,朝一桌子人转述,把大伙儿都逗乐了。
后来,程禾同那姑娘出双入对逐渐成为惯常的风景,再后来,就不怎么一起在我们的视野内出现了,两人的接头暗号简单得就是发过来的一串号码,某某宾馆的某某房间号。
其实,这种事儿,要是做到程禾这份上,也就挺无聊了,当然,我这是嫉妒之言。
我会一直在你身边4
程禾对我无心的一句话,又让我想起了顾婕。
或许是由于数次勾搭姑娘不成,以至于有些形单影只的缘故,我现在的情绪,无可救药,显得有些小资产阶级的多愁善感。
重归学校上学之前,还是暑假里头,那天早上,我记得清楚,她过来我家的。由于那天 台里的活儿似乎挺忙,她心情也显得不甚高昂。在我房间里做了一次,也不太有意思,后来两人傻愣着陷在客厅的沙发里看碟,看了一会儿“九寸钉”(“nine inch nail”)的演唱会,把韦伯的《猫》剩下的部分给看完了。
最后,那天上午我从头到尾完整看的是基耶斯洛夫斯基的《永无休止》。
我喜欢短命的基耶斯洛夫斯基,尽管他太理性,又过于温情脉脉,以至于走向一种虚无主义,虚无主义,教世界宗教学的老师如此评价我的论文。
值得一说的是,那天她穿着一件彩色横条的T恤,后来我才知道那居然是她自己手工做的。
据说原因是,我也有一件同样款型的衣服。
当时我就蒙了,只好打趣说,那咱们以后不妨去拍蜘蛛双侠。
后来我爸回来了,带了盒饭几个人吃,然后我俩就不知道该干吗好了。
“好困。”她抱怨道。
“谁要是上网到两三点,早上六点起床去爬山,然后再上班都会困的。”我有点儿揶揄她自作自受。
“爸妈把我给拖起来的。”她辩解道。
其实我不太能清楚地表述自己那天的表现是出于什么,或许是因为《永无休止》那电影,我产生了一种自暴自弃的决心和勇气。
我对顾婕说:“咱们还是去那宾馆吧。”
她不太愿意,我看得出来,究竟是出于什么原因的,我就不大明白了。
她很勉强地说,:“小凡,我不习惯那么直白地表达,我也不希望我们之间就是那么一种关系,有时候我在怀疑,你是不是只是在需要我的身体。”
我说:“怎么会,顾婕,你别瞎想。” 我心里在想:废话,我还一直觉得你觉悟挺高的呢。
两人之间沉闷了一会儿。
她说:“走吧。”
下楼,打车,开房,进了那种熟悉的丑陋套间,我突然没有了莋爱的兴致。
我对顾婕说:“你困了吧,睡会儿吧。”
她点头道:“嗯,你呢?”
我说:“我带了电脑,有个提纲我打算编编看。”
我给她铺好床,把被子从柜子里拿出来。空调温度开得很低,然后她也没脱衣服就睡了,似乎很快就进入睡眠。
我打开笔记本电脑,接上电源,长舒一口气,身子陷在那种司空见惯的摆在窗前的廉价沙发扶手椅子里,双腿搁上床沿,开始写作。
也许是那天房间里幽静的气氛很好,加之我总是喜欢在陌生的,似乎被人所遗忘的角落里写作,那样总是令我心情平静,我写得很顺利。
开始,透过窗帘的缝隙进来的阳光只是照射在我的双膝上。等劈里啪啦敲打键盘的声音停息下来,我踮着脚去倒了一玻璃杯的水来喝,再摆回原来的姿势时,才发觉阳光已经照在脚趾尖上了。
光阴逝去,如此悄无声息,我哑然失笑。
或许是写作顺利的缘故,我心情尤佳,我爬上床,看顾婕呼呼睡去的模样。
她闭着眼睛,细而温柔的留海落在眸间,我把那些发丝轻轻拂去,结果她就醒了。
她说,“小凡,怎么了?”
我说,“没什么,挺好的,你继续睡吧。”
她说,“做梦了。”
“哦。”
“想抱抱你。”她说。
我抱住了她,自然而然地便开始莋爱,那次顾婕表现得颇为热烈,两人感觉似乎都不错。
把窗帘完全拉严实了,只有几缕细细的光线,房间里一片黑暗,我盯着那几道金黄色的丝线看,甚是满足。它们划过这空间,如同蛛网,我开始想像自己是否象一只蜘蛛,在那贫乏的几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