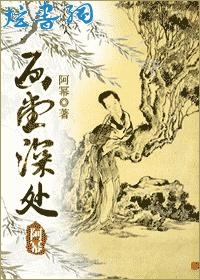画堂韶光艳 作者:欣欣向荣-第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计量做买卖
珍珠是前两年买进府的,进府时也不过才十四,模样儿也着实不算多出挑,倒是难为性子伶俐,爷们过来的时候,她近前伺候,说话儿,被爷瞧上,去年收用了,虽没个正经名份,玉芳看待的,也不一般,虽说是伺候她的,平时的活计极少指派她,只让她端茶递水,或是收拾床褥等事,衣裳也与她做了几身鲜亮的,首饰拣着好的赏了几件给她,打扮起来,怎还与那些丫头一样,加上爷前头也颇喜她,越发成了个不省事的性子,毕竟年轻,不知轻重,在顾家宅门里,以往老太爷活着的时节,爷荒唐胡为,也无人敢说半个不字,更何况如今,爷还不说什么是什么,谁敢拦他,不定寻个没脸的下场。
况这事说来说去,也轮不上她一个丫头出头去理论,她凭什么,说到底,她不也是钻了爷的被窝,才有了今日,如今倒来气不愤儿了,那徐大姐儿顶着童养媳妇的名头,让爷甘心收了她,这份手段,哪里还是往日那个木呆的人儿,她去了岂不自寻烦恼,本说喝住她便罢了,谁知倒惹她这么一通难听的话说出来。
玉芳脸儿一酸,道:“你真这样厉害,刚头爷在的时候,怎么一声不吭,我也犯不着拽着你,却去寻徐大姐儿做什么,不如跟着爷的脚儿去,若有手段让爷改了主意,我便真服了你。”
几句话说的珍珠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半晌儿说不出话来,玉芳见她那样儿,语气略缓道:“爷如今正在新鲜头上,你去寻她吵闹,不是自找苦吃,听我一句话,各自消停些要紧。”说完扭身进了屋里。
坐在炕边上心里却也暗叹,她是丫头起家,身后没个娘家撑着,更比不得年轻丫头们,一身招爷稀罕的皮肉,膝下也无子嗣,她敢说什么,爷那个脾性,便是如今这些年熬过来,爷说恼上来,抬脚就踢,举手便打,哪得什么体面,巴望着过几天顺心日子,比什么不强,虽心里这么想着,爷今儿这档子事也实在荒唐的过了,府里多少丫头,便是府里没有的,外头院中也有,再不济,人牙子手里寻几个标致模样儿的还不容易,怎就非巴巴的瞧上了徐大姐儿,这若传出去,也不怕人家戳脊梁骨,只她人微言轻,说什么也没用。
不说玉芳在这里暗暗气恼,再说顾程,从玉芳院里出来直接去了慧莲那边,跟慧莲一说,慧莲倒想起那日晨起之事,过后徐大姐儿就上了吊,这前后联起来,慧莲什么不明白,心里虽也觉这事儿荒唐,可也明白,如今到了这家业,谁能拦得住他,横竖也没纳进来,依着爷的性子,不定过些日子就丢开了,到那时再寻个由头,远远发卖出去也便是了。
这么拿了主意,便道:“爷想要个侍墨丫头罢了,什么大事儿,巴巴的还跟奴家说,让外头的人知道,还道奴家连丫头都容不得呢。”
顾程一瞧她应的痛快,心里欢喜上来,道:“那回头我让她过来给你两个见礼,只那丫头如今改了性情,倘若说话儿不妨头,你莫怪她才是,横竖还小,待我日后慢慢教她。”
慧莲听了,心里暗道,可见是心里中意,这还没怎样呢,就护在手里了,还小?哪里小了,虽说早先是廉哥儿屋里的人,算着今年,可不都十八了,倒也不能让那丫头太过如意了,嘴里便道:“只她也未读过书,大字不识一个,怎样伺候笔墨,便是爷现教,也来不及的,倒不如唤了人牙子来,再买上一个,会写字唱曲儿的丫头,在书房里轮换着伺候,岂不好。”
顾程听了,心里头暗道,徐大姐儿那样儿,瞧着真不是个能伺候人的主儿,跟个姑奶奶差不离,虽有小厮,也不得使唤,再添一个丫头也好,便应道:“这些事你跟玉芳商议着吧!挑了人送去我过过眼,识字唱曲儿的会不会不打紧,倒是要个手脚勤快些的才好。”
慧莲听了怔了怔,心话儿说,书房里伺候的,要手脚勤快的做什么,正说着,忽的外头旺儿传话进来道:“前头尹二爷来了,说有事寻爷呢。”
这位尹二爷却是这信都县县太爷的公子,尹仲华,因排行第二,外头都称一声二爷,今年才刚过二十,也是个不喜读书功名的闲散子弟,虽娶妻生子,手头上却不多宽裕,靠着他爹,赚些帮事的银钱使唤,跟顾程几个常在一处吃酒,故相熟,若论起交情来,倒也说不上多好,老太爷的丧事中,他倒是也送了奠仪过来,况,看着他爹的面子,顾程也不能怠慢了他去。忙起身到了前头,彼此见礼,让到厅中落座叙话。
话说这尹仲华,今儿来顾府也是真有事儿,俗话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他家也一样,他爹虽任了这信都县的父母官,却着实没捞到什么油水,虽为官数载,却也未积攒下多少家俬,况他上头还个大哥呢,便是那点儿家俬,也没他什么事儿,虽算个官家公子,手头却着实不宽裕,常愁无银钱使,恨不能哪里得笔横财来才好。
这么惦记着,就来了运气,话说这信都县城南原有一家当铺,临着旁侧花街,多有来典当东西物件寻biao子吃花酒的,倒做的好买卖,那当铺的东家姓刘,有个儿子,叫刘生财,却是个性好吃酒的不孝子,常吃的大醉惹出事来,为此他爹不知赔了多少银钱进去。
前些日子也不知怎的,在酒肆中吃醉了酒,为了个唱曲儿的粉头,跟一个外乡的汉子,起了口角动起手来,却不想遇上可歌硬岔口,三拳两脚把他打下楼去,滚落在当街上,两眼一翻,一命呜呼了。
那刘老头空有赚银钱的营生,却绝了后,发送了儿子,赌咒发誓的要为儿子报仇,告到衙门里,因那厮是个外乡人,打死人后,不知窜逃在何处,哪里寻影儿,他却自认是使的银钱不够,寻到了尹仲华门上。
尹仲华闻听他有意典当了铺子回老家去,暗道造化,可不是个现成发财的路,便跟那刘老头透了意思过去,那刘老头言道:“只报了仇,这当铺子连铺面带里头的东西,给上三百两银子便成。”
这尹仲华听了,心下暗喜,先开头本有意自己做这桩买卖,却又一想这三百两银子,他去哪里寻来,倒不如当个中人,得些便宜财,倒拎清,这才想起顾程来。
程大户不亏他的名儿,是这信都县里数得着的大户人家,县外头的田地有一半都是他家的,后归在顾程手里,虽一辈子吃喝花用不尽,往常吃酒,却也听他有意做桩买卖营生,这铺子给了他,岂不两下便宜,这才寻上门来。
他把这话跟顾程一说,顾程心下也活动起来,想他手里虽有田地家俬,却是祖产,不是他手里赚的,算不得他的本事能耐,再说,这田地收租虽稳妥,却要靠老天爷吃饭,赶上旱涝灾荒,一样没个进项,况他早就有意做买卖,只苦无适当营生罢了,这会儿听了尹仲华的主意,哪有不心动的理儿,却又道:“那刘老头虽如此说,却要先寻到他儿子的仇家,听说是个外乡的蛮子,如今却去哪里寻影儿,可不都是空话。”
尹仲华却呵呵笑道:“若无把握,弟也不来扰哥的清闲了。”顾程忙道:“可是寻到了不成?”
尹仲华低声道:“实话说与哥,那厮如今正在府衙大牢里压着呢,也是赶巧了,该当他背运,这厮却是个为色不要命的主儿,在咱们县里伤了人命,逃到真定府去,听说冯家姑娘生的标致,夜里当了飞贼,翻进冯家院墙内,惦记着奸那冯家的姑娘,不想被家丁拿住,扭送了衙门,那真定府的府台大人跟我爹是同年,颇有些交情,弟才知这些底细,可不白捡了个便宜吗。”
顾程听了,暗道这样的便宜他既得了,还来寻自己作甚?转念又一想,这尹仲华虽说是个官家子弟,手上却无什么银钱使唤,不说三百两,让他一下子拿出三十两来,恐也难,这是打了主意,让自己出这个本钱来了,虽有意,却又想这合伙的买卖干不得,他爹又是县太爷,倘若将来有个什么纷争,自己哪里能得便宜去,没得被这厮坑了,他可不干这样的傻事。
想到此,却笑道:“虽是桩好买卖,奈何老太爷刚去,一时半会儿的,也无此等心思……”寻了许多借口搪塞,却不妨尹仲华是个听弦歌知雅意的灵透人儿,听出顾程的话音儿,便笑道:“哥说哪里话来,如今可都过了五七,还有什么事让哥操持的,正好得这个营生做做,虽是好营生,奈何弟寻不住这些本钱,便是有这些本钱,也没哥的本事能耐,弟是见这桩买卖舍了可惜,才来寻哥的意思,若哥有意,典下他的铺子,日后赚得银钱,提携弟多吃几顿酒,也就是了。”
顾程这会儿才算明白过来,这尹仲华不是想跟他搭伙做买卖,是想从中得些好处银钱罢了,如此,这桩营生倒可一试。
想到此,扭头吩咐旺儿一句,不大会儿功夫,旺儿从后头捧出一个匣子,顾程递给尹仲华道:“这里头有四百两银票,弟先拿去,待典下铺子,哥另有重谢。”
作者有话要说:今天出去吃饭,现言明儿双更啦!!!
☆、喜退方知愁
尹仲华见顾程这事办得亮堂,心里暗暗欢喜,面上却也假意推辞道:“说好三百两,哥怎给这许多?”
顾程笑道:“弟莫推辞,想你上下奔波,不定搭了多少人情官司,哥也没旁的情儿可补,剩下的一百两,你拿去打点衙门上下人等,日后短不了有事求上去,有个人情,也好说话儿。”尹仲华这才收了。
眼瞅到了饭时,顾程让人备办了酒食饭菜,两人吃了一晌午酒,才送了他出去,回来书房,顾程却忽地想起旧年一桩事来。
那年廉哥儿落生的时节,玉皇庙的老道来批八字,因说廉哥儿犯了星象恐有灾厄,这才寻了个八字旺的徐大姐儿买将进来,挡灾,廉哥儿夭折后,顾程本都快忘了此事,不知今儿怎就想了起来。
暗道这徐大姐儿果然是个八字旺有福运的丫头,这么瞄着还真有些影儿,自己这才刚说把她收到身边来,这不,就从天上掉下来一桩好营生,改日寻那老道再给她掐算掐算,说不定是个旺夫旺子的命数。
又想起那丫头枕上风情,虽说有些别扭爱使唤小性儿,却也别有股子销魂之处,竟让他舍不下丢不开的,思及此,心里不禁痒痒起来,这么想着哪里还坐的住,起身出了书房,往廉哥儿院里去了。
旺儿在后头跟着,心里暗道这人真是要讲运气,你说之前徐大姐儿那么不得爷待见,怎么一转眼的功夫,就稀罕成这样了,早起才从这儿出去,这会儿又巴巴的寻了来,这会儿可刚过了午晌儿。
顾程到了跟前,却见院门紧紧闭着,他上前推了推,里头上着门闩呢,想起昨夜翻墙过去窃玉偷香的行径,不禁低笑了两声,仍让旺儿搬了个板凳过来,跟昨儿一般,翻墙跳了过去。
一跳过去,就看见那边葡萄架下,不不知何时挪了一张凉榻出来,徐大姐儿侧身躺在上头,想是刚洗过澡在哪里晾头发呢,一捧乌黑发亮的青丝拖在脑后,搭与凉榻边上,发梢从凉榻上垂落下来,一阵风过,荡啊荡的,真好似要荡到顾程的心里去一般。
如今这还未入夏呢,她倒如此怕热,身上只穿了件白衫儿蓝裙儿,脚上的绣鞋褪下,却套着一双鲜亮的大红绫纱袜儿,裹住芊芊玉足,缩与裙下,好不让人稀罕,脸上盖着一方旧帕子,自己翻进来,都没动一下,想是睡着了。
顾程蹑手蹑脚走将过去,到了跟前弯腰,把她脚上的红菱纱袜儿褪下来,顺手塞在自己袖中,把她一对玉白小脚握在手心揉搓。
徐苒昨儿被顾程折腾了一宿,哪还有什么体力,顾程走后,也提不起劲儿洗澡,草草吃了早上饭,就躺在炕上补眠,到了晌午,屋里闷热上来,热的她出了一身燥汗,才起来,吃了晌午饭,见灶上的大锅里还温着水,就闭了院门,在灶房里洗了个澡,不想回自己的那个热死人的小屋,到了正房屋里溜达一圈,瞧中了窗前的凉榻,费了些力气才挪出来,就放在葡萄架下的石墩旁边,她躺在上头边晾晒头发,边睡午觉正美呢,忽觉脚痒的不行,倒似有什么东西挠她的脚心一样,眼睛没睁开呢,一脚就踹了过去。
顾程哪里想到她睡觉还如此不老实,没防备,被她一脚正踹在胸口上,若搁旁人,这一下子不定要怎样倒霉了,奈何这会儿顾程正在热乎头上,挨了徐大姐儿一脚,不禁没恼,反而呵呵低笑一声道:“好个丫头,这一脚倒踹的爷心口窝生疼,既有这些力气,昨儿夜里怎不见你跟爷使,是想着留到今儿晚上施展吗?”
徐苒睁开眼,才发现是这老色鬼,暗暗翻了个白眼,心话儿早知是你,越发要使尽全身力气,最好一脚踹死你,也省得留着祸害别人,嘴里却道:“人家好好睡着,你来摸人家的脚做什么?这等无赖行径,挨一脚也活该。”那样儿说多刁就多刁,竟是半点儿惧怕也无。
顾程可不就喜欢她这如今这扎手的模样儿,瞧在眼里更多添了几分娇俏风流,馋虫勾上来,身子一歪,坐在凉榻边上,把她两只小脚在手里揉搓半晌儿,调笑道:“如今可还没入夏呢,刚洗了澡就在风口里躺着,回头着了寒凉怎生好,让爷先来摸摸,身上可凉了……”说着,大手不怀好意的伸过去,顺着徐苒裙下的裤儿腿儿,一点一点儿往上摸。
徐苒不禁暗叹,谁说古人保守来着,这男人简直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色胚,腿一缩一踢,把他的咸猪手甩脱,却寻不见了自己新做好的一双袜子,那薄纱料子做的袜子穿着虽舒服,却有一样不好,便是易滑脱,四下里找了半天,没找见,忽见顾程袖子边上露出一个边儿来,不禁白了他一眼,伸手去拽,被顾程一把按住,亲了下嘴道:“这袜儿做的巧,给了爷吧!全当个情儿意。”
徐苒推开他道:“你要这个做什?难道也讨去穿在脚上不成?”顾程笑道:“好个促狭的坏丫头,爷穿这个出去,岂不成了那小倌里的相公了,爷是瞧着你穿的好看,回头出去寻好的针线铺子,比着你的脚样儿,多做些几双,好睡觉时穿,也省得晾了脚心,生得病症,女孩儿家的身子娇弱,可不都在脚上呢,脚护好了,身子自然就强健了。”
徐苒忍不住噗嗤一声笑道:“原来你到是半个郎中。”“郎中不郎中的不打紧,这会儿让爷好生亲近亲近才是……”说着又凑过去,在她身上胡乱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