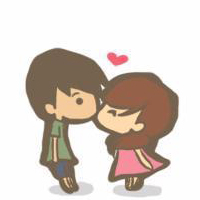雌性的草地_严歌苓-第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内容简介
《雌性的草地》介绍了在文革动乱的年代,一群年轻的姑娘被放置在中国西北荒凉的大草原上,她们在这个神圣而又庄严——“女子牧马班”——的集体中,在恶劣的草原气候和环境下牧养军马。故事从小点儿这个有乱伦、偷窃、凶杀行为的少女混入女子牧马班开始,以小点儿的观察角度来表现这个女修士般的集体。这个集体被荒诞的人性和庄严的神性所扼杀,年轻的肉体与灵魂作为牺牲,奉上了所谓“理想”的祭坛;而这“理想”,最终被认清为罪恶。
从雌性出发(代自序)
有的朋友对我说,《雌性的草地》有点昆德拉(MiLanKundera)的影子;也有人说它像玛格丽特·杜拉斯(MargueriteDuras);我来到美国后,一位懂中文的美国文学青年说,这部小说让他想起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我不知道。也不知与这些成功的老辈们有相似的嫌疑是好事还是坏事,人们是贬我还是褒我。
还有朋友告诉我:你这本书太不买读者的账,一点也不让读者感到亲切,一副冷面孔——开始讲故事啦,你听懂也罢,听不懂活该,或者你越听得糊涂我越得意,这样一个作家,读者也不来买你的账。
记得我的朋友陈冲读完《雌性的草地》后对我说:“很性感!”我说:“啊?!”她说:“那股激情啊!”我一向很在意陈冲的意见,她是个酷爱读书的人,读过许多好书,尤其当代西方文学,似乎是读书余暇中去做做电影明星。“真的,你写得很性感!”我仍瞠目,问她性感当什么讲,她说她也讲不清:“有的书是写性的,但毫不性感;你这本书却非常性感。”她说。
我是认真写“性”的,从“雌性”的立场去反映“性”这个现象。我认为能写好性的作家是最懂爱情、人性,最坦诚、最哲思的。比如昆德拉、玛格丽特·杜拉斯、D·H·劳伦斯,包括托马斯·曼(死于威尼斯)。仔细想想,性爱难道不是宇宙间一切关系的根本?性当中包括理想、美学、哲学、政治、一切。
当然,写性并不是我写这部小说的原始动机,最初让我产生写它的冲动是在一九七四年,我十六岁的时候,那时我随军队的歌舞团到了川、藏、陕、甘交界的一片大草地去演出,听说了一个“女子牧马班”的事迹。第二年,我和另外两个年长的搞舞蹈创作的同事找到了这个牧马班,想创作一个有关女孩子牧养军马的舞剧。这些女孩子们都是成都的知识青年,最大的也才二十岁。这块草地的自然环境是严酷的,每年只有三天的无霜期,不是暴日就是暴风,女孩子们的脸全部结了层伤疤似的硬痂。她们和几百匹军马为伴,抵抗草原上各种各样的危险:狼群、豺狗、土著的游牧男人。她们帐篷的门是一块棉被,夜间为防止野兽或男性的潜越,她们在棉被后面放一垛黑荆棘。她们的生活方式非常奇特(小说中我如实描写了她们的炊事、浴洗、厕所等),让一个如我这样的女兵也觉得无法适应,或根本活不下去。她们和天、地、畜、兽之间的关系都十分奇特,去想像一下:把一伙最美丽最柔弱的东西——年轻女孩放在地老天荒、与人烟隔绝的地方,她们与周围一切的关系怎么可能不戏剧性呢?在我们住进她们营帐的第二周,来了个男人。这就是书中的指导员叔叔。叔叔是个藏人,或是羌人。叔叔是他的名和姓,不是辈分。叔叔看见我们几个女军人就显出一种奇怪的敌意,我琢磨他是嫉妒我们,因为我们在这群女孩和外部世界之间牵了一丝联系,否则她们都得仰仗他去和社会、人间取得沟通。他每隔两周或三周到女孩们的帐篷走一趟,送些一月前的报纸、家信和食品。他长相极英武,气质雄浑,有颗雄狮般的大头。他穿一身五十年代的军服,又脏又破,骑马飞快,打枪贼准。不知是出于好客还是示威,他当我们面击毙了在远处草丛里跑的一只野兔,又当我们的面剥了兔皮,整套动作像脱袜子一样轻松麻利。那是只哺乳的母兔,当皮剥到胸腹部时,两排乳汁如微型高压水龙头一样喷射出来。这使女孩子们的生活基调又添加了一层残酷、恐怖的色彩。
多年后,我们听说那个指导员叔叔把牧马班里的每个女孩都诱奸了。这是对女孩们的青春萌动残酷、恐怖,却又是唯一合理的解决。
“女子牧马班”的事迹在一九七六年成为全国知识青年的优秀典型,报纸上大幅地登出她们饱经风霜的年轻老脸,记者们管她们叫“红色种子”、“理想之花”。当时我感到她们的存在不很真实,像是一个放在“理想”这个培养皿里的活细胞;似乎人们并不拿她们的生命当回事,她们所受的肉体、情感之苦都不在话下,只要完成一个试验。
这个试验以失败告终。“性”毁掉了这个一度荣耀的集体。失败告诉我们:人性、雌性、性爱都是不容被否定的。
明显的,这部小说的手法是表现,而不是再现,是形而上,而不是形而下的。从结构上,我做了很大胆的探索:在故事正叙中,我将情绪的特别叙述肢解下来,再用电影的特写镜头,把这段情绪若干倍放大、夸张,使不断向前发展的故事总给你一些惊心动魄的停顿,这些停顿使你的眼睛和感觉受到比故事本身强烈许多的刺激。比如,在故事正叙中,我写到某人物一个异常眼神,表示他看见了什么异常事物,但我并不停下故事的主体叙述来对他的所见所感做焦点叙述,我似乎有意忽略掉主体叙述中重要的一笔。而在下一个新的章节中,我把被忽略的这段酣畅淋漓地描写出来,做一个独立的段落。这类段落多属于情绪描写,与情节并无太多干涉。这样,故事的宏观叙述中便出现了一个个被浓墨重彩地展示的微观,每个微观表现都是一个窥口,读者由此可窥进故事深部,或者故事的剖切面。
当然,我不敢背叛写人物命运的小说传统。我写的还是一群女孩,尤其是主人翁小点儿,次主人翁沈红霞、柯丹、叔叔的命运。故事是从小点儿这个有乱伦、偷窃、凶杀行为的少女混入女子牧马班开始的。主要以小点儿的观察角度来表现这个女修士般的集体。这个集体从人性的层面看是荒诞的,从神性的层面却是庄严的。小点儿终于在这荒诞的庄严中涤去了自己生命中的污渍,以死达到了净化;而同样是这份荒诞的庄严扼杀了全部女孩,将她们年轻的肉体与灵魂作为牺牲,捧上了理想的祭坛。因此这份庄严而荒诞的理想便最终被认清为罪恶。
小点儿是一个美丽、淫邪的女性,同时又是个最完整的人性,她改邪归正的过程恰恰是她渐渐与她那可爱的人性,那迷人的缺陷相脱离的过程。她圣洁了,而她却不再人性。这条命运线诠释了书中许多生命的命运——要成为一匹优秀军马,就得去掉马性;要成为一条杰出的狗,就得灭除狗性;要做一个忠实的女修士,就得扼杀女性。一切生命的“性”都是理想准则的对立面。“性”被消灭,生命才得以纯粹。这似乎是一个残酷而圆满的逻辑,起码在那个年代。
写此书,我似乎为了伸张“性”。似乎该以血滴泪滴将一个巨大的性写在天宇上。
以此书,我也企图在人的性爱与动物的性爱中找到一点共同,那就是,性爱是毁灭,更是永生。
A卷 (上)
假如说以后的一切都是这个披军雨衣的女子引起的,你可别信。正像有人说,草地日渐贫乏归咎母牲口,它们繁衍生养没个够,活活把草地给吃穷了,你可别信。
到处有人讲这女子的坏话,你可别信。正像她说她自己刚满十六岁,是个处女,这话你千万别信。你要信了,就等于相信这枚雪白的头盖骨确实空空荡荡,里面并没有满满地盛着灵魂。
披军雨衣的女子停住,用脚拨弄一下,她不知道它是三十多年前的青春遗迹,它是一个永远十七岁的女红军。它在她眼里只是一枚白骨,她怎么也不会想到,它将间接地干预她的人格,间接地更新她卑劣的人生。
女子继续向前走。唯有流浪能使她自主和产生一种不三不四的自尊。从她走进这片草地,她的命运就已注定。她注定要用自己的身体筑起两个男人的坟墓;她注定要玩尽一切情爱勾当,在丧尽廉耻之后,怀抱一颗真正的童贞去死。
她宽大的军雨衣下摆把没胫的草扫得如搅水般响。老鼠被惊动了;一只鹞鹰不远不近地相跟着她。鹞的经验使它总这样跟踪偶尔步行进入草地的人;被脚步惊起的老鼠使它每次俯冲都不徒劳。浓密的草被她踏开,又在她身后飞快封死。
直到身后响起马的喘息,她才慌慌张张地开始辨别方向。
骑马人颧骨高耸,紫红发亮。有这样一对触目的颧骨,脸便坎坷了许多,添出一分英气,二分正气,三分杀气。他直奔披军雨衣的女子,抄到她前面挡了路。女子知道,尽管草地大得随处是路,但她的路必须从他手里讨出来。大太阳刚生出半个,稠糊糊的光正淹过她的头顶。他头发直竖并同马一样汗气如烟。
“往哪走?”他挪动身子,让出半只鞍。这意思是让她乖乖上马,然后一切又循老路。他拍拍鞍垫:“逛够了,回去吧。碰没碰到狼?”
她又干了一次。这样的深夜出走早已是失效的威胁。他有时也乐得放她一缰,为了使她更明白,偌大世界,唯一可投奔的,只有他瘦骨嶙峋的怀抱。
女子裹一下雨衣,把自己缩小。“这回我没拿你们的钱。”她忽然说,露出点泼劲儿。女子除下军雨衣的帽子,现在她的脸正对你。我猜你被这张美丽怪异的面容慑住了。你要见过她早先的模样就好了。假如有人说她是个天生成的美人,你可不能信。
男人此刻下马站到她跟前。“莫闹了,小点儿。”他喃喃道,“我没法,你也没法……”
小点儿看着他的下巴,看着他不讲话仍在升降的喉结。她突然想起这个跟她缠不清的男人实际上是她姑父。她试着喊了声“姑父”,感到这称呼特别涩嘴。
他莫名其妙盯她一阵,一下也想起她原是他的侄女。“那我走啦?这回我真没拿你家的钱,回头幺姑会查点搁钱的抽屉。”他伸出一双胳膊,她看出他想干什么,忙又叫:“姑父!”
他知道再也留不住她。他们对自己隐瞒的彼此间的真实关系,被她就此道破。很大很大的草地,一下子就没了她。
于是,这个披军雨衣的女子潜入了草地,背向她的退路,背向她的历史。
很远很远,你就能看见女子牧马班那面旗,草地最掩不住红色。旗插在帐篷顶上,被风鼓起时,帆一样张满力,似要带帐篷去远航。连下了几天雨,被雨冲酥的泥使帐篷每隔两小时起一次锚。旗却没倒过,只不断流淌血浆似的红色。雨下的夜色,四野通亮。马群一齐勾下头,水淋淋地打着喷嚏。清早天一晴,马群开始游动,只见一片婆娑的长鬃。旗在帐篷顶千姿百态地飘,飘得很响。帐篷里的人一时不明白什么声音会这样响。
班长柯丹捋了把糊满泥浆的头发。几天几夜她都在干同一件事,就是不断打捞塌在雨里的帐篷。帐篷一塌,里面的人就像被一网打尽的鱼那样瞎拱。“不要动,不要动!”她喊。“不要拽人家被子!……拽我干啥,滚你的蛋!”“冷啊!”有人哭着说。“我被子打得精湿!”有人说着哭。“拱!拱你妈呀!帐篷一会儿拱漏,浇把你龟儿!”她喉咙和话都越来越粗。渐渐地,吼也制不住她们骚乱哭闹,有双手伸过来,捺住她烦躁的肩膀。
“别吱声,班长,这样哪行?”
“你是哪个?”
“沈红霞。”
其实在她自报姓名之前,柯丹已猜准她。原因是她很难得开口说话。除她之外,柯丹已听熟每个女娃的嗓门,而正是这份陌生,使人对她的声音记得格外牢。正是她的缄默表现出她非同一般的语言才能。
“你说咋办①(注释:四川方言。)?”柯丹问她。她轻轻说了句什么,但谁也没听清。柯丹怀疑她或许什么也没说,她自己却打这儿开始有了主见,她在一刹那间想出一条稳定军心的绝招。果然奏效,马上出现了秩序。柯丹先是大声点名,然后再让她们挨个报数。这下谁都不敢再哭再闹。原是趁着混乱发发牢骚泄泄委屈,一有秩序谁哭谁就暴露。
这种不间断的点名报数持续到雨停天亮,柯丹惊喜地发现六个女知青被井然的秩序列成整整齐齐一排,睡得很有纪律很成队形,一张张脸都被雨水泡大了。帐篷中央有洼水,漂了只圆肚子老鼠。再到外面看看,帐篷早就不在原来的地方了,不知人带走了帐篷还是帐篷带走了人,反正它起码漂移了百把米,原址留着一垛饱吸水分的柴,新鲜得要抽芽长叶似的。她铆紧帐篷,见三个姑娘肿着脸在门口刷牙,没有水,她们用牙刷蘸了牙膏干蹭。
“张红、李红、赵红!”
她们抬起脸。这是三张难以区别又绝不相像的脸。三个人同时咽下牙膏沫,用手背抹抹嘴,她们知道班长反感太讲清洁的人。柯丹很少刷牙,碰到水富裕的时候也刷刷,只是像捅灶眼一样又狠又快。她对个人卫生态度敷衍,只为证明自己虽是少数民族,但在一切文明上她都不逊色于这些女学生。
“你们三个,去看看马!”
“沈红霞已经去喽……”她们说。嘴里一股水果糖味直扑柯丹的脸。自从女知青把这种又甜又香的牙膏带到草地,柯丹便认为刷牙有了一层很实惠的意义。
“人家去招呼马,你们一爬起来就晓得整自己嘴脸!”她劈手夺下一把粉红色牙刷,扔在地上。另外两个姑娘连忙攥着牙刷就跑。
柯丹全名叫柯丹芝玛,七个人当中,独她是土生土长的牧工。军马场领导当着六个女知青的面拍着她又宽又厚的肩膀:柯丹,她们六个就交到你手上啦;又对她们六个说:能不能放好马就看你们跟柯丹学得咋样啦。当时她想,学放马先要学的多了,比如学吃风干的肉,夹生的饭;还得学野地睡觉,露天解手。
她走进帐篷,两个值厨的姑娘正用手指狠命地从地上抠起一块状似胶泥却比泥更黑的胶黏东西。“那是什么?”她问。
“酱油膏。”
答话的叫杜蔚蔚,相貌远远大出年龄,从一开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