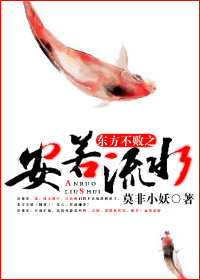流水迢迢-第6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过得数日,卫昭身子逐渐好转,皇帝便有旨意下来,仍命其为光明司指挥使,让姜远将皇宫防务重新交给卫昭。但皇帝体恤他重伤初愈,命他在府休养,只由易五主理防务,一切事宜报回卫府由其定夺。
卫昭也曾数次入宫,但前线战事紧急,宁剑瑜和高成、王朗联手,仍在娄山步步溃败,若非靠着“牛鼻山”的天险,便险些让薄云山攻破娄山。军情如雪片似递来,粮草短缺,皇帝和内阁忙得不可开交,卫昭入宫,总是怏怏而归,皇帝便干脆下旨,让他在府休养,不必再入宫请安。
江慈见卫昭夜夜过来蹭饭吃,不由哀叹自己是厨娘命,以前服侍大闸蟹,现在又是这只没脸猫。心头火起,便不在菜中放盐,或是故意将菜烧焦,卫昭仿若不觉,悠然自得地把饭吃完,喝上一杯茶,再在桃林中走上一阵才出园子。
江慈折腾几日,见无作用,自己便也泄了气,仍旧好饭好菜地伺候着,卫昭依旧静静地吃着,并不多话。
这夜卫昭饮完茶,在木屋门口站了片刻,忽道:“走走吧。”
江慈不明他的意思,见他往桃林走去,犹豫片刻跟了上去。
春风吹鼓着卫昭的宽袍大袖,他在桃林中走着,宛若白云悠然飘过。江慈跟在他的身后,听着细碎的脚步声,感受着这份春夜的静谧与芬芳,仿若回到了邓家寨,飘浮了半年多的心,在这一刻,慢慢沉静下来。
她凝望着夜色中的桃花,忽然觉得,这一刻,竟是自去岁长风山庄陷入漩涡之后,最为平静轻松的时刻。曾几何时,自己是那样渴望远离邓家寨,到江湖上闯荡历险,可真的经历这重重风波之后,发现自己心底里最想要的,却还是这一份宁静―――
卫昭停住脚步,转头见江慈若有所思,神情静美安然,不由微笑:“又想家了?”
“嗯。”江慈慢慢走着,伸手抚上身侧的桃花,轻声道:“我家后山,到了春天,桃花开得和这里一般美。我和师姐,会将落下来的桃花收集,然后酿‘桃花酒’。”
“你还会酿酒?”
“也不难,和你们月落的‘红梅酒’差不多,就是放了些干制的桃花,少了一份辛辣,多了些清香。”
卫昭转身,望向西北天际,夜色昏暗,大团浓云将弦月遮住,他眉目间也似笼上了一层阴影,但瞬间又复于平静。
夜风忽盛,二人静静立于桃林中,都不再说话。
风,凉意渐浓,也将数瓣桃花卷上卫昭肩头。江慈转头间看见,忍不住伸手替他轻轻拈去。
卫昭静静看着江慈将花瓣收入身侧的布袋之中。一阵细雨随风而来,江慈抬起头,正见卫昭明亮的眼神,如星河般璀璨。
江慈被他的眼神看得有些心惊,便对他笑了笑。
不远处的小木屋灯烛昏黄,身侧桃花带雨,眼前的笑容清灵秀丽。卫昭慢慢伸出手来,将江慈被细雨扑湿的几绺秀发拨至耳后。
他手指的冰凉让江慈忽然想起那夜他冰冷的身子,心中再度涌上那种莫名的感觉,却又不敢看他复杂的眼神,低下头,迟疑片刻,轻声道:“三爷,你身子刚好些,不要淋雨,还是早些回去歇着吧。”
卫昭的手指一僵,心底深处,似有某样东西在用力向外突起,但又似被巨石压住,压得他有些喘不过气来。
江慈听得他的呼吸声逐渐粗重,怕他伤情复发,忙上前扶住他的右臂:“三爷,你没事吧?”
卫昭痛哼一声,猛然闭上双眼,将江慈用力一推,几个起落,便消失在夜色之中。
雨,由细转密,将卫昭的长发沁湿,他在风中疾奔。
那日,为何不将她还给裴琰,真的只是,自己不愿过早露出真容吗?
这些时日,又为何会日日来这桃园,真的只是,为了看这一片桃花吗?
这夜,蒙蒙春雨中,响铃惊破京城的安宁,数骑骏马由城门直奔皇宫,马上之人手中的紫杖如同暗红的血流,洇过皇宫厚重巨大的铜钉镏金门。
卫昭久久立于皇城大道东侧石柱的阴影中,看着那道血流,和着这春雨,悄无声息地蔓延。
皇帝从睡梦中惊醒,披上外袍,多日来担心的事情就在眼前,他的面色反而看不出一丝喜怒。
重臣们集于延晖殿,心情都无比沉重,见皇帝进殿,匍伏于地,山呼的万岁声都透着忧虑。
皇帝冷声道:“少废话,该从何处调兵,如何调,谁领兵,即刻给朕理个条程出来。”
兵部尚书邵子和这段时日没睡过一个安稳觉,眼下早已是青黑一片,撑着精神道:“皇上,为防桓国进攻,本来是已经布了重兵在北线的,但后来见桓国没动静,便调了一部分去娄山支援宁将军。桓国这一攻破成郡,南下五百里,郓州、郁州、巩安兵力不足,即使将东莱和河西的驻军都顶上去,只怕还不济事,如果不从京畿调兵,就只得从娄山往回调兵了。”
静王面色沉重:“娄山的兵不能动啊,高成新败,宁剑瑜苦苦支撑,若还要抽走兵力,只怕薄贼会攻破娄山。”
庄王无奈,说不上话,低下头去。
董学士思忖片刻道:“成郡退下来的兵力,和郓州等地的驻军加起来,不到八万,只怕抵不住桓国的十五万铁骑,此次他们又是二皇子亲自领军,易寒都上了战场,看样子是势在必得,必须从娄山调兵。”
太子看了看皇帝的面色,小心翼翼道:“父皇,由谁领兵,也颇棘手。”
皇帝怒极反笑:“真要没人,朕就将你派上去。”
太子一哆嗦,静王心中暗笑,面上却肃然,沉吟道:“不知少君的伤势如何,若是他在,高成也不致于败得这样惨,桓国更不可能攻破成郡。”
董学士抬头,与皇帝眼神交触:“皇上,臣建议,娄山那边,还是宁剑瑜与高成守着,把王朗的兵往郓州调,那一带的八万人马,一并交给王朗统领,他在长乐多年,也熟知桓军的作战习惯,当能阻住桓军南下之势。至于娄山那块,让宁剑瑜将小镜河南线的人马调些过去,京畿再抽一个营的兵力北上驰援小镜河。”
皇帝微微点头:“王朗比高成老练,只能这样了。”
他转向户部尚书徐锻:“征粮的事,办得怎样?”
徐锻忙从袖中取出折表,将各地粮数一一报来,皇帝静静听着,心情略有好转。
徐锻念到最后,略有犹豫,轻声道:“玉间府的征粮,只完成三成。”
皇帝笑了笑:“玉间府是出了名的鱼米之乡,倒只收上来三成,看来小庆德王风流太过,忘了正事了。”
董学士心领神会,微笑道:“小庆德王也不小了,老这么风流,也不是个事,不如给他正儿八经封个王妃,收收他的心,想必也让皇上少操些心。”
“董卿可有合适人选?”
皇帝与董学士这一唱一合,众人齐齐会意,眼下西南岳藩自立,玉间府的小庆德王态度暧昧不明,对朝廷的军令和政令拖延懈怠,皇帝又不便直接拿了他,唯有赐婚,既可安他之心,也可警醒于他,至少不让其与岳藩联手作乱。
可这个赐婚人选,却颇费思量,要想安住小庆德王的心,一般的世家女子还不够份量,可小庆德王是谢氏皇族宗亲,也不能将公主下嫁于他。
陶行德灵机一动,上前道:“皇上,臣倒想起有一合适人选。”
“讲。”
“故孝敏智皇后的外甥女,翰林院翰林谈铉的长女,聪慧端庄,才名颇盛,必能收小庆德王之心。”
太子面上闪过不忍之色,诸臣看得清楚,知他怜惜这个表妹,可眼下国难当头,薄贼作乱,桓国南侵,如果小庆德王再有异动,三线作战,可就形势危急,唯有将小庆德王先安抚住,待北边战事平定了再解决西南的问题。
谈铉乃太子的姨父,才名甚著,在翰林院主持编史,门生遍天下,颇受百姓敬重,也素为“清流”一派所推崇,他的女儿与小庆德王联姻,小庆德王若要作乱,累及这位名门闺秀,必要冒失去民心之险。
但只要北边战事平定,皇帝显然是要腾出手来对付小庆德王的,到时,这位谈家小姐的命运,可就多舛了。
皇帝思忖片刻,道:“也没其他合适人选,就这样吧,董卿拟旨。”
“是。”
诸事议罢,已是天明时分。
太子出了延晖殿,眼圈略有些红,静王走到他身后,轻声道:“大哥莫要难过了,日后再想办法,让小庆德王上京做个闲散王爷便是。”
太子叹道:“姨母只这一个亲生女儿,我真是愧对母后。”
静王道:“只盼北线战事能尽快平定,小庆德王做个明白之人。”
太子眯眼望向微白的天际,摇了摇头:“桓国这一南侵,凶险得很啊。”
静王也叹道:“险啊。”
二人均负手望着北面天空出神,都不再说话。
卫昭拢着手,悄无声息地自二人身后走过,步入延晖殿。
见安澄急步进来,裴琰收住剑势,将长剑掷给侍女樱桃。安澄道:“相爷,金爷来了。”
裴琰微笑:“也差不多要到了。”
静王谋士金明见安澄出来,面色有异,忙道:“是不是相爷―――”
安澄道:“相爷伤势未愈,昨夜又受了些风寒,得请金爷移步才行。”
金明忙道:“有劳安爷了。”
金明随着安澄由前堂穿庭过院,不久便闻到浓浓的药草之气,细心的辨认一番,多是治疗外伤所用,心情便有些沉重,知裴相伤势只怕尚未痊愈,此行恐完不成王爷吩咐下来的任务。
室内光线昏暗,金明有一些不适应,半晌方看清裴琰面色苍白,斜躺于榻上,忙上前道:“金明见过相爷。”
裴琰以手掩口,轻咳数声:“倒是怠慢金爷了。”
“相爷太客气,金明惶恐。”金明面带忧色:“出京前,王爷千叮咛万嘱咐,说请相爷保重身体,还让我带了宫中特制的伤药。”说着从袖中取出一小木盒,递给安澄。
侍女进来,裴琰将她手中汤药喝下,接过帕子拭了拭嘴,低声道:“让王爷费心了,还请金爷回去禀告王爷,裴琰不敢忘记王爷之德,会尽快养好身子,我让人寻了几套孤本,争取回京与王爷共赏。”
金明有些踌躇,裴琰挥了挥手,安澄与侍女退去,金明上前低声道:“相爷,王爷说,若是您伤势大好了,看是不是想办法回京,现在局势有些不妙。”
裴琰缓缓坐起:“怎么不妙?”
“桓国撕毁和约,十五万大军南侵,攻到了郓州一带,皇上已将那一线的八万人马全交给了王朗。”
裴琰皱眉道:“倒让太子得了便宜。”
“是,皇上又下旨,将太子的表妹嫁给小庆德王为正妃。小庆德王将来若仍能稳做王爷,必是太子的强助,若是出啥事,皇上也必会因愧对故皇后,而对太子―――”
裴琰沉吟道:“这个倒也不急,我将来自有办法。”
金明一喜:“那是自然,王爷就说了,若是相爷在京,没有解决不了的事情。”
裴琰慢慢躺回榻上,叹道:“只恨我这身子不遂心愿,现在满心想帮王爷,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金明叹道:“也是没办法的事情,万事只能等相爷康复了再说。”
“嗯。”裴琰轻咳道:“还请金爷回去上禀王爷,只要伤再好几分,我便要回京城,届时还请王爷多多相助。”
金明忙点头:“那是自然,王爷就等相爷一句话了。”
裴琰立于窗前,看着金明出了园子,微笑着转身,步至案前,从容舒展地写下一行诗句。看着宣纸上的墨字,他颇觉满意,笑了笑,安澄却急步走了进来,凑近低声说了几句话。
裴琰手中毛笔一顿,眉头微皱,又舒展开来,淡淡道:“怎么让她跑了?”
安澄垂手道:“是安澄识人不明,请相爷责罚。”
裴琰放下手中之笔,思忖片刻,道:“明飞真是只为美色而带走的人?看着不象,你再仔细查一查他。”
“是。”
裴琰再想片刻,唤道:“樱桃。”
侍女樱桃进来,裴琰道:“将那件银雪珍珠裘取过来。”
看着狐裘下摆上那两个烧焦的黑洞,裴琰默然片刻,转而微微一笑,向安澄道:“你派个人,将这件狐裘送给三郎。”
七十、因何生怖
七十、因何生怖《流水迢迢》箫楼ˇ七十、因何生怖ˇ京城连着下了数日的细雨,加上桓国南侵,前线战事正酣,京城宵禁,到了夜间,以往繁华的街道上除偶有巡逻的禁卫军经过,空无一人。
禁卫军指挥使姜远将皇城防务交回给卫昭之后,便觉肩头担子轻了许多,晚上也有精神亲自带着禁卫军上街巡防。见一骑马车迎面而来,姜远立住脚步,手下之人忙上前横刀喝道:“大胆!何人敢深夜出行?!”
马车缓缓停住,一人在车内轻笑,姜远听着有些熟悉,上前两步,车帘后露出一张似喜似嗔的秀雅面容:“姜大人!”
姜远笑道:“原来是素大姐。”
他挥了挥手,手下都退开去,马夫也远远退于一旁。姜远上前轻声道:“素大姐还是莫要晚上出行,我的手下有些人不认识大姐,怕多有得罪。”
素烟抿嘴笑道:“大姐我也不是这么莽撞的人,今日实是有要事,正想找姜大人讨个牌子出城。”
姜远颇感为难,可素烟身后那人,与自己同属一营,实又不好开罪于他。
素烟见他沉吟,不慌不忙从怀中掏出一样东西,慢慢递至姜远面前,姜远看过,面色一变,猛然抬头。素烟仍旧温媚地笑着,却不说话。
姜远忙从腰间取下一块牌子,递给素烟:“要不,我送您出城?”
“倒不必了。”素烟笑道:“改日再请姜大人饮酒。”
“大姐慢走。”
马车出了京城北门,在乱石坡的青松下停住,马夫远远退开,隐入黑暗之中。
素烟掀开暗格,燕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