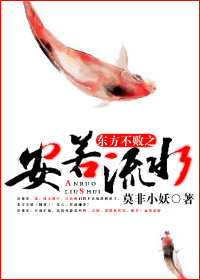流水迢迢-第2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裴琰叹道:“是啊,文妃娘娘虽然也被册为了贵妃,但比起庄王的生母和其身后的高族势力,王爷还是有点吃亏啊。”
静王心中暗恨,自出生以来纠缠于胸,生母为浣衣局宫女、出身寒素的自卑感,与身为皇子、天之骄子的自傲感夹杂在一起,让他忍不住露出激愤之色。
裴琰低头饮了口茶,又抬头微笑道:“王爷,现在局势很清楚,太子庸碌无为,皇上隐有废立之心,但与您争这个位子的庄王爷,他身后有着卫昭、陶相、高族这三大势力在鼎力支持,而清流一派及薄公又站于中间,唯皇命是从,敢问王爷,您的背后,有谁在支持您?”
静王站起身,长揖道:“望少君恕我鲁莽之举,日后,还需少君多多辅佐于我!”
裴琰忙站起来回礼:“王爷这般信任于我,愧不敢当。裴琰自当殚精竭虑,为王爷作一马前卒,鞠躬尽瘁,共图大业。”
二人同时起身,相视一笑。
静王把住裴琰双臂笑道:“听少君这一席话,令我茅塞顿开,对朝中局势有了更清晰的了解。只是不知少君现在作何打算?如若真要离开朝中一段时日,又有何妙计?”
裴琰转身拿起那套《漱玉集》,微笑道:“当年高唐先生批注此书,他论点再精妙,再旁征博引,发人深省,但仍是围绕着这本漱玉集来写的。”顿了顿又道:“我无论在朝在野,无论为官为民,长风骑十万人马日后不管是谁统领,这辅佐王爷的心,也是始终不会变的。”
静王面上露出感动之色,裴琰又道:“至于皇上这番布置之后,会如何动我,君心难测,我不便推断。但我自有计策回到朝中,只是需得王爷届时鼎力相助。”
“那是自然。”
裴琰捧起《漱玉集》,递至静王眼前:“这套《漱玉集》,还请王爷笑纳。”
静王忙推道:“此乃文中瑰宝,岂敢要少君割爱,能借来一观,足矣。”
裴琰道:“王爷,我这副身家性命都是王爷的,日后唯王爷之命是从,区区一套《漱玉集》,自然更要献给王爷,以证诚心。”
静王接过《漱玉集》,手抚书册,片刻后笑道:“好好好,今日得少君赠书明心,本王就厚颜承受这份重礼。日后待本王寻到相匹配的珍宝,自会回赠少君!”
裴琰将静王送出府门,慢慢悠悠地走回书阁,在窗前伫立良久,回转身,摊开宣纸,浓墨饱蘸,从容舒缓地在纸上书下三个大字―――“漱玉集”,他长久地凝望着这三个字,笑了一笑,放下笔,缓步走出书阁。
虽已至秋末冬初,但这日阳光明媚,那耀目的光辉,倒似是天地间在释放最后的秋色,赶在严冬来临之前,洒下最后一丝暖意。
黄昏时分,仍是暖意融融,江慈哼着小曲,蹲在院角自己开垦的那片花圃中,一手握着花锄,一手拨弄着泥土。
她自卫昭手上拿到一半解药,免了部分性命之忧,又由崔亮口中确定了那姚定邦确为奸恶残暴之流,下定决心替卫昭实施移花接木、混淆视听之计。这两日想到既能从卫昭手上拿到解药,又能令裴琰放过自己,心情实是愉悦。
裴琰进园,她斜睨了一眼,也不理他,自顾自地忙着。裴琰负手慢慢走过来,俯身看了看,眉头微蹙:“你的花样倒是多,也不嫌恶心!”
江慈抓起一把有数条蚯蚓蠕动的泥土,送至裴琰面前,笑道:“相爷,你钓不钓鱼的,这倒是好鱼饵。”
裴琰蹲落下来:“我现在在家养伤,哪能出去钓鱼。”
江慈忽地眼睛一亮,忍不住抓上裴琰的右臂:“相爷,府内不是有荷塘吗?里面一定有鱼的,我们去钓鱼,可好?”
裴琰急忙将她沾满泥土的手甩落,耳中听她说到荷塘二字,愣了一瞬,笑道:“哪有在自家园子里钓鱼的,改天我带你去映月湖钓鱼。”
“自家的园子里为什么不能钓鱼?那荷塘用来做什么?难道就是看看吗?或是醉酒后去躺一下、吹吹风吗?”
裴琰笑容敛去,站起身来:“子明还没回吗?听说他这两日未去方书处当差,是不是身子不适?”
“不知道,昨天早上见他还好好的,但晚上好似很晚才回来,我都睡下了,今天一大早他又出去了。”
裴琰面有不悦:“我命你服侍于他,原来你就是这样服侍的,连他去了哪里都不知道。”
江慈直起身,觉蹲得太久,腿有些麻木,眼前也有些许眩晕,一手捶着大腿,一手揉着太阳穴,嘟囔道:“你又不放我出西园,我怎知他去了哪里?再说了,他若是一夜未归,难道我就要一夜不眠吗?”
裴琰正待再说,却见她沾着泥土的手在额头搓揉,弄得满头是泥,笑着摇了摇头,转过身,见崔亮步进园来。
崔亮见到裴琰站于院中,似是一怔,旋即笑道:“相爷伤势看来大好了。”
裴琰与他并肩步入房中:“好得差不多了,皇上还宣我明日进宫,这么多日未曾上朝,也闲得慌。”
“相爷是忙惯了的人,闲下来自是有些不习惯。”
“看来我真是个劳碌命了!”二人相视而笑。裴琰笑道:“子明这两日去哪里了?”
崔亮神秘一笑,将门关上,坐回裴琰身边,替他沏了一杯茶,压低声音道:“这两日我想法子进了一趟密室,看到了那幅石刻图。”
“哦?!”裴琰身子微微前倾。
“图确是太师祖的原迹没错,但有些图形,似与师父所授有些微的不同,所以我怕有错,选了京城附近的细看了一下,记住部分图形,这两日去了红枫山实地验对了一番。”
“看子明胸有成竹的样子,定是验对无误的了。”
“正是。”崔亮微笑道:“我现在有八九分把握能将图原样绘出并找到各地矿藏,相爷大可放心,只要再去一两趟,最后确定各种图符,就定能无误了。”
裴琰笑得极为愉悦:“子明天纵奇才,我向来是信得过的。”
二人正说话间,江慈猛然推开房门,探头道:“崔大哥,你晚上想吃什么?吃醋溜鱼还是豆腐煮鱼头?”见裴琰欲待张口,她又笑道:“相爷定是不在我们这里吃的了,我也没备相爷的份。”
裴琰一噎,崔亮见江慈额头上满是泥土,忍俊不禁,走过来左手扶住她的面颊,右手握住衣袖细细地替她擦去泥土,柔声道:“你做什么我都吃,只是别太累着了,那片花圃留着明年春天再弄,何苦现在弄得满身是泥的。”
江慈笑道:“反正闲得慌,没事干,翻弄翻弄。”抬眼间见裴琰面色阴沉,忙挣开崔亮的手,跑了出去。
崔亮回转身,见裴琰望着自己,有些尴尬,自嘲似地笑了笑:“相爷,小慈她,我―――”
裴琰微笑:“子明劳累了两日,早些歇着,我还有事。”
“相爷慢走。”崔亮将裴琰送出西园,回转身,慢慢走到厨房门口,长久地凝望着厨房内那灵动的身影,默然不语。
江慈转身间看见,笑道:“崔大哥,这里烟熏子气重,你还是回房去吧。”
崔亮走到她身边,替她将散落下来的一绺秀发拢到耳后,轻声道:“小慈。”
“嗯。”
“以后,做什么事,不要太任性了,该忍的时候还是要多忍忍。”
“好。”江慈边往锅里加水边点头道:“我知道的,现在就是借我十个胆,我也不敢到处乱跑了,等师姐回来,我会老老实实和她回去的。”
“那就好。”崔亮笑了笑,终没有再说话,他步出厨房,望着暮霭渐浓的天空,轻轻叹了口气。
晚秋入夜风寒露重,天空中数点孤星,愈显冷寂。
城门即将下钥之时,一顶青丝锦帘软轿悠悠晃晃被四名轿夫抬出了南门。
守城的卫士望着那顶软轿远去,一人笑道:“红绡阁的姑娘们生意倒是好,这个时候还有出城去陪恩客的。”
其余的人哄然大笑:“小六子,等下换班后,咱们也去红绡阁,叫上玉儿,替你暖暖被子!”
那人直摇头:“不行不行,这个月的俸禄早用光了,昨晚又手气臭,输了个精光,我还是回家找自己老婆暖被子好了。”
笑闹声中,城门轰然关上,嗒的一声,落下大闸,夜雾轻涌,京城内一片寂静,仅闻偶尔的更梆声。
天上一弯弦月泠泠然,寒风轻吹,万籁寂无声。
铁蹄声踏破霜夜宁静,一匹骏马披星戴月,疾驰至南门口,马上之人丢下令牌,睡眼朦胧的值夜军士慌不迭地打开城门,马上之人怒喝一声,奔如流星,如闪电般消失在蒙蒙夜色之中。
三二、胸有丘壑
三二、胸有丘壑《流水迢迢》箫楼ˇ三二、胸有丘壑ˇ京城南面二三十里地,是红枫山。山多红枫,时值深秋,寒风吹得林间枫叶飒飒作响,又是荒鸡时分,黑蒙蒙一片。
崔亮在向南的官道上疾行,寒雾让他的眉间略显银白,呼出来的热气瞬间消散在寒风之中。
他回头向北望去,低低道:“相爷,你所谋事大,我实不敢卷入其中。崔亮这条贱命,只想留着走遍天下,游历江湖,就不陪你玩这危险的游戏了。”
他再低低地唤了声“小慈”,轻叹一声,终回转身,继续前行。
北风呼卷过他的耳边,隐隐送来铁蹄之声。崔亮面色微变,深吸了口气,闪入官道边的枫树林,攀上一棵枫树,将身形隐入黑暗之中,透过树枝,望向下方官道。
蹄音如雨,踏破夜空的宁静,“玉花骢”熟悉的嘶鸣声越来越近,裴琰的轻喝声清晰可闻,崔亮面色黯然,屏住呼吸,就连眼睛也只敢睁开一条小缝。
“玉花骢”自官道上疾驰而过,崔亮略略放松,却仍不敢动弹,心中叹服裴琰心机过人,竟还是猜到自己要从这红枫山南下,星夜追截,看来只有在这林间躲上一阵了。
时间一点点流逝,崔亮躺于枝桠间,仰头望向天空冷月寒星,感受着寒冷的夜风拂过面颊,眼前一时是师父临终前的殷殷嘱咐,一时是裴琰俊雅的笑容,一时又是江慈无邪的笑容,心情复杂难言。
蹄声再起,他侧头眯眼望去,朦胧夜色中,玉花骢慢慢自官道上走过,马上之人看不清面容,但从身形来看,似是无精打采,全无来时的急怒,透着沮丧之意。
崔亮看着这一人一骑自山脚而过,慢慢消失在京城方向,心呼侥幸,却仍有些警觉,再在树上小憩一阵,睁开眼,估算着已是日旦时分,裴琰应早已回到京城,方滑下树来。
他拍了拍身上树屑,再望向京城方向,默然片刻,负起行囊,向南而行。
再行数里,已到了窑湾。此处是一个三叉路口,向南共有两条大道,三叉口的东面,是一条潇水河的支流―――柳叶江,如一弯柳叶包住红枫山,形成一个江湾,故名窑湾。
在三叉路口西面的山峰上,建有一座离亭,具体年代并不可考,只知匾上之字乃前代大儒高唐先生所题――望京亭。木亭依峰而立,如临渊而飞的孤鹰,超然绝然。
崔亮在三叉路口犹豫片刻,提步向渡口走去。他知只要在这渡口想办法躲到天微亮,找到船只,放水南下,便可脱离险境。可刚迈出几步,他便心中一惊,停住脚步,望向道边树下的那个黑影。
裴琰负手从树下慢慢走出,微笑道:“子明要走,为何不与我直说,也好让我备酒为子明饯行。”
崔亮眼神微暗,沉默一瞬,轻声道:“累相爷久候,还将玉花骢让他人骑走,实是抱歉。”
裴琰笑道:“只要能与子明再见一面,便是千匹玉花骢,我也舍得!”
他抬头望向半山腰的望京亭:“不如我们到那处登高迎风,我也有几句话,要在子明离开之前,一吐为快。”
“相爷请。”崔亮微微侧身,跟在裴琰身后,登上望京亭。
裴琰负手立于亭中,仰望浩瀚天幕,素日含笑的面容平静无波。
崔亮立于他的身侧,遥望空蒙夜色,听着山间枫涛吟啸,只想抖落浑身尘埃,融入这一片空明之中。只是身边的人,恰似那一道枷锁,两年来禁锢了他的脚步,在这霜夜,他又急追而至,终让自己功亏一篑,陷入滔天的风波之中。
他暗叹一声,低声道:“相爷,我志不在京城,您又何苦费尽心机将我留下?!”
裴琰转身直视崔亮:“子明又何尝不是费尽心机,利用江姑娘作幌子,将我骗过。若不是安澄机灵,见子明去了红绡阁,觉得有些不对劲,细细查过回禀,我与子明,岂不是再也无法相见?!”
“相爷又是如何得知我一定会走这红枫山?”
“子明故布疑阵,这两日都来红枫山勘查地形,想的就是让我一旦发觉你离开,认为你不会走这边,又让红绡阁的软轿转去西南,安澄都险些上了子明的当。”
崔亮苦笑一声:“还是相爷对我看得透彻。”
裴琰叹道:“子明啊子明,你又何苦如此?我待你确是一片至诚,我裴琰这些年,广揽人才,礼贤下士,其中有当代鸿儒、名家大师,却都未曾有一人,令我象对子明这般用心的。”
崔亮忍不住冷笑:“相爷两年来派人时刻盯梢于我,确是用心。但您无非看中我是鱼大师的传人,识得那‘天下堪舆图’,为的是让我将那图原样绘出,为相爷实现胸中抱负而搅动这九州风雷,改变这天下大势!”
裴琰微微眯眼:“子明确是深知我心。只是我与子明说句实话,要得到‘天下堪舆图’,找出各地矿藏的,并不是我,而是我的叔父。”
“当年的震北侯爷裴子放?!”
“不错。”裴琰叹道:“子明,就算是我想得到这图,你又何苦这般逃避,倒象是我要将你杀了灭口似的。”
崔亮摇了摇头:“我倒不是怕相爷杀人灭口,实是这图关系重大,崔亮不敢轻易让之重现世间,连累苍生百姓,带起无穷战火。”
裴琰沉默片刻,道:“倒也不象子明说的这般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