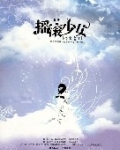路西法效应-第3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福监狱实验里的例子,当初一开始我们只是用“不过是个角色”来和真实个人做区别,但是当角色行为得到报偿时,
却开始造成深刻的影响。就像“班上的小丑”虽然赢得他无法用特殊学业表现得到的注意,可是接下来就再也不会
有人认真看待他了。或者是羞怯,一开始时可以用怕羞来避免笨拙的社会互动,这时羞怯是一种情境式的笨拙,但
是当怕羞的次数多了,原先只不过是扮演角色,最后却真的成了怕羞的人。
挫败感也是如此。当人们扮演界限僵化的角色,并因此赋予既定情境许多限制,像是限制什么行为才是适当、
被期待及获得强化的等等,这时候人们就可能做出很糟的事来。当人处在“正常模式”时,会用传统道德和价值观
来支配生活,然而角色的僵化性却关闭了正常模式中的传统道德和价值观。角色分隔(partmentalization)的
自我防卫机制,允许我们在心智上接受相互冲突的信念与期待,让它们成为彼此分隔的密室,以避免争执。于是好
丈夫也可以毫无罪恶感地演出奸夫的角色,圣徒可以是一辈子的鸡奸者,亲切的农场主人可以是冷酷无情的奴隶主
子。我们必须承认,无论如何,角色扮演的力量均足以形塑我们的看法,当一个人接受了教师或护士角色,他就可
能会为了学生及病患的利益终其一生牺牲奉献。
角色过渡:从医治者变成屠夫
这方面最糟的案例是纳粹党卫军医师,他们的角色是在集中营囚犯中挑选出处决或“实验”的人犯。而在经过
重新社会化之后,他们已经完全摆脱常态的医治者角色,完全进入杀人共犯的新角色当中。基于为了公共利益而必
须有所作为的群体共识,他们接纳了几个极端的心理防卫机制,以避免面对事实——身为犹太人集体屠杀事件的共
犯。要理解这段复杂过程,我们必须再次提起社会心理学者利夫顿。
刚进入这环境的新医生,一开始一定会对他所见到的景象感到惊骇,他会问一个问题:“这里的人怎么会做出
这些事?”一个普通的答案就能解答一切:对他(囚犯)而言,什么是比较好的?是在粪堆里苟延残喘还是乘着一
团毒气到天堂去?于是这个新人就会完全被说服了。面对严酷的生命现实时,大屠杀是每个人都被期待去适应的手
段。
将犹太人灭绝计划塑造为“最终解决方案”的心理学目的有两个:“它代表着独一无二的大规模屠杀计划,而
且从根本上把焦点锁定在问题的解决。”于是它把整件事变成一桩有待解决的难题,任何手段只要是必需的,都可
以来达成这个实用性目标。这样的理智训练,让同情与怜悯从这名医师的日常巡诊中完全消失了。
然而挑选人犯进行毁灭的工作是“如此繁重,和极端的邪恶又息息相关”,这让高等教育的医师们必须运用一
切可能的心理防卫机制,以避免面对他们是谋杀共犯的事实。对某些人来说,将情感与认知分离的“心理麻木”成
了常态:而另一些人则采取精神分裂式办法,过着“双重”的生活。于是在不同时间里,同一位医师身上可以存在
着残忍与高贵的极端特质,这必须召唤“存在于自我中两个彻底不同的心理丛结:一个是以‘普遍接受的价值’以
及身为‘正常人’的教育和背景为基础,另一个则是建立在‘与普遍被接受价值极端不同的(纳粹一奥斯维辛)意
识形态’的基础上”才能做到。这些双重倾向日复一日地来回摆荡。
角色互动及其脚本
有些角色要求相对的伙伴关系,就像狱卒角色的存在如果要有意义,就必须有人扮演囚犯才行。除非有人愿意
扮演狱卒,否则一个人无法成为囚犯。在斯坦福监狱实验中,不需要什么特别的训练就可以扮演角色,也没有手册
教你该怎么做。回顾第一天狱卒的笨拙以及囚犯的轻浮举止,只是因为两方都正在适应这个陌生角色。但是很快地,
随着以狱卒一囚犯共生关系为基础的权力差异愈益明显,我们的实验参与者也轻易地进入了他们的角色中。演出囚
犯或狱卒,一开始根据的脚本是来自于实验参与者自身关于权力的经验,包括观察父母之间的互动(传统上,父亲
是狱卒,母亲则是囚犯),以及自身对医生,教师、老板等权威人士的回应,最后,通过电影中对监狱生活的描绘
而刻画在他们脑海中的文化铭印,也是脚本的来源之一。社会已经帮我们做了训练,我们只需要记录下他们演出角
色时的即兴程度,就可以取得资料。
许多的资料显示,所有实验参与者的反应,实际上都曾在某个时候远超出角色扮演的要求,而这些反应渗透到
囚禁经验的深层心理结构中。一开始,有些狱卒的反应受到我们的说明会影响,在会中,我们曾大略提及为了模拟
真实的囚禁情境而希望创造出什么样的氛围。但无论这个舞台环境对于当个“好演员”这件事曾大略提供出何种一
般性要求,当狱卒私下独处,或是相信我们没有在监看他们时,这些要求理应不会有效。
实验后的报告告诉我们,单独私下和囚犯待在牢房外头的厕所时,有些狱卒会特别残暴,他们会把囚犯推进便
器中,或是推到墙上。我们观察到最残酷的行为都发生在深夜或是清晨的值班时间,如我们所知,狱卒们认为这时
候他们不会被我们监视或录音,在某个意义上也可视为是实验“关闭”的时候。此外我们也看到,尽管囚犯们不反
抗,而且随着这场狱中灾难达到顶点而露出颓丧迹象,狱卒对囚犯们的虐待还是每天不断推陈出新、愈演愈烈。在
一场录音访谈中,一位狱卒笑着回忆,实验头一天他还曾经因为推了一个囚犯一把而感到很抱歉,但是到了第四天,
他却已经对推挤和羞辱他们毫无感觉了。
克雷格敏锐分析了狱卒的权力转变。他仔细回想进入实验没几天后,他和其中一位狱卒之间发生的冲突:
在实验开始前,我和囚犯以及所有狱卒们都曾做过访谈,虽然为时短暂,但我觉得自己是从个体角度来认识他
们。也许因为这样,尽管他们的行为随着实验进行越来越极端、嗜虐,但我对他们是真的毫无敌意。不过很明显的
是,因为我坚持和囚犯们私下谈话——表面上的理由是和他们进行咨询,而且偶尔也会吩咐狱卒们停止一些特别严
重且毫无理由的虐待,所以他们把我当成背叛者。因为这样,有一位狱卒在日记中这样描述我和他的互动:“那个
心理学家离开(咨询)办公室前责备我铐住囚犯而且蒙住他的眼睛,我很气愤地回答他,我做这些都是为了安全的
考虑,而且这是我的事,不管怎样都和他无关。”他的确这样告诉过我。奇怪的是事情似乎颠例过来,是我协助创
造了这个模拟环境,现在我却因为无法支付这些新规范,而被一个我随机分派角色的狱卒戗得哑口无言。
谈到狱卒说明会可能造成的偏差,我们才想起我们完全没有为囚犯办任何说明会。那么当他们私下独处时,
当他们脱离不间断的压迫时,他们都做些什么?我们发现他们不是去认识对方,或谈论跟监狱无关的现实生活,而
是非常着迷于当下处境的各种变化,他们增饰自己扮演的囚犯角色,而不是与之疏离。狱卒们的情形也一样:从他
们私下在寝室或在准备轮班、换班空当中搜集到的信息显示,他们彼此很少聊和监狱无关的事或私事,常聊的反而
是关于“问题囚犯”、狱中即将出现的麻烦或对工作人员的反应——完全不是人们认为大学生在休息时间会讨论的
话题。他们不开玩笑、不笑,也不再其他狱卒面前流露出个人情绪,原本他们可以轻松运用这些方式让形势愉快点,
或是跟角色保持点距离,却没有这么做。回想一下克里斯蒂娜稍早的描述,她谈到她见到的那位亲切、敏感的年轻
人,一旦穿上制服进入他在牢场的权力位置之后,却摇身一变成了粗野残暴的西部牛仔。
扮演斯坦福监狱实验的成人角色
在进入斯坦福监狱实验给我们的最后教训之前,我想要再提出两个最后的观点来讨论角色权力及运用角色来正
当化违法行为。我们现在先跳出狱卒与囚犯是由志愿者扮演的,回顾一下几个角色:来访的天主教神父、假释委员
会的委员长、公设辩护律师,以及在探访夜出现的父母。父母们不仅觉得我们展示的监狱情境良好、有趣,还允许
我们将一系列武断独裁的规定用在他们身上、限制他们的行为,就像我们对待他们的孩子一样。我们也信任他们会
好好扮演深植于内在的角色——他们是循规蹈矩的中产阶级公民,尊重威权、极少直接挑战系统。我们同样也知道
即使囚犯们处于绝望中,而且人数远多于狱卒,但是这些中产阶级出身的年轻人也不可能直接杠上狱卒。其实只要
有一个狱卒离开牢房,囚犯与狱卒的人数比甚至可以达到九比二,他们却不曾反抗。这类暴力不属于他们从小习得
的角色行为,却可能是出身较低阶层的实验参与者所熟悉的,而且比较可能会采取行动改变自己的处境。事实上,
我们找不到证据证明囚犯们曾经策划要发动人身攻击。
角色的现实依赖支持系统而存在,系统对角色提出要求、规范,并且阻止其他现实情况入侵。回想一下,里奇
1037的母亲向我们抱怨他的情绪不佳时,我立刻动员了我的制度性威权角色回应并挑战她的观察,我暗示囚犯1037
一定有些个人困扰,所以他的情绪状态完全和监狱的运作问题无关。
回溯我当时的反应,我的角色从一个十分有同情心的老师,成为一心只顾搜集资料的研究者、麻木无情的警务
长,这样的转变最令人痛苦,在这个陌生角色中的我,做出一些不适当的怪事,我狠心打断了一位母亲的抱怨,而
她的确有理由抱怨;当帕洛阿尔托市的警局警官拒绝将我们的囚犯移到市立监狱时,我的情绪变得十分激动。我想
我会那样做的原因是因为我完全接纳了我的角色,也就是要让监狱尽可能正常运作。但也由于接纳了这角色,我只
关注“我的监狱”的安全和维持,于是在第二名囚犯也达到崩溃边缘时,我并没有察觉到有中止实验的需要。
角色的过错与责任
我们可以深深沉浸在角色之中,又能在必要时将自己和角色区隔开,也因此,当我们由于身为某个角色而犯下
过错时,很容易帮自己撇清个人责任。我们拒绝为行动负责,将责任怪罪在扮演的角色身上,说服自己本性和角色
没半点关系。这种说法显然和纳粹党卫军领导人在纽伦堡大审时的开脱之词有异曲同工之妙:“我只是照命令行事。”
只不过辩护的理由变成:“别怪罪到我身上,我不过是做我当时那位置上的角色该做的——那不是真正的我。”
赫尔曼和克莱416曾经接受过一次电视访问,我们回想一下赫尔曼当时如何合理化他对克莱的虐待行为。他声
称自己只是在进行“属于我的小小实验”,目的是观察要把囚犯逼迫到什么程度,才能让他们造反或是挺身维护自
己的权利。事实上,他主张自己的严酷行为是为了刺激囚犯们变得更好,而残暴的主要报偿就是囚犯的起义。这个
事后合理化有什么样的谬误呢?从他处理克莱416香肠造反事件的方式还有“中士”的反抗辱骂,我们可以轻易看
出端倪。赫尔曼并没有赞许他们起身维护自己的权利和原则,反而是大发雷霆,变得更极端、嗜虐。赫尔曼彻底运
用身为狱卒的最大权力,做出远超出情境的需求,只为制造自己的“小小实验”来满足个人的好奇心和乐趣。
为了进行斯坦福监狱实验后效的回溯性调查,赫尔曼和道格8612曾在最近接受《洛杉矶时报》的访谈,而他
们都用了类似理由来说明当时的行为——一个自称“残酷”,另一个人则用“疯狂”来形容;他们的理由则是一切
作为都是为了取悦我。”也许他们所扮演的正是日本电影《罗生门》里的新角色吧,如同电影里的每个人都对事实
有一套不同观点。
匿名性及去个人化
除了规定和角色权力之外,由于制服、装束和面具的采用,掩盖了每个人的一般面目,从而促成匿名性的出现
并降低了个人责任归属,情境力量也变得更有权威性。当人在情境中觉得自己拥有匿名性,也就是觉得没有人会意
识到他们的真正身份(所以也没有人会在乎)时,反社会行为就比较容易被诱导出现。假如情境本身又允许个人冲
动、服从指令,或者鼓励建立一些一般情形下会受鄙视的行为方针,情况更是如此。银色反光太阳镜就是这种工具,
它让狱卒、典狱长和我在与囚犯往来时显得更高不可攀、更缺乏人情味。制服则赋予狱卒一个共同身份,必须称呼
他们“狱警先生”也是一样的道理。
有大量的研究资料证实,去个性化助长了暴力、破坏公物、偷窃等越界行为(将在后面的篇章中进一步讨论),
尤其当情境支持这类反社会行为时,这对孩童造成的影响并不亚于成人。在文学作品,如威廉·戈尔丁(William
Golding)的小说《苍蝇王》中找到这类过程描述。当群体中所有人都处在去个性化的状态下,他们的心智运作方
式会改变:他们活在一个延伸现在的时刻中,使得过去和未来都变得遥远而不相关。感觉会支配理性,行动能凌驾
反思。在这种状态中,导引他们行为不偏离社会正轨的一般性认知和动机激发过程已不再发挥作用。阿波罗式的合
理性及秩序感被迫让位给戴奥尼索司式的过度放纵甚至混乱。接下来,人们不再考虑后果.发动战争就会变得像做
爱一样容易。
于是我想起来自越南的一行禅师的启发:“为了彼此斗争,同一只母鸡生下的同一窝小鸡,脸上的颜色不会一
样。”这是个妙喻,可以用来描绘去个性化在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