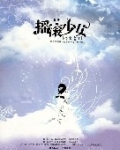路西法效应-第3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负面的方式行动。
我们十分惊讶地发现,狱卒们几乎和大多数囚犯有相同程度的负面看法及负面的自我评价。事实上,“好狱卒”
乔夫·兰德里对自我的负面评价比任何囚犯都还多,负面情绪在所有人当中也最普遍,只有一位实验参与者的负面
情绪比他更严重,就是道格8612。从我们与囚犯的访谈中,可以归纳出一个特色,即囚犯在情绪表达以及自我评价
及行为意图(主要是意图表现侵略性,并且对自身处境的看法倾向负面悲观),都普遍有负面反应。
这些访谈显示,在留下来进行实验的囚犯及被提前释放的囚犯身上,实验对情绪影响出现了清楚的差异。对照
留下来的和被释放的两群人(根据每个访谈中的表现),比较他们在负面看法的表达,负面情绪、负面自尊感及意
图表现侵略性的平均数。结果发现,被提早释放的囚犯的期望更加负面,并较常表现出负面情绪、负面自尊感,在
意图表现侵略性次数方面,则多于坚持留下的牢友四倍。
当囚犯们暂时不必列队答数、无须卑躬屈膝听人差遣,或无须参与公众事物时,窃听囚室中的私人对话,可让
我们了解囚犯在私底下的交谈内容。请记住,一开始时,分配在同一囚室的三个室友们彼此完全陌生。只有当他们
回到隔离的囚室时,他们才开始互相认识,因为在公共活动时间时,任何“闲聊”都不被允许。由于囚犯们同处于
封闭的环境中,并且预期接下来将有两个礼拜的互动,因此我们认为,他们将会寻找共通点以联系彼此。我们预期
听到他们聊彼此的大学生活、主修的课程、职业、女朋友、喜欢的球队、音乐偏好、嗜好、实验结束后打算在剩下
的暑假中做些什么事,也可能会聊到要怎么花掉即将到手的报酬。
完全不是这样!所有这些预期几乎都落空了。在我们所录到的囚犯对话中,有整整九成都跟监狱主题相关。只
有一成的谈话焦点落在个人的或生平经历介绍。囚犯们最关心的事情是食物、狱卒的骚扰,他们希望能够开个会让
大家发发牢骚,并构想脱逃计划,他们也关心其他囚室囚犯及一些孤僻囚犯们的行为表现。
当他们有机会暂时远离狱卒的骚扰以及无聊沉闷的照表操课,有机会借助社会互动而暂时超越及抛开囚犯角色、
建立自己的人格认同时,他们却没有这么做。囚犯角色支配了个别人物的所有表达。监狱情境支配了他们的看法及
所关心的事物,可说是迫使他们进入一种延伸现在的时间定位。无论自我是处于被监视或者暂时获得喘息的状态,
都无关紧要。
囚犯们并不分享他们对过去和未来的期望,因此,每一位囚犯对其他囚犯的唯一了解,都以观察当下行为表现
为基础。我们知道的是,囚犯们在服刑期间以及从事其他差役时,眼中看到的通常只会是彼此的负面形象。但这个
负面形象却是他们在同侪眼中建立自己的性格印象时,唯一的凭借基础。由于他们只关注于当前情境,囚犯们也因
此助长了一种心理状态,这种心理状态更强化了他们的负面经验。因为一般而言,当人们面临恶劣处境时,会试图
以时间观点将情境区隔化,于是他们可以借着缅怀过去来自我安慰,并借此想象一个更好的、不一样的未来。
这种囚犯自我加诸的心理状态,甚至会造成更大的伤害:囚犯们开始采纳甚至完全接受狱卒针对他们制造的负
面形象。在所有囚犯私下互动的回报中,有一半都可归类为不具支持性质及不具合作性质的互动。更糟的是,当囚
犯们评价相同遭遇的牢友,或向他们表达关心时,85%的几率不是赞赏或鼓励,有时甚至是不以为然!以下数据在
统计上有重要意义:谈话焦点较着重于监狱议题而不是非监狱议题,偶然发生率只有1%;谈话焦点集中在牢友的
负面特质与集中于正面或中立特质相对时,偶然发生率只有5%。这意味着,这类行为效应是“真实存在”,不该
归因于囚室里私下的随机谈话。
囚犯们经由这些方式逐渐内化监狱中的压迫,于是,看着同伴被羞辱、像绵羊一样驯服,或者是做着不用大脑
的下贱工作,就是同伴印象形成的主要方式。既然对其他人没有任何尊敬之意,又如何能在监狱里拥有自尊?最后
这项未预期的发现,提醒我想起“认同加害者”的现象。心理学家布鲁诺·贝特尔海姆用这个词来描述纳粹集中营
中的囚犯是如何内化他们的压迫者本身的权力(首次运用这个词的人为安娜·弗洛伊德)。贝特尔海姆观察到,某
些囚犯的行为表现就像他们的纳粹狱卒,他们不只虐待其他囚犯,甚至穿上被丢弃的纳粹党卫军制服。这些受害者
不顾一切地希望在充满敌意、朝不保夕的生活中幸存下来,他们只意识得到侵略者的需求,而不是去反抗;他们拥
抱了侵略者的形象,然后变成侵略者的样子。在有权的狱卒及无权的囚犯之间存在着惊人的权力差距,然而这差距
却被这类心理操练极小化了。人变成与敌人共存——在自己内心。这种自我欺骗可以避免对自身处境的现实评价,
抑制斗争行动、对抗策略或是造反,而且不容许对自己的受难同胞有任何同情。
生命是自欺欺人的骗术,要骗得天衣无缝,就必须习惯成自然,一路骗到底。
——威廉·黑兹利特《论迂腐》,载《圆桌对论》
(William Hazlitt,“On Pedantry”,The Round Table,1817)
斯坦福监狱实验的教训和信息
叙述完扮演囚犯及狱卒角色的年轻人个人特质和特殊行为反应后,现在要思考这项研究提出的广泛概念性议题,
及其教训、意义和所要传达的信息。
科学实验的优点
从某个角度面言,社会学者,犯罪学者以及来自囚犯的叙述都曾为我们揭露监狱生活的邪恶面,而斯坦福监狱
实验并没有让我们对监狱产生任何新看法。监狱是个野蛮的国度,能够激发人类天性中极恶的一面。监狱是暴力及
犯罪的温床,在这方面的贡献远胜于它促进的建设性改造。60%或更高的再犯率说明了一件事:监狱已成为刑事重
罪要犯的旋转门。我们已经了解到,作为社会的犯罪控制工具,监狱是彻底失败的社会实验,除了这件事之外,斯
坦福监狱实验到底还能让我们知道些什么?我认为答案就存在于这个实验的基本规则中。
在真正的监狱里,监狱情境以及居住其中的人们的缺陷无可避免地交织,混淆在一起。我回忆起我和帕洛阿尔
托市警察局警官的第一次谈话,当时我向他解释我为何不去观察地方监狱,而选择进行这样的研究。我设计这项实
验的目的是为了评估一个模拟的监狱情境,对于生活在其中的人——包括狱卒及囚犯——造成的影响。透过种种实
验控制,我们可以进行一系列的尝试并得到结论,而这是在真实世界中不可能办到的.
首先是系统性的选择步骤,确保了每个进入我们监狱的人都尽可能是正常、普通、建康的人,他们不曾有反社
会行为、犯罪或是暴力记录。此外,由于实验参与者都是校园里的学生,相较于教育程度较低的同年龄人,他们的
智能都在平均水平之上,较不具偏见,对自己未来也有较高的信心.再者,由于实验研究的关键——随机分配——
不管这些好人们原先的意愿是否倾向哪一方,他们的角色都由随机分配,一切纯属机运。进—步的实验控制还包括
了系统性观察、不同形式的证据搜集以及统计资料分析,这些都被用来裁定在研究设计的参数中,受试者经历事件
所受的影响。斯坦福监狱实验基本规则就是让人摆脱地域限制,让天性摆脱情境、让白布脱离染缸。
然而我必须承认,所有的研究都是“人为的”,是真实世界相似物的模拟。尽管如此,不论是斯坦福监狱实验
或者是我们即将在之后篇章中读到的社会心理学研究,姑且不论经过控制的实验研究的人为性质,当这类研究以敏
锐的手法尽力捕捉“世俗实在”(mundane realism)的基础本质,其研究结果就有相当的概化能力。”
就许多明确的性质而论,我们的监狱显然不是“真正的监狱”,但就我认为是“监狱经验”核心的“囚禁经验”
的心理特质而言,这项实验的确是把握到了。当然了,从实验中推导出的任何研究发现都必须提出两个问题,首先
是“比较对象为何?”下一个则是“外部效度”(external validity)为何?——这个实验能不能有助于说明与
之平行的真实世界?这类研究的价值在于它有能力阐明潜在过程,确认因果次序,并建立起能传递所观察到之作用
(observed effect)变项。除此之外,当统计的意义不能被视为偶然存在的关联而排除不论时,实验也能建立出
因果关系。
几十年前,社会心理学的理论研究先驱库尔特·莱温(kurt Lewin)曾经主张建立实验社会心理学的科学。莱
温坚持,从真实世界中提炼出有意义的议题,无论在概念上或实作上都是可行,而这些议题也能在实验室中检测。
他认为只要研究经过悉心设计,并且谨慎执行自变项(作为行为预测项的先行因素)的操作,就有可能建立确定的
因果关系,而这是田野或观察研究所无法做到的。尽管如此,莱温还更进一步主张运用这类知识去影响社会变迁,
主张运用在研究基础上得到的证据,去了解并尝试改变及改善社会及人类的功能。而我必须试着追随他启示的方向。
狱卒的权力变化
在使一个人的意志屈服时品尝到的权力滋味,远胜于赢得他的心。
——埃里克·霍弗,《心灵的激情状态》
我们有些志愿者被随机指定扮演狱卒角色后,很快便开始滥用新取得的权力,他们残酷成性,日夜无休地贬低、
鄙视、伤害“囚犯”。他们的行动符合我在第一章中对邪恶的心理学定义。其他狱卒虽然并未特别有虐待倾向,但
是显得冷酷、苛求,对于受难同袍们的处境极少流露出同情。只有少数狱卒可被归类为“好狱卒”,他们抗拒了权
力的诱惑,而且有时候能为囚犯的处境着想,多少为他们做点事,比方说赏个苹果或塞根香烟给人之类。
尽管在制造恐惧和复杂性程度上,斯坦福监狱实验和纳粹集中营系统间有着极大差距,但奥斯维辛死亡集中营
中的纳粹党卫军医生和我们的斯坦福监狱实验狱卒间还是有个有趣的相似性。纳粹党卫军医生和实验中的狱卒一样,
也可以分成三种群体。根据利夫顿于《纳粹医生》的描述,“爱国者热切地参与处决过程,甚至为了杀人而自愿‘加
班’;有些人则多少可说是按照条理工作,只做觉得自己该做的事;剩下的人则是不情不愿。”
在我们的研究中,勉强扮演自己角色的好狱卒意味着“不作为即善”(goodness by default)。与其他值班
同伴的恶魔行为相较之下,给囚犯们施点小恩小惠。正如先前提到的,他们之间没有人曾介入阻止“坏狱卒”们虐
囚;也没有人跟工作人员抱怨、迟到早退或是拒绝在紧急情况下加班,甚至没有人为了必须做这些讨厌的工作而要
求加斑费。他们只是“不作为之恶综合征”(Evil of lnaction Syndrome)的一分子,这部分将会在后面篇章中
完整讨论。
我们回想最好的狱卒乔夫·兰德里,他和最坏的狱卒赫尔曼一起轮小夜班,但他从来不曾尝试让赫尔曼“冷静
下来”,或是试着提醒他“这不过是个实验”,这些孩子只是在扮演囚犯的角色,没必要让他们受这么多苦。乔夫
只是默默承受痛苦——跟囚犯们一起受苦。如果他的良知能够激励他做些有建设性的行动,那么这位好狱卒也许可
以发挥相当的影响力,改善在他值班期间日益升高的虐囚现象。
从我在许多大学中的多年教学经验,我发现大多数学生并不关心权力的议题,因为他们在自己的世界中拥有许
多资源,可以凭借才智和辛勤工作来达成自己的目标。只有当人拥有许多权力而且想要继续享受权力,或是没什么
权力却又想要更多的时候,权力议题才会受关注。然而权力之所以成为许多人的目标,主因是享有权力的人可以任
意支配资源。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经这样描述权力的诱惑:“权力是春药”。权力的诱惑吸引着年轻貌美的女性
投向又老又丑的权威人士的怀抱。
囚犯的病理分析
哪里违背意志,哪里就是人的监狱。
——爱比克泰德,《谈话录》(Epictetus,Discourses,2th century)
研究一开始时,我们比较关注扮演囚犯角色者如何适应无权无势的全新地位,而不是那么关心狱卒的适应问题。
当时我刚花了一整个暑假
时间沉浸在我在斯坦福大学与人共同执教的监禁心理学,所以已经准备好要站在他们那一边了。卡罗·普雷斯
科特刚跟我们说了一堆狱卒手下发生的虐待和堕落故事。从曾经是阶下囚的人口中,我们也听说了囚犯性虐待其他
囚犯及帮派斗争等恐怖的亲身经历。所以克雷格、科特和我早就私下倒向囚犯那边,暗自希望他们能够撑过狱卒施
加的各种压力,尽管他们被迫戴上外在的劣势标签,仍然希望他们能维持人性的尊严。我甚至想象自己会是电影《铁
窗喋血》里保罗·纽曼那一类能以智慧方式进行反抗的囚犯,从没想过自己会成为他碰上的狱卒。“
当囚犯叛变以出人意料的速度发生时,我们感到相当欣慰;他们抗议狱卒指派给他们的奴役差使根本是找麻烦,
也质疑任意武断的执法以及让人筋疲力尽的频繁列队报数。当初我们通过报纸广告招募他们来参加所谓“监狱生活
研究”,但现在他们对这研究的期待已经完全破灭了。他们原本以为只是做几个小时的低贱差事,其余时间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