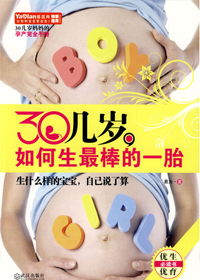她们都挺棒的-第1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艶的色彩,另外我再这么短的时间内不可能完成。我这么一说,那就只能是那个像伊能静的小姐干的了。空姐迟疑了一下,叫我不要声张,在外头等,她取了工具到里面几分钟就收拾好了。我重新进去,屁股一触到马桶,体内的污物早已迫不及待滚出来。我快意地想象它砸向芸芸众生,特别是砸到衣冠楚楚的家伙打著者哩水喷着香味的头上,虽然只有灰尘那么大了,但它毕竟是我的屎,有着我的臭和我的愤怒。我把愤怒发泄完毕,出来对空姐说,你最好把这个事情调查一下,我受了一点刺激,也受了一点冤枉。空姐答应会查的,让我先回座位上。
在我回座位的途中,居然没发现伊能静坐在哪里,我只好跟林建设探讨这个问题。林建设认为这个小姐可能肛门藏有白粉之类的,怕拉出去,我一直不认同,那么漂亮的女人肛门拿去藏毒品,显然大材小用,而且他妈的太残忍了。临下飞机时,空姐告诉我已经调查过了,那个小姐承认是她干的,她可能有点心理毛病,害怕大便拉出去会砸了人。我在霎那间突然觉得那位小姐真是很可爱,我恨不得大便能多砸几个人,她却害怕砸了人,如今像这么有怜悯心的女人不多了。所以我默默地祝她不是毒品贩子,祝她是个好心肠得有点过敏的女人,祝她的肛门有正当的用途。
3
来机场接我们的是对方公司的公关部经理,一个三十来岁的女人,看起来是个广东土著,个儿矮,唇厚,脸宽,有颧骨,但她化妆很到位,简直化腐朽为神奇,妖艶而高贵。她的名片上写张霞,我们叫她张经理。我个儿矮,虽然喜欢高女人,但实际上矮的女人更有亲和力,我和她坐在后排,一上车就跟她聊上了。如果不看其它部位,她的两片厚嘴唇还真他妈棒,口红很深但很有神采,很想拿一根什么东西让它夹祝对了,是口交,这种嘴唇最适合口交。但从她性感的嘴唇里蹦出来的幷不是什么性感的话题,她喋喋不休地介绍她的公司,概括地说内容如下,老总是一个摸到几十万彩票起家的家伙,先前是做妇女用的卫生巾,但不是安尔乐,是个不怎么知名的品牌,估计全国大部分妇女都没用过这种品牌,虽然没多少女人用,但也赚了一把,可见女人的胯下是个很要命的消费带。卫生巾没做多久,很快就开始做家电,又发了,老总不断地追求有文化品位的产业,在广东、福建入股投资了多家媒体,现在想跟我们报社合作,是触角伸向北京的第一步,等等等等。
由于她说得非常流利,我怀疑老总是个很爱炫耀的家伙,没事干就叫手下宣传创业史。不过这种傻逼太多了,比如说一个在《中国青年》的朋友告诉我,他们杂志宣传了一个在中关村搞IT的家伙,那家伙就买了几百本《中国青年》分给手下及亲戚朋友,结果有一天他发现公司厕所里扔了好几本,有人还在他的照片下写上“自恋狂”、“网络炮灰”等字样,大概都是辞职或被裁员的人写的。不说这些傻逼了,说说张霞,虽然她说的这些鶏巴创业史我丝毫不感兴趣,但幷不妨碍我们愉快地坐在一起,除了嘴唇,她的香水也让我舒服,绝对是很名牌的很巴黎的。其实上大学那阵子我对香水特熟,什么金典淡香精、超级古龙香水,还有什么爱丽安、绿茵、百葳尔、蓝钻佳人、恬梦走珠,一出口就能溜一串,还能根据你的口味、职业、场合、消费能力建议用什么品牌,原因是当时我做过香水的传销。现在这些知识我忘了,否则倒可以夸夸张霞。总而言之,张霞口红和香水给我很好的印象,老实地说,呆在广州的两天我一直有源源不断的情欲,我相信就是被张霞的口红和香水引出来的。这说明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第一印象很重要,如果是一个太监来迎接你,你大概什么都不会想了。
张霞给我们安排在白天鹅宾馆,五星级的,其实对我来说几星级倒无所谓,关键是要生活丰富。她在窗口指着珠江对我说,你看,这里风景不错吧,这也是特意给你们安排的。我想张霞可能把我当成爱看风景发牢骚的文人雅士,其实对我来说,珠江如果变成一条大腿更好,是的,如果是一条王祖贤的美腿,横在窗外,那他妈的才叫好风景。海珠桥变成一根小阴茎,搁在大腿上,对我而言,这才是妙不可言的住处。可是,狗日的珠江根本就不像个大腿,至少不是我喜欢的雪白的大腿,水浑得要死,像是马尿和驴粪搅和的。自从我们的母亲河流行变色以后,所有的河流都变了颜色,所有的女孩都染了头发,剃了阴毛,当然剃了阴毛有时候会更好看些,可是河流变了颜色就不那么好玩了,不但让人想不起来可以比喻成大腿,连小腿、手臂、手指头甚至手指甲都比喻不成。从珠江的颜色来看,倒可以比喻成阴道,因为谁也没见过阴道,从阴道出来时我们的眼睛还没睁开呢,所以可以认为阴道就是这么黑糊糊的。可是,你要是从珠江想起了阴道,以后你就再也不想进入阴道了。总而言之,张霞给我安排的风景实际上没有风景,但这也怪不得她,她怎么会想到从北京来的客人一点文化都没有就会往这里想呢!
反正,住着得了,不要想太多,下午三点钟还有个谈判会。在开会之前林建设让我整理一些材料,主要是我们报社的发展计划,让我看看有没遗漏材料,我才不管有没遗漏呢,又不让我当副主编,我的心不能操那么远。再说这种鸟材料还真没什么人会去看,至少没什么人会去认真地看,该谈的问题都摆上桌面谈,我从来不把脑力花在无谓的东西上。这一点我很早就认识到,比如说大学里写论文,我当时就知道这玩意儿跟我的生活八辈子挨不着边,从来都是在文学阅览室里抄。有一回写列夫·托尔斯泰,我写他的宗教观与创作的关系,在一本《论托尔斯泰文集逊上抄,抄完了却忘记做个记号,叫别人不要抄这里的,结果有个叫谢为的同学抄的跟我一样,当然,也许是谢为先抄,忘了做记号,反正我们撞车了,犯了做论文的大忌。老师给我的论文评语是“关于托尔斯泰的这个问题,你可以和谢为同学一起探讨”,给谢为的评语是“这个问题你可以和李有钱探讨”,好在老师幷不为难我们,都给我们及格。毕业以后我和老师还是莫逆之交,和那些没人听课却天天要点名的老师相比,我的这个老师太英明了,他绝对替托尔斯泰做了一件好事,至少到现在我还没讨厌这个喜欢写大部头的家伙,虽然也不热爱他。靠,我怎么扯到托尔斯泰了,回过头来谈谈文件,我不花一个脑细胞就给整理好了,比抄托尔斯泰要简单一百倍。我关心的不是假模假样的文件,我关心的是要不要跟他们坐在会议室里憋他妈的一个下午。以前我在机关里上班,开会时总要坐在一个漂亮的小妞旁边才呆得住,比如说平时不怎么说话的小妞开会时绝对会跟你窃窃私语,还把香水弄到你鼻子里。这时候你会觉得开会特别有意思。把味如嚼蜡的东西变成有意思的东西,我觉得这就是生活的艺术。从这一点上说,我确实有几颗艺术细胞,远不比留长发的小白脸差。可是,搞这种艺术要有小妞才成,要开人比较多的会才成,像这种谈判会,绝对不成。好在林建设说我没必要去,忙我自己的,可能是他怕有什么机密让我知道。不过我也才懒得知道,事情知道太多了心里累,八岁时我就明白这个道理。那时我姐姐在谈恋爱,跟一个经常给我吃话梅糖的家伙,要我保守秘密,我每一次都要在父母面前隐瞒姐姐的去向,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不是说随便扯个谎就可以了,是心里累,像块石头搁着,有一天我实在受不了了,我告密了,图个心里舒服,我宁可不吃当时买不起的狗日话梅糖。
当天下午我去找一个大学同学,毕业后他在广州一个中学教书,好象是44中,我的这个同学大学时从不谈风月,只知道踢足球、打篮球、喝啤酒,好象中性人,可是一毕业就立马结婚,几个月之内就操出了个儿子。这个速度太快了,搞得我们都怀疑儿子是不是他的。带着这个疑问,我坐上14路车,几站地就到了前进路那个中学,我看到一张昔日生猛的脸如今慈祥了,我的同学,一个中规中举的父亲正在给儿子换尿片,他已经从儿子大便的颜色中观察到病症了。从他儿子的长相不能判断是不是亲儿子,有像的地方也有不像的地方,当然,我老怀疑别人的儿子是不是亲儿子也不对,即使不是亲儿子,但人家就当亲儿子,也可以享受天伦之乐。但我他妈的就是爱往邪里想,总想让生活出点彩,总想让别人的老婆红杏出墙,总想扭曲正常的生活。这就像一个偷窃上瘾的人,别人送的东西不要,偏要去偷。所以你要理解我的想法,我真正的目的只想让生活更精彩,更好玩。好了,我不管我同学的儿子是不是亲的,也不管他老婆有没有外遇,我只和我的同学聊了一会儿天,我发现我们根本谈不下去,没法谈,他所知的太有限了,他知道最多的就是教材改革后语文课本中多了哪几篇文章以及超市里尿片和进口奶粉的价位,甚至他连疯牛病都不懂,也许听说过,但根本没有和进口奶粉联系起来。我深深地感受到,中学教师的环境和待遇会把一个人活生生给毁了,太封闭,他教最多的人,但他最无知。差不多所有当老师的同学都这样,我确实是很切身地感觉到,所以我要说一说,我要很忧国忧民地呼吁一下改善教师的环境。我和我同学谈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娱乐问题,说白了,也就是我问他广州妓女的分布状况。我的同学思索了一会儿,也许他根本不知道,但他觉得连这个都不知道就太没文化了,所以用搜索引擎查遍整个大脑,最后他告诉我海珠广场有很多妓女,在晚上,全是穿裙子的,干起来方便,最便宜的五块钱。但是他建议我玩十块钱以上的,五块的太没档次,基本上又老又丑,但也不要太贵,100块钱能玩三四个也就可以了。我很感谢他为我这样细心地分析,特别是为我经济上精打细算,打听完妓女我就回宾馆了,尽管他一再挽留我吃饭,我还真怕吃完饭后他会叫个十块钱的妓女来陪我。
我回来时会议早就结束了,我问林建设有没结果了,林建设摇摇头,说,越谈越复杂了,细节上的分歧越来越多,明天可能还要搞一天。这正是我想要的结果,我当然不会关心洽谈愉快不愉快,我只想在广州多玩一天而已。对我来说,公款旅游的机会已经灭绝,只能借少有的出差机会见缝插针玩一把。我在机关的时候,机会倒是不少,每次出去交流或采风什么的,反正名目不少,招待方总会把当地最漂亮的姑娘叫来陪舞,姑娘一般都是当地的幼儿园或小学教师,或者艺校学生,招待客人是她们例行的工作。我对跳舞倒不感冒,我觉得交谊舞是一种比手淫还逊色的活动,比如说你把爪子搭在姑娘的腰上偶尔还碰一下她的胸,吸着她的芳香和体温,你要是这段时间刚好性问题得不到解决,下面就会硬起来,在这种场合下硬起来比较麻烦,你既不能用手弄,也不能指望姑娘会去安慰它,而且它把裤子撑起来有碍观瞻,甚至还会捅到姑娘的大腿。所以我只能认为交谊舞是一种比较不到位的性活动,比手淫还低一个档次。更让我难受的是,我看到随行的那些德高望重的老头子搂着姑娘们做卿卿我我状,一种愤怒就会涌上心头,你凭什么可以这样糟蹋姑娘,你又不花一个子儿,你他妈的凭德高望重,就可以像一堆牛粪挨在鲜花上。一般来说,我心里没事的时候就会对诸如此类的现象产生愤怒。愤青是怎样炼成的,就是这样一点一滴炼成的。所以我绝不相信愤青是在美国轰炸我驻南使馆、美国飞机把我飞机搞掉诸如此类的事件中炼成的,至少这种愤青绝对不是合格的愤青,正点的愤青。
还是回头侃侃我这个愤青在广州的活动。晚上张霞请我们去玩,说今晚一定要玩得痛快。这句话一说出来我们就觉得阴险,不就是想把林建设拖垮了明天在谈判上俯首称臣吗!所以女人搞阴谋只能搞很肤浅的阴谋,她们可以搞得很恶毒,但基本特征是肤浅,只要你不晕了头,就能看出破绽。我回头咨询林建设,林建设不愧是老江湖,颇有大将风度地穿上那件欧洲定做的西装,说,那就走吧。张霞边走边问,你们喜欢玩什么呢?林建设指着我,说,你问小李吧,年轻人喜欢玩什么就玩什么。这个问题还真把我问倒了,想玩的东西太多了,最想的就是抱个俄罗斯大美妞一边做爱一边教我说俄语,还有脱衣舞也不错,能把性冷淡的挑逗得欲火焚烧的那种。不过这个好意思跟人家提出来吗?这他妈的就叫欲望太多不知所措。我支吾了半天,结果又落入俗套,说去唱歌吧。这个建议一提出来我就后悔,可后悔有什么用呢,谁叫你胆子鶏巴校我们随着张霞上了车,也不知道她要把我们弄哪去。我估计一年365天她不止要招待365拨客人,广州的娱乐场所应该了如指掌,这样很好,连嫖妓都有人张罗一直是我的梦想。当然,我以前的梦想不是这个,上小学那阵子我想当个老山前线的战士,躲在猫耳洞里啃着饼干时不时把敌人干掉一两个的那种;上中学了就想当画家,今天上黄山明天上庐山描绘祖国的秀丽山川被很多女孩子崇拜自愿给你当人体模特甚至自愿给你研究人体;上了大学就想弃画从文,主要原因是上了该死的中文系,整天想往文学史里钻,当时想写一部比《红楼梦》更红的千百年后还有人盗版幷有上万人整天研究我就可以混饭吃的经典名著,而且有了这部名著后《红楼梦》就没什么人谈了,千年之后还有漂亮女人一边啃我的作品一边想象我很帅的样子,当时这种想法也克服了我的自卑心理,反正现在丑一点没关系,死后就越来越美化甚至神化了。毕业后这些美梦都掐了,有一段时间在很多公司里混,当时的梦想就是当个白手起家的企业家,主要原因是整天手头吃紧,连请女孩喝茶都要找个男的一块儿买单,所以都在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