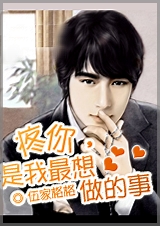抢劫,是要遭雷劈滴!-第1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幕しê吞弥饕膊荒芩嬉庾叨牡胤剑耸比从幸桓龌疑纳碛霸谑榉棵磐庾呃醋呷ィ辈皇钡刈プツ源⒚洌苁俏薮氲难印�
楼主的功力深不可测,自然不可能听不到屋外的动静,过了一刻钟还没见他安静下来,眉头一皱,道:“要么进来,要么滚远点。”
吓?屋外的人吓了一大跳,左右张望了一下,明白屋里的人是在跟自己说话之后脸上顿时现出喜色,“喔——”了一声之后忙推开门钻了进去,然后小心地将门合上,回转身时正对上青年看过来的眼睛,心中一跳,唤道:“小天——”
小天,自然就是吉盛天,两年前他在地宫时本以为自己被困死了,却被眼前这个男人的一句“有进来的路自然有出去的路”的话提醒了,当下接着他潜水过了进来时所经过的那个石室,轻而易举地用宣武帝配剑劈开了那道木制的门,果然那后面就是一条通向山外的秘道。说来好笑,那本是很容易发现的出口,却因为宣武帝留下的手书而白白被困了三年时间。不过也正是这三年时光,天宇的人大约以为他被困死在青岩山中了,自是早就放弃了对那里的搜寻,也没有在全国下达对他的通辑令,倒令他轻松地便回到了南地,寻回以前建立的微薄势力,又加以发展,以达到了如今的规模。
大牛见儿子只看着他不出声,心里“呯呯呯”地跳个不停,这两年小孩儿的身量又拔高了许多,才十八岁就已经比他高了半个头,在外面多种多样的食物的滋养之下身形也变得更为挺拔健硕,使得他这个做爹的站在他面前总提不起长辈应有的气势,反倒像他儿子似的,从不敢顶撞他(话说,大牛兄,乃在小天童鞋还小的时候也不敢顶撞他吧?)。“小天——”大牛眼神游移,“那个,那个——”
吉盛天的脸沉下来,冷冷地道:“说。”
“呃——”大牛压下夺门而逃的冲动,结结巴巴地说出自己前来的目的,“你,你,今天,呃,是不是,呃,要打一个姑,姑娘啊?”
吉盛天的眼神暗了暗:“谁去找你了?”
“你怎么知道的?”大牛一愣之后忙捂住自己的嘴,眼巴巴地看着自家儿子,很希望他没听到自己说的话,可显然那是不可能的。对上儿子一双了解的眼睛,他在心里默默地对那个男孩道歉,明明他有叫自己保密的,可自己却一下子就说漏嘴了,真是不好意思。
“哼!”吉盛天自然是不屑于回答这种白痴问题的,他倒是奇怪自己那几个堂主护法为什么要多此一举地要这个人保密?反正只要这人一来找自己他就会明白是谁透露了这种事出去。“你想帮她求情?”
大牛小心翼翼地看着自家儿子,期翼地道:“可,可以不打吗?”
吉盛天眼中闪过一抹讽刺,随即道:“可以。”
“真的?”大牛顿时喜笑颜开,不怕死地上前拉住小孩儿的袖子摇了两摇,道,“小天,你真好!”(汗,怎么那么像小情人跟奸夫撒娇?)
“你替他挨就是了。”吉盛天抛下一个炸雷。
“啊?”大牛怔了一怔之后反应过来,傻眼了,“为、为什么啊?”
吉盛天没有给出答案,冷冷地看了他一眼,道:“卫祥。”
“楼主。”灰衣男子从暗中闪身出来,恭身行礼。
“带去叛血堂,传我命令。”
“是。”卫祥一礼之后提了呆站在旁边的男人便闪身出了书房,而迟钝的大牛童鞋直到被提出了很远才明白过来似的,凄惨地叫道:“小天——”
吉盛天冷冷地从鼻子里发出一声“哼”,拾起之前停下的文书继续办公。
***
结果大牛就真的替冯欣挨了那三百下杖责,当然,这三百下比之叛血堂正宗的杖责差得甚远,仇盛不能对违了教令的秘血堂主循私,却不得不对这个他所不喜的传说中暴虐淫乱的前吉禅国主留情,毕竟再不愿意承认此人也是楼主的父亲,楼主能让他活到现在就不可能放任他被自己打死的。十分的力道也只命人使了两分,可就是这两分也打得大牛皮开肉绽,哭爹喊娘,被人惨兮兮地抬回了德园。
望着一路惨叫着被抬走的男人,逃过一劫的冯欣却没什么开心的表情,反倒满是疑惑:“这个人真是那个人吗?”
她这话问得有点没头没脑,可在场的人都明白了他的意思,这时男人已被抬得远了,可隐隐的还是有哭喊声传来,可见那人的声音到底有多大。
崔胜收回远眺的眼,道:“你该相信楼主不会连自己的父亲也不认得。”
揉了揉额头,冯欣不屑道:“一点小伤就哭成那样子,简直不敢相信他曾经统御一方领土。”虽然是被那个人救了,她却没有一点感激之情,反而很是鄙视地道,“真不明白楼主,怎么会认这种父亲?还留他在楼里供养着,不如丢出去任他自生自灭好了!”
赫连明心道:楼主可没有认那个男人做父亲,从他从来不曾叫过那人一声就可以看得出来,只是以楼主的性格会带着他一路从天都逃出来,现在又将他养在楼里倒真的是很奇怪,到底为什么呢?
***
复血楼位于支天山脉尾部的山尾峰上,整个建筑依山而建,坐北前南,正南方是楼众集会处理事务的忠义堂,紧挨着忠义堂的是楼中占地最小人数最少的回血堂,之后是一大片桃花林,林后便是楼主吉盛天的平园,东侧由南向北分布着左护法所居的明园,秘血堂,和赤血堂,西侧则是右护法所居的毅园,练血堂,和叛血堂,而德园却要在平园后面的那一大片树林的还要后面去了,也就是整个复血楼最北面,紧挨着山壁的地方。
一行人将哭天抢地的大牛抬回德园扔在地上,看也没看一眼这替人受罪的倒霉男人便转身离去,无人理会的大牛只得忍了痛寻了平时自己捣鼓出来的土药艰难地往腰臀上涂了才趴到床上,偏着头看着地上发呆。德园说是一个园子实在有些不恰当,不过是土墙围了一大块地方,又在墙里修了两间房子,也没什么摆设,就算日常用品也是很粗糙的,更没有什么服侍的人了。其实大牛也不需要什么服侍的人,自从三年前跟儿子做了那羞人的事情之后,他的身体便慢慢好了起来,到现在虽然没有前世那个身体那么健壮,却也与一般人无异,平时的生活什么的都可以自己打点,只是以前还不觉得什么,这时候身上痛得他睡也睡不着,再对着空荡荡的屋子,突然就觉得有些凄凉。
吉盛天就是踏着这凄凉的目光走进德园的,这时天已大黑,处理了一天的公务的他却没有应有的疲惫,双目仍是精光四溢,也对比得床上的人更加病恹恹的。“啧啧啧,真惨。”
用平板的语气说着幸灾乐祸的话,反而更加气人,大牛也真是被整得惨了,对于捧在心尖上的儿子也生了一股怨气,破天荒地将头扭向床里边,不去理会他。
“还生气了。”吉盛天慢悠悠地走过去站在他床边,道,“你救了别人一命,也不见她有丝毫感激,竟然就将救命恩人丢在这里不闻不问。”
“俺救人又不是为了要人感激!”大牛猛地扭过头,愤怒地看着他。
吉盛天倒也不恼,就那么淡淡地看着他,直看得他脸上的怒色渐渐淡了下去,讪讪地将头挨回枕上方才开了口:“我要你做的事全都忘了?”话已出口,却半晌不见他回答,带着几分威胁地“嗯?”了一声。
“没有。”大牛视线粘在床单上,仿佛突然觉得这张原本觉得太过艳丽的床单变得好看了一样,嘴里闷闷地答道。
“喔?”吉盛天干脆一屁股坐在他边上,饶有兴趣地道,“说来听听。”眼中闪过一丝危险的光。
“不准说‘俺’,不准出院子。”大牛声音还是闷闷的。
“还记得。”吉盛天视线扫过他盖在身上的被子,“那还记不记得我说过,如果犯了,将如何惩罚?”
大牛这才感觉到危险,身体微微一颤,却咬着嘴唇不出声。
吉盛天看着他的表情,戏谑道:“看来是记得的。”说完伸手就去掀他的被子。
大牛身子一抖,猛地一个翻身,忍住腰臀处传来的剧痛,一脸哀求地看着他:“小天——”
吉盛天挑挑眉,没有出声。
“可是,俺,不,我,我受伤了……”大牛急得眼泪都快下来了。
“你自找的。”吉盛天冷酷地丢下一句话,毫不留情地一把掀开他紧紧抓着的被子,尔后往床柱上一靠,命令道:“过来,主动取悦我。”
以下河蟹……
神秘来客1
代人受过的大牛这一次当真被弄得很凄惨,拖着被鞭打得满身青紫的身体再被吉盛天用他最难受的姿式进入了一遍又一遍,中途便撑不住地晕了过去,但是很可耻的,当第二天他醒来发现自己被清理得干干净净,背上也上了香香喷的药膏时,心里那一丝丝委屈立即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满心的感动和喜悦——小天还是关心他的!(完全忘记了自己凄惨的状况是拜何人所赐!)
儿子给擦的药自然不是他自己捣鼓的土药可以比的,只是过了一夜,大牛身上便不再如一开始那般痛了,再加上心情很好,足以让他认为自己要不了两天就会痊愈了,唯一美中不足的大概就是后方隐秘的地方有些不适了。此时已是太阳高挂,大牛撑着身子从床上下来,脚方落地便听到一阵“咕咕”声,他摸摸肚子,这才想起自己上一次吃饭已经是昨天早上的事了,只得把满腔的感动之泪压了又压,扭着难看的八字步出门弄吃食去了。
德园地处复血楼最偏僻的北边,被三面光秃秃的山壁半包着,阳光算不得很好,却也能种活些东西。大牛本就是种地出生,是一刻也闲不住的主,也是见不得荒地的人,早在一年多前刚搬来的时候便央了儿子命人买了些种子回来,将整个园子开垦除草,细细分了几块地种了各式的瓜果疏菜,又放养了一批鸡鸭鹅,倒是给冷清的日子添了许多生气。洗米下锅,大牛塞了几块大柴在灶膛里便急急忙忙拌了盆糠料往园子东南角的笼子赶去,饿了一天有多的家禽看到主人都打木条之间伸长了脖子出来叫唤,大牛忙抓了一把食料撒进去,引起一阵翅膀扑腾声。大牛见了这景象先是乐得咧大了嘴,随即便有些忧郁,这些小东西看了他还会“咯咯”“嘎嘎”地叫几声,也不知道他那宝贝儿子什么时候能叫他一声“爹”?(牛牛,光想是没有用的,想叫小天天叫乃“爹”就要主动出击啊!把自己打扮得闪亮一点,然后主动一点,再用眼神那么一勾……咳,河蟹,河蟹……)
喂好鸡啊什么的之后,锅里的稀饭也差不多熟了,大牛就着咸菜喝了三大碗,摸摸撑得肚子微微鼓起,长吁了口气,正要去洗锅洗碗的时候猛地学得有些不适,头一偏,正见到一个漂亮的大姑娘站在院门口瞅着他,不由愣了愣——有小天的吩咐,这个院子除了每月会有人来送米和一些日常用具,可再没人踏足过。见那大姑娘面色有些奇怪,大牛踌蹰了片刻,结结巴巴地开了口:“姑,姑娘,你,你有什,什么事?”
他却没想到这个“大姑娘”正是害他挨了一顿鞭子的人,冯欣等几个堂主都是在吉禅亡国之前便跟了吉盛天的,光凭关于这个前吉禅国主的传言便足够她们讨厌这人了,在见识了他昨日“优美动听”的惨叫声之后,对这个“传说中”的楼主之父更添了几分厌恶,只是好歹人家也是为她受的罪,不来看看也说不过去,却也不甘不愿地拖到了近午才过来。皱了皱好看的眉,冯欣语气不太好地道:“你没事?”这话说得,倒像是在说别人“你怎么没死?”似的。
大牛倒也不恼,好脾气地笑笑:“我没事啊!”看来昨夜儿子的教训还算有用,至少他没有一张口就吐出个“俺”字。
看他笑得傻子似的,冯欣毫不顾忌地将鄙视表现在脸上,不善的目光从头到脚在他身上溜过一圈,最后定在他捧在手中的大海碗上,撇撇嘴,道:“吃得可真不少!”那么一大碗吃得干干净净,连颗饭粒都没有,他是猪啊?(如果冯大堂主知道她眼里的‘猪’足足吃了三海碗会有什么反应?)
大牛脸皮本来就薄,被一个大姑娘这样一说,顿时整张脸红得跟某种动物的PP一样,怕是放个鸡蛋上去也能给烤熟了!湿漉漉的眼睛眨了眨,小声地嗫嗫道:“是,是挺多的——”
这样一副被欺负的小绵羊模样使得冯大堂主一噎,什么刻薄话都再也说不出来,恨恨地瞪了他几眼,冷哼一声,扭头就走。美丽的倩影很快消失在树林之间,只余下空气中的些许轻香以及呆立原地正摸不着头脑的大牛同学——这个大姑娘到底是来做什么的?
***
自那日在院子见过那个漂亮的大姑娘之后,就像打破了某种看不见的什么东西,大牛居住的这个偏僻无人问津的小院逐渐热闹起来,每日都有一个或数个不认识的人前来,也不进院子,就站在院门外张望。这些人有的会跟大牛搭几句话,问他些关于己身的事情,老实的家伙都一五一十说了,也有些人从头到尾一言不发地看着他,直看得他全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才走。大牛总觉得有什么不妥,可他又说不清楚哪里不好,以他的性格又做不出不理会人或是赶人走之类的事,心里便分外盼着儿子前来好问问他,可平常隔个三五天最多七八天就会来一次的人却足足半个月没有见到人影,他又怕死了儿子的“惩罚”,不敢随意地出院子,只好忐忑不安地等着。
吉盛天一进院子便见到那个男人傻站在鸡舍前面,盆都空了手还一动一动地往外抓东西,心念一转间便明白他是在为最近那几个人的行为而烦恼,却恶劣地假装不知,很是不经意地道:“你给鸡喂什么?”
吓?!大牛惊得手一松,铁盆跌在地上发出一串“噼哩啪啦”的刺耳声音,想也没想地就要去捡,腰弯到一半猛地醒起刚才听到的声音有些耳熟,动作一顿,惯力的冲击下差点扑到地上去,手忙脚乱地站好了,这才看向来人,惊叫道:“小天!”
这个男人真的是什么时候都那么好笑!吉盛天心里“嗤”了一声,明知故问:“怎么?才十几天不见就认不得我了?”
大牛不好意思地抓抓头,他知道自己的反应是有些夸张,但他这次真的很,很,很期盼见到小天,虽然每次他来都要压着自己做那种事。
瞧他那傻样!吉盛天暗骂,心情却意外地轻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