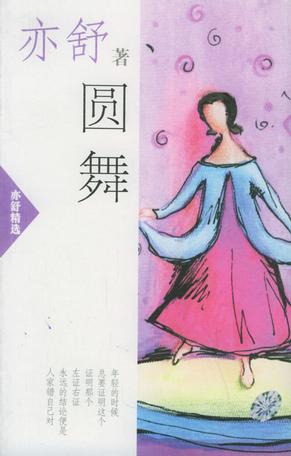圆舞-第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新居不一样,一点尘都没有,两个女工寂寞至死,只得不停地东抹西抹,永远在抹。
清洁溜溜,令人惆怅,太整齐了,家似酒店。
一星期有时见不到傅于琛一次。
我也寂寞。
周未招待同学来游泳,有点心茶水招待。她们都已有异性朋友,故此打扮得花枝招展。
那时流行小小的比基尼泳衣,粉红色底子,苹果绿大圆点,为求刺眼,在所不计,头发梳得蓬蓬松松,缀一只小蝴蝶结。
但我已开始穿黑色。
傅于琛买所有的衣服,都是他挑的。
都是在膝头以下的宽裙,料于软熟,有风会贴在腿上,我同时代百分之百脱节,同学的裙都仅仅遮住臀位。
无论傅有多忙,都不忘替我打扮。
头发,不准熨,必须长过肩膀,不给穿高跟鞋,双双鞋都是小圆头浅浅的,像舞蹈鞋。
游泳时,通常穿一件头黑泳衣,梳马尾巴。
像来自另一个星球。
所以男孩子都不来追我。
女同学见义勇为,替我化起妆来,但每次回家,总要擦得干干净净,太像个贼,我厌倦。
也有给傅于琛抓住的时候。
他并不骂。
但三日后带回来一本画册,叫我看。
画家是毕加索,画叫马尾女郎,模特儿是碧姬芭铎,傅于琛说:“这是你学习品味的时候了。”后来都没有画过眼睛,但一直醉心各式各样的口红,一整个抽屉都是,密密麻麻,几百管。
喜欢搜集东西,是因为没有安全感,这是后来心理医生说的。
下午,同学散去,回家吃晚饭,趁泳池换水前,独个儿游了十多趟。
已经很疲倦,天又近黄昏,拉住池边想爬上去,竟没成功,滑下,再试一次,又乏力落水中。
有人伸出他的手。
我抓住,被他拉上去。
水溅湿他灰色麻布西装。
“你是谁?”我问。
“你想必是傅小姐了。”他微笑。
我罩着大毛巾,坐下来。
时间近黄昏,无论什么都罩着一层灰网与一道金边,看上去特别有气质,忽然想到自己也必然如此,不禁矜持起来。
这时傅于琛缓缓走出来,闲闲地说:“哦,你们已经认识了。”陌生人笑说:“让我介绍自己,我叫邓路加,是傅先生的助手。”忽然之间,我一言不发走回屋内,像是被得罪那样。
更衣下楼时,邓路加已经离去。
“怎么样?”傅于琛问我。
“你指那人怎么样?”“是。”“是你故意安排的?”“是。”“为什么?”“你需要朋友。”“自己会找。”“不见你动手。”“谁要你安排,你以为每个人都是棋子?”“承钰,不准用这种口气说话。”“我不喜欢他。”“你还未认识他。”经过安排认识的男朋友,多么反浪漫!
太令我气馁,为什么没有人追呢,如果男孩子排队在门外侍候,傅于琛就不敢做这种杀风景的事。
向往偶遇,在极端不可能的情形下,他见到我,我看见了他,心碰碰地跳,手底出汗,知道大限已至……多么好,将来就算痛苦也是值得的。
忽然想起来,“我母亲第二次婚礼记得吗?”“当然,我认识你的那一天。”他微笑。
“你为什么在场?”“我是她的老同学。”“如果你没收到帖,或是收到帖子没空去,或是到了那里只与新娘握手就走,我们就见不到了。”傅于琛接下去,“当日我的确另有约会。”“女方爽约?”“是。”“谁那么大胆?”我觉得不可思议。
傅于琛眼神温柔,看着我微笑。是,在我心目中,他是最好的,没有人应该拒绝他。
他说下去,“当时遗产问题并未明朗,我不过是一个不务正业的浪荡子,谁会对我忠心耿耿?”“我。”“你只有七岁。”我也笑。
“但必须承认那已是极大的鼓励,”傅于琛回忆,“足令我恢复信心。”“那女生是谁?”“不记得她的名字了,只知道是一个酒店的经理。”“她一定后悔终生。”我夸张地说,“直至永远,她都会对旁人说:大名鼎鼎的傅于琛,他曾经约会我,但我没有去,呜呜呜呜。”傅于琛笑意便浓,他说:“真的,这简直是一定的。”我俩哈哈大笑起来。
傍晚,只要他有空,便开一瓶酒,用乳酪送,谈至深夜。
“可曾对我母亲有意思?”他摇摇头,“学生时期,她是个可爱的女生,可惜我们不接近,也许我较为孤僻,且又不是高材生或体育健将,谁会对我另眼相看。”“接到帖子,只想:第二次结婚了,倩志永远要出风头,什么都要抢闸做。到那日,闷闷不乐,无处可去,只得到婚礼去呆着。”我默默地听。
“那真是一生中最黑暗的一段时期,”隔一会他说,“承钰,你是我的小火焰。”我笑。
永远不会告诉他,开始喜欢他是因为他寄来的明信片上有美丽的邮票,就那么简单。
“晚了,睡吧。”“我不要再见到那个邓路加。”傅于琛摇摇头。
我仍保留那张甫士卡。
我有一只年龄比我也许还大的洋铁饼干盒子,那张明信片在它里面保存着。
因为生活太无常,故此努力保留琐碎的东西,抓住它们,也似抓住了根。
将来老了,将会是那种买十个号码收租的老太婆。
邓路加时常来。
有时一个人坐在偏厅看书,老厚的一本英语小说,一下子看完。
没有人睬他,傅于琛少回来,我则做功课,只有佣人隔一会替他换杯热茶。
肯定邓路加视这为工作的一部分,一边坐一边收薪水,何乐而不为,多没出息。
他并没有缠上来,可见对我并没有发生真正的兴趣,这太过令人懊恼,过了几个星期,反而与他攀谈。
听见我同他说话,邓合上他的《鼠阱》。
“好看吗?”“精彩绝伦。”“能借给我吗?”“请便,我再去买。”“每次你只来这里读小说?”他微笑。
“你不觉得浪费时间?”可恶,他仍不回答。
“告诉我,傅于琛的女朋友长得怎么样?”邓路加诧异我直呼父名,扬起一条眉。
过一会儿他说:“不知你指哪一位?”非在他嘴里得到消息不可,一定要把他的嘴唇撬开来。
叹口气:“你总明白孩子对后母的恐惧。”邓路加略略动容。
“倘若她不容我,怎么办呢”“脸上的忧虑倒不是假装的。
“不会的,马小姐人品很好。”姓马。
傅于琛连这个都不告诉我。
“她为人开通吗,是不是你们的同事?”我说。
“别太担心,傅先生自然有所安排。”邓先生说。
我深深叹息一声,两只手托住头,像是不胜负荷。
“你还是小孩子……我带你去看部电影如何?”真被他逗乐了。
原来邓以为他担任着一个保姆的角色。
“你的任务到底是什么呢?”他老老实实地说:“带你出去玩,令你开心,开头还以为你至少已中学毕业,谁知还小白袜,棒棒糖,你有多大,十五?”“是,我还是小孩子,唉,多么希望可以长大成人。你呢,你什么年纪?”“二十三了。”赶紧作一个艳羡状,“真了不起,你可以同二十多岁的小姐来往。”“我喜欢比较成熟的女性。”“我也喜欢比较成熟的男性。”他腼腆地笑,以为我指的是他。
太妙了,简直是最佳娱乐。
“那么你心目中的人,该比马小姐大?”“不不,约比她小一点,不过似她那般气质差不多。”“她时常到写字楼来吧?”“一星期总有一两次来找傅先生吃中饭。”“照你所说,你选择的女性,都是正派的,像马——她叫什么名字?”“马佩霞小姐。”“谢谢你。”我站起来。
“你到什么地方去?”“做功课。”“不看电影?”“不了,”我温和地说,“你说过,你只喜欢成熟的女性,我只得十五岁。”“可是,”他怔怔的,“与你说话蛮有意思。”“你再坐一会儿,不客气。”我说。
自邓路加身上,已得到很多。
马佩霞。
这名字不错,不知道她长相如何,人同名字是否有些相似。
佩霞。把云霞带在身边,霞是粉红色的云。
第二个星期,趁有空,我就到傅氏办公大楼去。
预先也没有通知,由邓路加到接待处把我领进去。
他兴奋莫名,“你来看我?”我摇摇头。
“哦,”他冷静下来,“你来见傅先生。”“是。”“他在见客。”“我等一下好了。”邓请我到会客室。
我还穿着校服,拎着书包,这是我第一次踏入傅于琛事业的天地,大人的世界。
老实说,根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来,总而言之,马佩霞到过这里,我也有权来。
坐下后,不禁悠然向往,在办公地方,连邓路加都变了样子,不再是听傅于琛摆布的一个呆瓜。
在岗位上,他完全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指挥如意。
每个人都静静做着他们应做的事,只见脚步匆匆滑过,他们低声说话中交换的术语都是我听不懂的,似一种密码。
女职员打扮得高贵艳丽,全部套装高跟鞋,化着浓妆,发式合时。
我很心折,傅于琛就是这里的统帅,他控制全间办公大楼,他是脑,他是神经中枢。
女性对异性的虚荣崇拜悠然而生,感觉上我是他心爱的人之一,沾了不知多少光。
心中不平之气渐渐消失。
邓路加说:“这个会,要开到六点钟。”手表说四点半。
本来等下去也无所谓,但忽然觉得自己渺小,这不是闹意气使小性子的地方。
“我先走了。”我说。
“有重要的事吗?”邓路加有点不安。
我摇摇头。
忽然想起来问:“马小姐时常等他开完会?”邓笑,“才不会,只有傅先生有空时,马小姐才出现。”我略为失望,想法竟同我一样哩,也这般为他着想,你瞧,能干的男人往往得到质素高的女伴,因为他们有选择的机会。
“我送你回去。”邓说。
“不用。”“我去取外套,等我一分钟。”我没有等他,独个儿出办公大楼,到楼下马路,仰头看这座高三十层的大厦,大厦灰色的现代建筑衬着亚热带碧蓝的天空,美得不能置信。大门上有银灰色金属字样:傅厦。
我叹口气,叫部车子回家。
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留意傅于琛的事业,细读报章财经版上有关傅氏的消息。
我不想做他家中一名无知的妇孺。
那日他回来吃晚饭。
问我:“路加说你下午到办公室来过。”“是。”“想参观我工作地方?”“是。”“改天约个时间,我叫路加带你逛,我们有三百多个员工,近百部电脑,写字楼占地面积有三万平方米。”“你现在很有钱吧。”他一呆,笑出来。
我看着他。
傅于琛温和地说:“有钱?有足够的钱,早就不做了。”“但你早期太浪荡,你自己说的,所以下半生要拼命工作,弥补过去少年的不羁。”“你倒是很了解我。”他有点意外。
“你一定富有。”“富足是一种心理状况,最富有的是满足的人,富有与金钱并无大的联系,承钰,这一点你要记得,三百亿与三千亿有什么分别。”“但贫穷太可怕,”我说,“我差些被赶至马路睡觉,记得吗?”“那是多年之前的事了,我要你忘记它,永永远远把这件事自你脑袋驱走,好不好?”我苦笑,“恐怕一辈子都记得呢,从没觉得那么凉那么怕,从此之后,再也不怕蟑螂蚂蚁毛虫这些东西,只怕被赶出屋子。”他不以为然,“只要有我在,你不必忧虑。”“但是……你会结婚。”他很狡猾,“你也会结婚。”“你真认为我会结婚?”“当然,女大当嫁。”“嫁给谁?”“大好青年。”“像邓路加?”“路加有什么不好?人家是世家子弟,邓氏五代住在本市,祖宗做过清朝的官,曾祖是总督的幕僚,并非一般暴发户可比。”“我不关心。”傅于琛一直说下去:“邓家托我带路加出身,他才到我处来做一份差使,你别看轻他,将来他的王国大于傅氏。”我忽然想起,“你呢,你为什么一直流放在外?”“我的故事截然不同。”“你从来没说过。”“你一直没问。”“傅家有些什么人?”“我还有三个姐妹”“她们在什么地方?”“都住在本市。”“你从来不见她们。”“我们不是一母所生。”“我明白了,你是私生子,你父同你母没有正式结婚,他们姘居生下你。”“承钰,你的坦率时常使我难堪。”“是不是?”“是。”“他们对你不好?”“家父很怕大太太。”不用再说了,他一定吃尽苦头。
“你母亲呢?”我说。
“她去世早。”傅于琛说。
“你是孤儿?”“一直是。”“我也是,”我拍胸口,“我也一直是孤儿。”“你说得不错,承钰,我们俩都是孤儿。”我与他沉默下来。
过一会儿我问:“后来呢。”“在我三十二岁那年,家父去世。”“那是我认识你的那年。”“是。”“发生了什么?”“他把遗产交我手中。”“你不是说他怕大太太?”“他死了,死人不再怕任何人。”“那个老虔婆还活着吗?”“活着。”“啊呀,她岂非气得要死?”“自然,与我打官司呢。”“她输了。”“我持有出世纸。”他微笑。
“所以你们父子终于战胜。”“可以那样说。”“你们付出三十三年时间作为代价?”“也可以那样说。”“快乐吗?”“我所做的,只不过是我必须做的,与快乐有么关系?”他叹口气,“事实上世上一切同快乐有么关系?”“你与我在一起,也不快乐?”“承钰,你是我生活中唯一的安慰。”“是吗,唯一的?马小姐呢?”他怔住。
我看着他,他也看着我。
“谁告诉你她姓马?”我不出声。
“你不要碰她,知道吗?”我大大地觉得委屈,“你保护她,而不是我?”傅于琛冷笑,“我太清楚你的杀伤力。”“我——”他已站起来离开,不给我机会分辩。
我怒极,伸出脚大力踢翻茶几,茶几上盛花的水晶瓶子哗啦一声倒下,打在地上,碎成亮晶晶一千片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