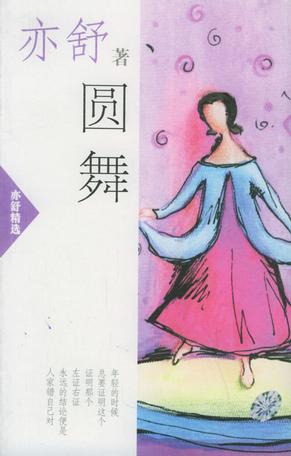圆舞-第1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她问:“马小姐介绍你来?”“是。”“什么事?”“胸部撞了一下,痛不可当。”“请躺下,我替你检查。”她的手势很纯熟,我忽然警惕起来,这不是检查乳癌?同杂志介绍的步骤一模一样。
我留意医生的表情,她很安详,我也松弛一点。
她已经觉察到,“不要紧张,身子干么抽搐?”“没事吧。”“这里有一个脂肪瘤。”我看着她,希望在她双眼中,找到蛛丝马迹。
“我们依例抽样检查一下。”我一骨碌自床上跳起来,“我不过是来取两颗止痛药,没想到会有这样的麻烦。”“很简单的——”“我不想做。”我扣钮子便走。
拉开医务所的门,便看到马佩霞,我恼怒地说:“你的医生朋友是个郎中,我来止痛,她却几乎没推荐我把脑袋也换掉。”医生没有生气,马佩霞却白我一眼。
我莫名其妙地激动。
医生过来说:“不要害怕。”我害怕,怕什么?拉着马佩霞就走。
到街上,风一吹,人醒过来,问马佩霞:“你怎么来了?”“来看你可需要照顾。”“你原不必这样。”我握住她的手,“快要做新娘子了,忙不过来的苦,还得抽空出来照顾我。”“怎么忽然客气起来。”她微笑。
我没有回答。
“承钰,我一直想,如果没有我,你同傅于琛不至于到现在这样吧。”我一怔,失笑,人总是离不开自我中心,连温柔谦和的马佩霞都不例外,她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了,我不忍告诉她,她不过是傅于琛芸芸舞伴中的一名,即使舞姿出色,他也不会同她过一辈子。
当下我微笑道:“我们现在不是很好吗?”她不言语。
“我疲倦,要回去休息。”“我送你。”我没有拒绝。
车子到门口,马佩霞问:“要不要我上来陪你?”我摇摇头。
上得楼来,用锁匙开了门,看到客厅里坐着一位女客。我一怔,这是谁,我并没有约人。
女客闻声转过头来,见到我,立即扬声笑说:“我是乔梅琳,不请自来,请勿见怪。”我十分意外,多年来与老一代的人相处,已经学惯他们摸哑谜,很少接触到如此开门见山的人。
“嗨,”她说,“好吗?”乔梅琳比晚上浓妆的她要年轻好几岁,一双眼睛晶光灿烂,照得我几乎睁不开眼来。
她精神这样充沛,像是服食了什么药似的。
我疲倦地说:“乔小姐,今日我没准备见客,精神也不好。”她立即问:“有什么事,我能否帮你?”多么热情,而且表露得那么自然率直坦诚,我深深诧异,对我来说,相识十年,才可以成为朋友,而敌人,敌人要二十年的交情才够资格。
乔梅琳笑着说:“我一直希望能够做得像你那样国际著名,成为哈泼杂志选出来的美女。”“这两年有色模特儿大大抬头,风气所钟而已。”她上门来,到底是为什么?
“我路过这儿,顺便探访你,如果你不介意,我们可否喝杯茶?”“为姚永钦吗?”我为她的坦率所感染。
她一怔“不不不不不,”一叠声地说,“不是我夸口,似他那样的公子哥儿,本市是很多的,乔梅琳不必为他担心事。”我笑问:“那么你上来,是特地为了要与我做朋友?”“有何不可呢?不是已经说过,我仰慕你已经有一段时候了。”我去开了门,“有空我们吃茶吧。”“如果你真的关心姚永钦,那么让我告诉你,他昨天下午已经同另外一位小姐到里奥热内卢度假去了。”我喜出望外,随即压抑自己,“啊是,里奥在这种气候可美得很呢。”“我希望你信任我。”“再见。”我在她身后关门,问女佣为何放陌生人进屋。
女佣大不以为然,“她是乔梅琳,她不是陌生人。”我倒在床上休息,却不能完全松弛,因为傅于琛的缘故,他今天要来与我摊牌,曲终人散,舞池只剩我们两个人,我想听他要说什么,我等了这么些年。
朦胧间只觉得女佣像是又放了人进来。
客人直入,到我床边推我,我睁开眼睛,是马佩霞。我取笑她:“欧阳夫人,你怎么缠上了我?”“承钰,不要再说笑话。”是傅于琛的声音。
永远的三人行,马佩霞说什么都要在要紧关头轧一脚,真正可恨。
“什么事?”傅于琛看着我,“承钰,我要你即刻入院检查。”我一怔,原来如此,“喂喂喂,别这么紧张好不好。”转头看马佩霞,“你那道上的朋友说了些什么?”“她坚持你做切片。”我坐起来笑问:“为着什么?”“穿衣服,”傅于琛说:“不要与时间开玩笑。”“我不去。”“承钰,只需二十分钟,我与你在一起。”“你应该与欧阳在一起度蜜月。”“你出院后我自然会去。”“我要与傅于琛说两句话。”“好,我在外头等你。”我点起一枝香烟,看着他,“你又找到借口了。”“我不明白你指什么。”“你后悔了,又决定在音乐中留恋下去,可是?”他温柔地说:“废话。”“我自医院出来,你又不知该同谁结婚了。”“同你。”我凝视他。
“你不学无术,除出结婚外,还能做什么。”“我以为你永远不会问。”“我要等你长大。”“我早已经长大。”“不,时间刚刚好,”他停一停,“怎么,还要不要同我结婚?”“那是我自七岁开始唯一的宏愿。”“是,我记得我们相识那年,你只有七岁。”“当时你的舞伴,是一位黄小姐,叫伊利沙伯。”“你记忆力真好,”他叹口气,“她嫁了别人后生活愉快,养了好几个孩子,都漂亮如安琪儿。”他对黄小姐是另眼相看的。
“你心中再也没有事了?”“没有,心病已经完全痊愈。”“那么我们即刻出发到医院去。”我还在犹疑。
“看在我份上,纯粹给我面子,可好?”我换上衣服,马佩霞看到我们,按熄烟火站起来,说道:“也只有你能够说服她。”我已疲倦,华丽的跳舞裙子已经皱残,脚有点胀,巴不得可以脱掉鞋子松一松,我想坐下来,喝杯冰水,傅于琛建议得真合时。
医生替我局部麻醉,我睁着眼睛,看着乳白色的天花板,许多事,都得独自担当,我的面相,我的生命,我的痛苦,都属于我自己。
母亲给我一个好看的躯壳,借着它,生活得比一般女子灿烂,我应当感激。
看护垂询我,“一点都不痛,是不是,好了,你可以起来了,回家多喝点水,好好休息。”“我肯定什么也不是。”她也微笑说:“当然什么都不是,只是买保险。”她扶我起身。
只有傅于琛陪我回家,马佩霞呢。
“她回去收拾行李。今晚去峇里度蜜月。”能够去那么闷的地方,他们多多少少有点真感情。
据我所知,傅于琛从来没有同他任何一任妻子去过那种地方。袁祖康与我也没有,我们尽往人堆里钻,夜夜笙歌,半年夫妻俩也说不到三句话。
在十年前,马佩霞这样快活的结局是不可能的,真感激社会风气开放。事。
我点着一技香烟。
“牙齿都黄了。”傅于琛嘀咕。
我莞尔。来了,开始管头管脚了,那是必然的事。
“一天要抽多少?”“我又没有别的乐趣,吃喝嫖赌全不对我,这是我唯一的嗜好,况且世界将近崩溃,非洲有些人民已经饿了十年,处处有战争,让我的牙齿安息吧。”“承钰,我真不知拿你怎么样才好。”“陪伴我。”“我得到美国去一趟。”“干么?”“去离婚。”啊是,他尚是有妇之夫。
“我一个人做什么?”他微笑,“你有你唯一的嗜好,我不担心。”“快些回来。”他说:“开始限时限刻针对我了。”我们紧紧拥抱。
纽约有电话来分配工作,我说要筹备婚事,暂时不想工作。他们引诱我:“两天就放你走,四十八小时内保证你获得十二小时睡眠,婚前纪念作。”“我要问过他。”“问了第一次以后每次都得问,周小姐,你想清楚了?”“我很清楚。”“他很有钱吧。”“市侩。”“卢昂在这个时节非同小可呢,你一直喜欢金色雨花,站在树荫下,那些金黄色的小花不住落在你头上、脸上、身上,记得吗,金色的眼泪。”“不。”“你这个狠心的歹毒的无义气不识抬举的女人。”“我必须先问过他。”“你呼吸要不要征求他同意?”“事实上,的确如此。”他叫我落地狱,我说你请先。
不想再工作。模特儿生涯并不好过,一天变三个妆的时候,真觉脸皮会随着化妆扯脱,发型换了又换,大蓬头发随刷子扯将出来,心痛有什么用。
而且最不喜欢听见“啊你便是大名鼎鼎的周承钰”,一声啊之后,人们的双眼即时架上有色眼镜,再也看不到实实在在的周承钰,他们的幻想力如脱缰之马,去到不可思议的境界,陷我于万劫不复之地步。
我们都没有朋友,因为没有真人可以生活得如他们想象中那么精彩,一接触到真面目,他们往往有种被骗的感觉,十分失望。
脱离工作,过一段日子,人们会忘记,可幸他们的记忆力差。
夜长而沉闷,电话铃响,我似少女般跳跃过去,“付于心。”我说。
“我是乔梅林。”她真的不放弃,存心要与我接近。
“你觉不觉得坐在家很闷。”我觉得好笑,她会寂寞?
随即发觉不公平,想当然,我们都犯这个毛病,替别人乱戴帽子。
“当然闷,”我换了一个公正的角度说话,“我们在同一只船上。”“要不要出来喝杯茶?”“我不行,我要等电话。”“他出了门?”“是。”“你至少还有个精神寄托。”我觉得与乔梅琳颇为投契,一生人从未接近过同龄女性,她有她的一套,热情、爽朗、自信,毫不犹疑地主动接触反应迟钝的我,难能可贵。
物以类聚,她也是个为盛名所累的女子。
“你要不要过来?”我终于邀请她,“吃一杯蜜糖茶,对皮肤有益。”“我的皮肤糟透了。”乔梅琳的派头比我大,也较懂得享受,驾一辆美丽的黑色跑车,惹人触目。
我笑说:“我什么道具都没有。”她凝视我,“你不需要借力于任何道具。”“你的开销一定是天文数字,”我说,“不过收入也必然惊人。”她坐下来,“怎么样才可以做到像你那样谦和?”“我?我是最最孤僻的一个人。”我笑起来。
“我真的仰慕你,知道吗?”“谢谢你,我也一样,请喝茶。”她趋向前来,握住我的手。
我略表讶异,本能反应地轻轻缩回我的手。
“今天你心情好得多。”她看出来,好不细心,比起我首次见她,心情差得远了。
乔梅琳手上的钻石非常大非常耀目,这也是我没有的,我什么都没有。
她像是知道我在想什么,笑着说:“都是自己置的,没有利用过男人,没有占过他们的便宜。”这我相信,看得出来。
“那次同姚永钦出现,是赴一个制片的约,他叫他来接我。”她还要解释。
我笑了,“梅琳,我想你不必介意了,他在里奥不知多开心,我们真可以忘记他。”“你同他来往,有三年了吧。”“那段日子我非常沮丧,他帮了我许多。”“我知道,当时你胖了许多。”我点点头,“你在杂志上读到?”“是的,所以刚见面,就像认识你良久的样子。”我释嫌,是会有这种感觉的,可惜我不大留意本市的花边新闻,否则可以礼尚往来。
“你的事业在巅峰吧。”我问。
“可以这样说。”“我的却已完结了。”梅琳笑,“你有事业已算奇迹,你从不迫、逼、钻、营、撬、谋、推、霸……你没有完,你还没有开始。”我睁大眼睛看住她。
是是是是,我需要这样的朋友,乔梅琳太好了,区区三言两语,说到我心坎儿里去。
她不但美貌,且有智慧,我越来越喜欢她。
她看看表,“不早了,改天再来看你。”轮到我依依不舍。
她较我独立得多,所以感觉上要比我年轻一大截。
我不能高飞,因为傅于琛是我的枷锁,但我是甘心的。
躺在床上,有种温存的感觉,那许多许多辛酸并不足妨碍什么。
电话一大清早响起来。
这一定是付于心。
“周承钰小姐。”“我是。”“德肋撒医院的王医师。”我坐起来。
“你的报告出来了,周小姐,肿瘤内有恶性细胞,请你马上来一次。”我呆了一会儿,“我马上来。”“一小时内见你。”我只有二十八岁!
我跌坐在地上,痛入心肺。
这不是真的,我从来没有这样恐惧过,紧紧闭上眼睛,接着是愤怒,母亲已经活到五十多岁,什么毛病都没有,为什么偏偏是我,思路乱起来,耳畔充满嗡嗡声。
我想找傅于琛,但他在什么地方?我们一直玩捉迷藏,到最后再也没法子知道双方的行踪。
我一个人到医院去。
“你要快快决定动哪一种手术。”我僵坐着。
“第一种是整体切除。第二种是肿块连淋巴结一起切除,但有可能要接受六个月辐射治疗及六个月针药治疗。”我低下头。
“假如你需要再次诊断,我们建议你迅速行动,不要拖延。”我站起来。
“周小姐,康复的比率高达百分之六十以上,请快些决定动手术,我们可安排你在下星期入院。”“谢谢你。”“速速回来。”我用手紧紧捂着脸,眼前金星乱冒。
我的天。
脚步蹒跚地走到医院门口,听见有人叫我,“周承钰,周承钰。”啊!茫茫人海,谁人叫我,谁人认识我?
我停住脚步,转过头去,乔梅琳坐在一辆开蓬车内向我招手。
我走近她。
她有一丝焦虑,“女佣人说你在德肋撒医院,我找了来,有什么事吗?”我脸如死灰地看着她,“肯定要动手术。”她脸色大变,痛惜地看着我。
我牵牵嘴角。
“上车来,我送你回家。”在车上,梅琳沉实地简单地告诉我,她母亲两年前死于同一症候,经验仍在。
经过六十分钟讨论,我们安排在另一间医院做第二次检查。
梅琳冷静、镇定,办事效率一流,我们没有心情促膝谈心,对白断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