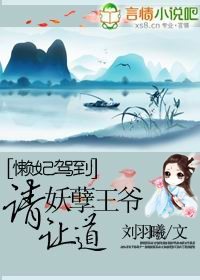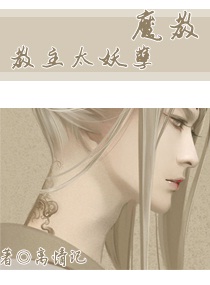妖孽神仙一念间 作者:张迷经-第3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那溅开的白色石末,多像漫天洒下的雪花。剪纸的婆婆也在云端吗?哪一颗云主才是她的归宿?
我不断砸碎云主,手臂已经被震得麻痹,身边累起小山一样的碎屑。最后,剩下的大块白色,唯有白云犬了。
、最终念
看着我手中的岩石,白云犬露出警惕的眼神,让我哑然失笑。
云主皆被砸碎,神仙无法着地,只能永远留在云端喝风饮露。我终于报了仇,畅快的心里明亮如白昼。可是那白昼是那么短,一瞬间就过去了,只剩下漫长的黑暗。
想起魔昂最后一次和我长谈。他说,他看到海洪爆发的那一刻,快活到了极点,可一刻过后,快活的感觉就淡了、手又痒了。我清晰记得他拿到我眼前的指腹与掌心,在月光下布满了深深的纹路和交错的疤痕。
魔昂说,能把过去的一切通通忘掉,也算好事。
我心里想着这句话,站起身,走下陡峭的山坡,向更北的地方走。不知经过几个日与夜,终于走到北方密林。我找到一棵粗壮的松树,掀开一块鳞状的树皮,熟悉的松脂香气瞬间在鼻子前绽放。
松脂在树皮的伤口一点点聚集,凝结成眼眸大的一滴,即将滚落到地。我站到那颗松脂下,让它落在了我的头顶。
白云犬安静地趴在我的脚边。不知名的虫子在枝头嗡嗡鸣叫。偶尔树丛中扑棱一声,飞起一只惊乍的小鸟。松脂悄无声息地在我头顶一丝一绸地累积,终于撑不住散开来,粘稠的液体顺着发梢流下。我闭上眼,感受着松脂缓慢覆盖我的全身。
天黑了、再亮起。开始,阳光透过松脂,还能照进我闭合的眼底。几天过后,凝结的松脂上覆满落叶鸟羽,不再通透,已经变成一块新鲜的垢。
我的感官里只剩下松脂浓浓的气味。那气味牵引着海边的童年。犹记得第一次去北方密林时,我的个头只及得上师父的膝盖。那时他的胡子就已经花白,他跟我说:“北方密林的松脂得天独厚,不但能伸能缩,还能消除记忆。无论是快活的或是憋屈的,通通忘掉,永远不会再记起。”
如今,我已活了百余年。其中,一百年里都是空空泛泛,唯有那余下的几年,也便是最近的几年,日子才变得生动。我遇到了神仙、魔人、白云犬,我经历了天上地下的幸运与凄凉,我重逢了我的哥哥、爷爷与母亲,又一个个与他们离别。过去只是听说过的喜怒与哀乐,终也在我空旷的心底渐渐萌生,却在瞬间荒芜一片。
把这一切都忘了吧。因为魔昂说,忘掉也是一种好事。
我已有多日未眠。此时心中做出决定,终于松下心神,沉沉入睡。
再次醒来时,却是一惊。我只发觉眼皮睁不开,身子被困得难受。挣扎了许久才明白过来,我是在松脂中。只是经过长久一眠,我却淡忘了自己把自己困在松脂中这件事。莫非,松脂是从记忆的顶端开始吞噬?那我接下来忘掉的会是什么?是来北方密林这一路,是砸碎的一地云主,是铺天盖地的浪潮,是巨岛垮塌的轰鸣,然后就是魔昂看我的最后一眼!只是单单预想到记不起魔昂的最后一眼,我已不能忍受!
我在松脂中发疯地挣扎起来。我气愤自己的糊涂决定。我怎么能想忘掉魔昂呢?我宁愿一直痛苦地记着啊。他是我的哥哥,他曾经因为一点点把握就出海来寻我。我已经忘了和他的儿时记忆,再不能抛下这刚刚过去的几个冬夏。
松脂稠密而柔韧,我连眼睛都睁不开,只能无望地扭动着身体,终究浪费掉所有力气。身体空虚得如一张白纸,脑筋却绷直得不敢松懈。我怕我一不留神,就忘了一点儿和魔昂有关的记忆。
我努力去记起魔昂的脸。我在泉水边给他画过那么多张画像的。我要清晰记得他的眼神,他的鼻子,他说过的每一句话,他身上的每一道疤痕。可是,越紧张,情况越不妙。我急得想跺脚,却猛然想起自己虽然周身被松脂覆盖,但脚下却是踩着林地。
我费力地碾动脚底,想碾开脚下的淤泥,腾出哪怕一点点空间。经过不懈地挣扎,腿脚终于获得一丝丝松动。我此时俨然成了一棵树,正在竭力往泥土深处扎根。我多么希望脚下的土壤里蕴含着一颗有力的种子,它能茁壮勃发,从我脚下破土而出,像树苗撑破岩石一样撑破我身上顽固的松脂。
我一边在脚下磨蹭,一边在心中回想魔昂,不敢松懈。心力交瘁中,我的神智渐趋恍惚,终于撑不住泛起迷糊。强作清醒过来,我却莫名感受到脚下有了动静。一线微微的震动似乎正从泥土深处传来。
难道真的有一颗种子在萌发?还是我已经疯了?我轻轻挪动下脚底,那震动登时停住了,似乎被我吓到。我立刻不敢再动分毫,祈祷那颗种子继续萌发,果然隐隐约约中又感受到了脚下的动静,而且似乎越来越近。
嘶——一阵痛楚钻入脚底!我却开心得发狂。多么清晰的痛楚!果然是某种顽强的草木钻出了地面,会是一缕初绽的松针吗?
咦——刚刚扎入我脚底的尖锐东西又抽了回去。然后,我感觉到脚下的动静绕开了我!它在我旁边破土而出。
沮丧之间,一丝光线投入眼底。久违的明亮越来越多,似乎有谁正在拿去粘在松脂上的落叶与鸟羽。
我想看看,努力撑起眼皮,嵌开一道细微的缝。透过昏黄的松脂,我见到一个扭曲的身影。有几分熟悉,却又不是苍耳、双火、花卫或者嘎达,不似任何一个魔人或仙人的形状。直到它把长长的指甲伸进松脂,我才恍然认出——竟然是泉水边的那只硕鼠!
这么一想,果然越看越像。它在松脂外面跑动的身影分明透着一股惯性里的紧张与毛躁。它不断把树枝、石块插入到松脂中搅动,虽没有章法,却也给了我一些协助。在它拿一根大树棍把松脂搅得扭曲变形时,我总算在手边找到一处薄弱的松脂层,把拳头顶了出去。
一直折腾到夜晚,我才算从松脂中解脱。虽然身上还沾着余脂,但站在地上却是前所未有的轻松。明黄的月亮挂在夜空,而对于我来说,洒在我身上的不是月光,而是与魔昂的记忆。我长长叹口气,有种失而复得的踏实,回想之前的自己真是太贪心,明明已经拥有过那么深刻的过去。
“真的是你啊?”硕鼠瞪着豆样的小眼珠呆愣愣地盯着我,小小的嘴巴猩红如初。
我勉强一笑,算是回应。
它用长长的指甲碰碰我,迷惑地问:“你是怎么了?跟过去好像不一样。”
我抬头看看月光,却是和多年前一样颜色。低头一瞥,白云犬还在一球松脂中挣扎,赶紧把它拎了出来。
白云犬好奇地绕着硕鼠闻了闻,总算没有忘记它。我才想起问硕鼠的来路。
硕鼠紧张兮兮地说:“你还记得我在泉水边挖洞的时候,不小心把那块石碑挖倒了吧?”
我记得,我曾把歪倒的石碑洗刷一遍又重新安插。
硕鼠瘪瘪小嘴,难过地说:“从那时起,我就常常做噩梦。梦到过那个想挖我眼睛的魔人,还梦到过一些我也不认识的。就在前几天,原来和你住一块的那个老头也跑到我的梦里来了。”
“是爷爷吗?”我想起了泉边的青包。
硕鼠点点头说:“他要我挖洞,还让我看地下的样子,给我指方向。他说出土时,一定要选在有脚磨蹭声音的地方。他样子那么可怕,我不敢不听啊,就一直挖过来了。”
原来是爷爷在托梦给硕鼠来帮我啊。我记起爷爷走时,身体在瞬间苍白如纸,魔昂挖出一个土坑让爷爷安息。而魔昂走时,只留给我一个眼神,我也应该去大海中把他的身体找回来才对。
于是,我告别硕鼠,离开松林往南走。如今已是暖阳高远的秋季,时而刮过一阵潇洒的秋风。大水早已消退。走在干枯的蒿草丛里,感受到粗糙的叶子擦过皮肤留下一阵细小的痛。
回到仙都时,经水一淹的房屋群落只剩下空荡荡的框架。过去那些好看的装饰大多破败不堪。路过仙宫的路口时,白云犬叫了几声,似乎依稀想起点儿什么,可动动鼻子,又没完全想起,如同打了一半的喷嚏。
我走在凌乱的街道上,记起一个占卜的神仙曾说过,每个生灵初来世间都是完美无缺的,但当他一日日长大,他的元神就一点点损耗,损耗在名利上,损耗在艰辛里。所以,你一生走过的每一寸土壤,都曾留下过一点点你的生命。我经过魔昂曾经困在笼中受难的那片土壤时,停留了许久,似乎真的感悟到一点点魔昂的气息。我抬步继续前行,期望在深海中与魔昂更盛大的重遇。
来到仙都与海边分叉的大道口时,我仰头间看到湛蓝的天上飘着几团浮云,其他的都不动,唯有一小朵与我一样向南而行。待我走上海边的小路时,那朵奇怪的云终于摇摇晃晃落在我的面前。
“完美!”是苍耳的声音。他从云团中风尘仆仆走出,脸上得意地笑,“不偏不倚,我的云正好落在你面前。”
其实,他分明在天上瞄了恁般久。不过想到我砸碎了他给众仙的那么多云主,我还是奉承了他一句。只是假装这种东西之于我尚不熟练,好在苍耳向来不计较阿谀的诚意,只要是迎合他就好。
他和我一起走去海边,路上抱怨说:“已经不习惯用脚走路了。”
我跟他坦白云主的事情。他摆摆手不甚介意,“反正给他们云主的时候,他们已经感谢过我。如今让他们飘到九天之上受几辈子的清苦,待我钻研得法解救他们时,那必定又是另一番盛大的感恩戴德,其实蛮好。”
哈哈大笑过后,苍耳神色一转,跟我说:“我总是做善事,将来会有福报,你的魔昂就不同了。他挖垮巨岛不但把自己砸死,你知道引发的大水造了多大的孽吗?我在云上飘着这些天,可是把这场大水看得一清二楚,如今大水都转移到魔人国去了,不会浮水的魔人只有死路一条。”
如果世间真有所谓的道理,那我想我和魔昂是理亏的。但我的舌头却兀自反驳起苍耳,和他比起了罪过——“你的遗情散害那么多魔人与鸟兽昏迷,被救过来的只是少数,天知道就那么一直昏迷至死的有多少,更别说因此而发生的饥荒。”
苍耳挑起眉毛撇撇嘴,饶有兴致地说:“你是被大水洗过脑子了?过去跟你师父只学会了动手,现在居然也会动口了。我倒是要跟你好好辩一辩。”说着,他停住脚,理了理破烂的袖口,做出要论的架势。
然而我还一心赶去海边,自然没有停。
苍耳就面向我倒着走,一边退一边念叨:“我的遗情散,那只对异恋有用。在魔人国,异恋可是禁忌呐,我帮着肃清犯禁的魔人,那叫功德。而你的魔昂呢,他引发的大水可没长眼睛,见到谁都淹。”
我没有回应。
苍耳接着说:“还有更严重的呢。大海本来是水的归宿,千万年来如此。但魔昂挖垮了那么多座岛来填海,被挤出来的水该盛放在哪?如今洪水都流转到了魔人国,在群山之间兜圈。总有一天,它们会再次回来,到时又将是一场大洪水。如此反复,根本停不下来。”
对于苍耳刚刚说的禁忌之论,我不以为意。对于神仙来说,妖魔是禁忌。对于禁欲者来说,异恋者是禁忌。这不过是一派的自以为是罢了。说不定某一天,禁忌就会变成推崇。但是,苍耳说的洪水反复,却被我听到了心里。
见我没有回击之力,苍耳得意了。我问他有没有治水的办法,他却只是含含糊糊地说:“法子总归会有的。”
来到海边时,浩荡的水面让我陌生。上次离开时,海边的庭院还能在水面露出房顶,如今是彻底不见了。开阔的海面吞没掉大片树林,我已经找不到过去的多少痕迹。
苍耳踩进水里一脚,被冷水侵得一哆嗦。他劝我别去海中白费力气,我自然没听,跟他淡淡道了别。
游在水中,口鼻都充斥着腥咸的味道。小时候,海水很淡,与河水无异。如今,想是魔人国与仙人国两处的海流有了沟通,不知道魔人国的咸海是否因此淡了些。
我只依稀记得巨岛的所在。从前游往都是从双火的岛上出发,此番从岸上出发,只有一个大概的方位。潜行中,但凡遇到一座沉岛,我就会近前仔细看看。偶尔找到一座磅礴的,便误以为是,但再往前游一游,又会遇到一座更大的。直到来至一处完全陌生的水下群岛。本来还抱有的一点儿侥幸终于殆尽。我想我是迷了方向,不如先去找双火那座岛,然后再照搬旧路,说不定更可靠。
然而,就在我打算离开群岛时,却在沙石中看到一块明亮的铁片,似从仙兵铠甲上掉落的碎屑。很快又找到一块,还见到了一颗颅骨。我恍然明白,这哪里是群岛啊,分明就是那一座举世无双的巨岛垮塌而成。只是当时,我对于它的巨大并没有具象,根本没料到它能分裂出这众星般的群岛,占据千百里海域。而且它垮而不倾,每座小岛上的草木都依然向上。
我在群岛间游窜数日,找到一些零碎的骨头,却都像是仙兵的。我偏执地以为,如果我见到魔昂的骨头,必定能一眼认出来。
一天,我浮在水面上休憩时,遇到了双火与花卫一行。他们没有游水,而是乘着一条被双火叫做“舟”的东西,打算搬迁到陆地上。
听说我在找魔昂,魔兰凄然而叹,她说自己在那场大水中就有过不好的预感。双火和嘎达则引咎自责没能帮上忙,我劝他们时,花卫怀中的孩子哭闹着醒来。
花卫一边拍孩子,一边跟我说:“他就在那场大水来临时出生的。”
“那不如就叫昂吧,”双火一拍脑袋,“这也算微微报答老大带我们来仙人国的恩情。”
花卫皱皱眉,问魔兰:“这妥吗?管这么小的孩子叫昂,魔昂若有知怕是会生气吧。”
魔兰不禁要仔细想想。我赶紧摆摆手,谢绝了双火的好意。
双火暂且作罢,但仍在想名字的事情,嘀咕道:“昂听起来多有气势,仿佛能把塌下的天给撑起来。如果不叫昂,那叫什么好呢?”
魔兰开导他说:“你叫双火,不如就给孩子叫炎,以后让他知道魔昂是谁就够了。”
我也觉得“炎”这名字贴切,任谁一听就知道他是双火的后代了。
双火劝我和他们一起上岸,但我找到魔昂之前不甘离开这片海。于是他们留给我一把铁锹,乘舟继续向岸边航行。
我用铁锹从群岛的中央开始挖。这一方海底坚硬得跟铁锹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