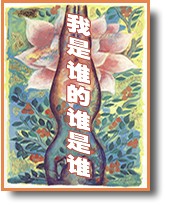谁的路过开了花-第5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看了看时间,简俊伸了伸懒腰,他打开卧室的门瞧了瞧圆杉的状态,见她还在安睡他放下心来。
才二十多岁的女孩子,担受的委屈不公太多了。任谁看了都会怜惜,她跟陈子岭的关系太复杂,两个人真的能修得个结果?对于这个问题,简俊一向没有信心。
陈子岭回来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了,他第一件事便是进卧室去看看圆杉的情况。他抚了抚她紧皱的眉头,在她眉心印下一吻。
两个男人又说了些公事,最后简俊撇了撇嘴,示意门端。陈子岭饮下一口清水,挑眉。
“怎么?”
“她……你要怎么办?”
圆杉醒来了,她躺在床上发了一会儿呆,口有些渴便起身去厅里斟水。
走到门口,却听到简俊的声音。
她转身看了看身后的大钟,都这么晚了,简俊还没走。她感到有些抱歉,太麻烦他了。正想出去道谢,却听到了他们的对话。
陈子岭答得理所当然,“我要跟她结婚。”
“什么?!”简俊不禁声音提高,下一秒便自觉噤声。他压低了声音,“你疯了?!”
圆杉的嘴角似扬非扬,她按了按心口。这里连一丝欣喜都没有了……
“我没疯,我要跟她一直在一起。”
简俊不赞同地摇头,“你们之间的伤害太多了,根本就不合适。”
陈子岭没有说话,圆杉也垂下了眼睫。
“你要一辈子瞒着她吗?”
陈子岭放下水杯,有些踌躇:“我觉得她已经知道了。”
“知道什么?知道你利用她谋得巨款?知道你从一开始就不安好心?知道你利用她取得了跟王俊仁的联系?还是知道了你是她十岁时绑架她的绑架犯?”
陈子岭眼色深沉,下颌绷紧。
简俊摇着头,“你看,你们之间存在这么多的问题,怎么还能如初地走下去?兄弟,你就不要自欺欺人了。”
圆杉睁大了眼,捂住了嘴巴。她怎么想也想不到,她伤痕累累的心还会被伤得更加彻底。她的心不是已经死去了吗?为什么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心还是会一阵一阵地抽痛?
原来……原来他从一开始就是企图利用她的身份让她像白痴一样去跟路政刚要钱!
她以为自己已经再也哭不出来。可是眼泪还是像不要钱一样滴落个不停。
陈子岭,陈子岭。我路圆杉上辈子究竟是对你做了什么恶事,为什么你这辈子总要纠缠着我不放过我?这近乎一年的时间原来都是虚假的。什么浓情蜜意什么生死相依统统都是假象!靳安锦说得对!你利用靳安娜取得警局的第一手资料,又利用我取得巨款!我当初凭什么信誓旦旦地说你对我是真心的?我究竟凭什么?!
圆杉咬着手指挨着门板滑坐下来,她就是个白痴!被人卖了还替别人数钱的白痴!
她在这一刻真切地感受到什么是万念俱灰,什么是天塌下来的感觉。她抠着虎口那个瘢痕,不断不断用力抠。路圆杉,你蠢到这个地步不死又有什么用?
门内的她无声大哭,门外的他倔强执拗。
“我会为我的年少轻狂负责,可是我对她不会放手。”
“兄弟,我们现在事业未成,根本就不是考虑儿女私情的时候。”
圆杉紧紧闭上眼睛,泪花在眼睫上绽放,闪闪发着就像刀子□她心脏一样的光。
当她知道他是绑架她的绑架犯时,她想过要杀了他,可是失败告终。在后来她却再也提不起勇气要将他从她生命中完全拔除。这是第二次的背叛了,原来这一切都是闹剧都是欺骗,你叫她怎么接受?
他对她有了真感情?不……她无论如何都不会相信了。肯定又是想从她身上讨什么便宜。她还有什么便宜可以占?不是早被他榨干了吗?她什么利用价值都没有了,短短一年时间。自从遇上他,她的人生观已经被彻底扭曲。他还要毁她到什么时候?!这样下去不行!她真的会成为疯子,她一定要离他远远的。她再都硬不下心肠去对付他,那她躲得远远的,总可以了吧?
她抹干眼泪,打开了房门。
厅里的两个男人听见开门声都吓了一跳,陈子岭小心地走近,牵起了她的手。
圆杉淡淡拂开,他僵住。简俊尴尬地别过头。
“陈子岭,我过几天就要考雅思了。”
他敛眉,“什么意思?”
圆杉深深吸了一口气,“关于我们两个人的未来我想了好多好多……我们真的,不适合。”
陈子岭蓦地瞪圆了眼睛。简俊一愣,不可置信地回过头去盯着她,可是她神情很决绝。他站起身来,“人老了就是吃不消,我回去休息了。”
他正往门外走去,圆杉断然的声音从他背后传来:“不用。”
圆杉望向陈子岭,眼睛里闪着的,不再是那种依恋痴缠,如今的眼神,不过是绝望以后的一种淡然:“陈子岭,为什么你可以这么若无其事?你每晚对着我,你就不会做噩梦?”他震惊地看着她,圆杉近乎冷酷地微笑,“可是我会。从我知道真相的那一刻开始我就没有一天睡过安宁的觉,你每晚躺在我身旁,我只觉得煎熬。白天你出去了,我就想着要怎样才能杀死你。夜晚你回来了,我还是想着怎样杀死你。”
陈子岭捉住了她的手,愤怒地把她拽进怀里:“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
圆杉反手抓着了他的手,将他的手拿开:“你别急,听我慢慢说。我脑子很清醒,这一年的时间我都在糊涂。但请相信我,再没有一刻钟的时间有我现在这样清醒。”
“当我知道你是绑架我伤害我划伤我的绑架犯时我震惊得说不出话来,那时候崩溃得想死。可是后来我想,为什么我要死?做错事的人不是我为什么我要去死?要死的人,”她笑得越发甜美,“不是你么?”
陈子岭从来不知道自己会有这样心痛的时候。她的字字句句都仿佛是沾血的匕首,将他割肉剔骨,痛得他只剩一滩血水。
“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我抽屉里的枪不是你掉包的么?”
“什么枪?你给我说清楚点!”
简俊吸了一口凉气,“子岭完全不知情,枪是我掉包的。”
圆杉诧异地盯着他,随后淡然一笑:“都没所谓了。”她看着陈子岭难以置信的表情心里涌出了淡淡的欢欣,她就是要他痛。她就是要把所有的一切都摊在他面前,她要看他挣扎至死!
“我准备了一把真枪,要置你于死地。你相不相信,我真的开枪了?”陈子岭的脸色霎时变得苍白,她靠前,他便晃着身子后退一步,“你说什么?”
圆杉的笑容残忍得让人惊心,她上前一步,踮起脚尖,就在他的耳侧,温言软语:“我说,我就用你教我的枪技,朝你的胸口开了一枪。可是很可惜,装着子弹的真枪竟然被简俊掉包。”
陈子岭一个踉跄,高大的身子就在她的面前栽倒下去。圆杉在上方睥睨着看他,眼底和嘴角都是冷酷得悲凉的笑意。简俊几步上前扶起陈子岭,他制止了,“我要继续听,听你怎样恨我,杀我,恨不得我去死。”简俊不赞同地瞪着圆杉,“你说够了没有?”
陈子岭苍白着脸,大喝一声,“你继续说!”
圆杉踱着步,继续把血淋淋的仿若刀子一般的事实披露在他眼前。
“那个男人叫周志是吗?”这话刚出口,两个男人便不约而同地抬起头来惊异地看着她。圆杉转过脸来,笑意盈盈,“那是我害死的。”
两人深深吸上一口气,可是肺腑都是刺骨的寒意。陈子岭红着眼,咬牙切齿怒道:“你说什么?”
“十年前,你们绑架我的时候我身边有一个娃娃。它是路政刚特别为我订造的电话,它的肚脐就是一个按键。它不仅是电话还装有定位追踪器。警察很快就来了,然后我躲在从里看着你们火拼,看见有人死有人逃。”她屈□子,笑意阴森残忍得仿若阿修罗,“所以,你欠了我那么多,我也欠了你几条人命。陈子岭,我们之间,到底是你欠我多一点还是我欠你多一点?”
简俊和陈子岭两个人蓦地瞠圆了双眼,眉眼里带着泪,都是恨。陈子岭捂着眼睛,嘴唇带出笑意,可是眼里流泪不止。
她要把一切他最害怕的东西以最残忍的方式剖在他面前,要他跟她一样痛,比她更痛!他陈子岭,凭什么可以活得比她好!
陈子岭摇头不信,“这一切都是你编来的,不过是你想要离开我,我不会信!”
“陈子岭,你确定要一直自欺欺人下去吗?”圆杉蹲在他面前,轻轻地抱着他,“陈子岭啊,我们之间有这么多的爱恨情仇,怎么还能在一起。”
陈子岭流着泪,颤抖着举起了手抱着她。
“不,就算是这样我也不会让你离开我!”
简俊红着眼,一言不吭地开了门离去。
圆杉捧着他的脸,印上一吻。爱恨汹涌得化成了唇齿间的温存,他们从没有过这样激烈的亲吻。仿佛燃尽了一生的气力,才成就这样一个决绝的吻。
“陈子岭,放我走,好不好?”
他口腔里都是咸苦的泪,不知是她的,还是他的。
他绝望地摇头,说不出话,只是一直摇头。
这一年来的甜蜜爱意,终是到了尽头,化作一股缠绵的青烟,此后再也没了爱。
作者有话要说:这个写得好爽!!!
、旧事如尘
杜卿婷的肚子最后还是被杜瑞博发现了。
两父女吵了好大一架。杜瑞博还激动地要亲手把胎儿打掉,多得欧丽不停调解才消了他的火。
“那是你的宝贝孙啊,你舍得打死他?”
杜瑞博冷吭,“那个人渣的种我不会承认!你们听着!从今天开始把小姐关在房里!谁也不能接近!不用给她送餐了!”
“你是要饿死婷婷吗!”
“她肯打掉就什么事都没有了!”
欧丽看着那个怒气冲冲的背影,不敢再说任何话来刺激他。
杜卿婷晕倒在房内,惊动了杜瑞博,最后医生一来便把这个爆炸性的消息轰给了他。
杜卿婷呆滞地坐在地板上,目光失神一片茫然。她曾经多么想把肚子里这个小家伙打掉,可是她从非洲安全归来,这个小生命似乎是格外顽强,顽强得她都于心不忍。
杜瑞博很忙,经常在家待不了多久便又要做起空中飞人。欧丽是这个家的女主人,在没有他的期间就是她持家。于是欧丽想到了圆杉,她们的关系好,兴许能在这件事中多少都出一分力。
圆杉见到杜卿婷的时候她吃了很大的惊,在她印象里,无论杜卿婷多大她总会特别注意仪容仪表,永远都打扮得十分大方得体地出现在众人眼前,势要惊艳落到众人的眼底。
她一身衣着邋里邋遢,头发不知道多久没有洗过了,发油到一片亮堂堂的光。眉眼憔悴嘴唇苍白,她看着她欲言又止。她把她从地板上拉了起来,两个人窝在床上一起发呆。
圆杉的状况也好不到哪里去,但最起码她还懂得要把自己收拾得漂亮,尽管心已经一片糜烂,可是她要告诉所有人,她一直都过得很好。
那之后陈子岭把她困在了房间里,甚至派人二十四小时地盯着她。那时候她真不懂陈子岭的想法,两个人都到这个地步了,为什么他还不懂得放弃?只要一面对他她的心就会打颤,她也害怕不知道什么时候在自己神志不清不楚的时候会把陈子岭杀了。然后她对着他的尸体,或者悲切得恸哭也或者平静得近乎冷漠。她也不愿意丢了人性,有时候做起梦来会看见自己双手都沾着鲜血,也不知道是陈子岭的还是程无双的,更或许是路政刚的。
醒来时有时候是在陈子岭的怀里有时候是滚到了地板上。
陈子岭似乎是打算要把那天发生的事一一抹掉,他对她一如既往地好,甚至更加体贴,除了会软禁她。他如果早上有空的话会一大早就做好早餐,然后守在她床前等她醒来。
他会很温柔地对她说,“宝贝儿,起来,我们去吃早餐。”
然后她盯着天花板发了好长时间的呆,他仍然极好耐心地等。最后她闭上了眼,继续睡去。
他毫不灰心,到了中午也会做好午饭等她醒来。他的嗓音温柔得就像三月的春花,“起来洗漱,午饭一定要吃,不然你的胃会痛。”她听了这话,怔了一瞬间,随后想起来以前的某天她胃痛得要死,冷汗涔涔,他把她抱出了门。那时是冬天的凌晨,干燥的冷更加难受。车子开到一半的时候抛了锚,拦了半天也拦不到一辆的士。然后他便一路抱着她,在冷寂的街道上穿着薄衫,而她披着大衣。他一路狂奔到医院,路上有好几次都差点把她摔出去,他却愣是不知道使了什么法子把受力的那一方转向了自己。
把她送到医院的时候其实更需要看病的那个人是他自己,他看着医护人员把她接过以后便一下子倒了下去。后来她才知道,他是光着脚把自己抱到医院的,一件衫湿得像沾了水的衣裳,蹭破皮的地方也很多,整个人的状况比她差得太多。可是这一切他都瞒着她,翌日她醒来的时候第一眼看到的人就是他。他打扮得齐齐整整,一个人难掩疲惫却仍精神爽利。
要不是听到护工们的话她会被他这样骗了去,或许是一辈子。
圆杉回过神来,转了一个方向,闭上了眼。眼角渗出了冰凉的液体,落在枕上湿了脸颊。
总是在失去以后回忆才是疯狂地冒出来,把她的心又再凌迟了一遍。
她听到自己干瘪的嗓子,活像二胡的声音:“陈子岭,你放了我吧。”
一片冗长的沉默,攀过了山,越过了海,却发现原来没有自己一直想要看到的风景。
“快点起来吃饭,饭菜要凉了。”
这样的生活一日复一日,初时那个冰化了的陈子岭如今俨然就是一滩温暖的冰水。
有一天她终于肯主动出来,他看见她的那一瞬间眼睛里闪着的都是惊喜的光。整张俊脸立马生动起来,他一脸喜色地道:“我去热一热饭菜。”
他从她身旁穿过,她拉住了他的身,她感到他高大的身子即时僵硬下来。她没敢看他的表情,她怕自己绷不住,会崩溃。她说,“陈子岭,你一身骄傲哪里去了?”
他默默地挣开了她的手,走进了厨房,随后连同炉火响起的声音一同渺渺地飘了进来。他好像在说,“一早就没有了,从我决定要跟你在一起的那时候开始就什么也没有了。”
她垂下眼帘,安静地坐在餐桌前等待。他把饭菜端了出来,她看着桌上这三菜一汤,尽管总说服自己要立下一副硬心肠,可总忍不住心软。
他坐在她面前,看她一小口一小口地进食。他忽然说道:“其实我一早就买好了我们的婚房,我理想中的生活就是现在这个样子。”
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