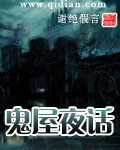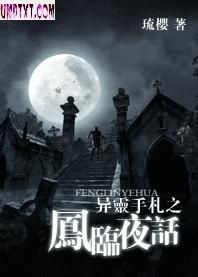燕山夜话-第3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指其榜问赵普曰:明德之门,安用之字?普曰:语助。帝曰:之乎者也,助得甚事!普无言”。类似这样的故事,在宋人的笔记中还能找到一些。可见赵普的文化水平确实不高,连拟定一个门楼的榜额都不会,罗里罗索地叫做什么“明德之门”。宋太祖看了很不高兴,所以责问他为什么要加个之字。
但是,深入一步看去,赵普实际上早已知道读书的重要,而且暗地里很努力学习。特别是对于《论语》这一部书,赵普读得烂熟。所以后来在宋太宗赵光义的面前,赵普就敢于说:“臣有论语一部,以半部佐太祖定天下,以半部佐陛下致太平。”在这里,他说的分明是一部《论语》,想不到人们却把他的话断章取义,变成了“半部论语”,并且历代相传,居然成了典故。
我们现在不管他说的是一部《论语》也好,是半部《论语》也好,都应该由此体会到少而精的读书方法。虽然,在赵普和其他古人的心目中,《论语》是他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唯一法宝,他们只要熟读这一部书就足以应付一切了。这一点,我们与他们根本不同。如果我们现在也还是死抱住《论语》这一部书,读得烂熟,尽管也有用处,却仍然无补于实际,这是可以断言的。但是,我们却无妨按照我们的需要,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中,选定任何一部书,读得烂熟,正确地掌握和运用其中的原理原则,来解决我们所面临的许多实际问题。
比如说,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的《共产党宣言》这一部书,我们假使能够读得烂熟,那末,我们就决不至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发生认识上的错误。又比如说,对于马克思的《资本论》,我们假使能够熟读其中的一卷或半卷,那末,在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建设中,这就有很大的作用。同样,对于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个报告,我们假使反复地加以研究,用来解决当前的许多重大问题,显然是有极大作用的。
无论读的是哪一部经典著作,只要真的读得烂熟了,能够深刻地全面地掌握其精神、实质,在这个基础上,再看有关的其他参考书,就一定会做到多多益善,开卷有益。所谓精与博的关系,在这里也就自然而然地会得到合理的解决。当然,精读的书多一些更好,参考书更是看得越多越好,这些都是无止境的,决不要以一部书为满足。我之所以引用“半部论语”的典故,无非是要提醒大家特别注意这个问题罢了。
至于在读书的时候,尤其对于必须精读的书籍,态度务须认真,精神务须集中,遇到不了解的或者不完全了解的地方,总要查问清楚,不应该一知半解自以为是。如果自己选定了一部经典著作,自己又懒得读,想找便宜,假借集体学习等名义,只听别人朗诵或讲解,以代替个人专心的阅读,结果一定学不到什么东西。
唐代一个节度使韩简读《论语》的故事,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唐代高择的《群居解颐》和五代孙光宪的《北梦琐言》都记载了这个故事。据说:“节度使韩简,性粗质。每对文士,不晓其说,心常耻之。乃召一孝廉,令讲论语。及讲至为政篇,明日谓诸从事曰:仆近知古人淳朴,年至三十方能行立。外有闻者,无不绝倒。”
不要以为只有韩简才把“三十而立”,错误地理解为“年至三十方能行立”。诠要是自己不专心读书,而一知半解自以为是。那就难免要做韩简第二,第三或者等而下之了。
读书也要讲“姿势”
看见这个题目,一定会有人觉得很奇怪。可不是吗?我们要养成读书的习惯,这是可以理解的。为什么读书也要讲“姿势”?这就难以理解了。
其实,这个问题还是不难理解的。无论做什么活动,都要讲究一定的姿势。人们日常的每个动作,如果仔细加以观察,几乎都有与它相适应的某种姿势。正确的姿势和不正确的姿势,产生的结果往往很不相同。从我们大家熟悉的学校生活情况来看,这个问题就更加容易理解。
走到操场,有一个最突出的感觉,就是人人都特别讲究姿势。跑步要有跑步的正确姿势,打球要有打球的正确姿势,举重要有举重的正确姿势,跳高、跳远也要有跳高、跳远的正确姿势,如此等等,不胜枚举。如果姿势不对,不但身体得不到良好的锻炼,甚至会扭伤、跌倒,后果很坏。因此,体育老师和熟练的运动员,生怕年青的同学下操场活动没有经验,积极地在现场进行辅导,讲解各项动作的正确姿势,纠正许多不正确的姿势。下操场的同学也很注意练习各种姿势,互相督促,成绩显著。
同样,在生产实习和参加实验的时候,大家也很认真听取老师傅和熟工人关于操作规程的讲解,并且在机器旁边从事操作的过程中,很注意每个动作都保持正确的姿势,以防止意外事故的发生。
但是,当我们走到学生自习的教室和图书阅览室一看,情形却很不一样。在这些地方,一部分同学往往表现得很随便,有的顶着阳光,有的背着光线,或者斜倚在书桌旁边,或者蹲在阴暗的角落里,埋头在看书、做习题。还有的虽然坐着写东西,可是,偏偏又把头侧向左边,搁在左臂上,斜着眼睛看右手的笔尖在练习本上移动。为什么他们在这些地方,对于自己读书和写字等等,就完全不讲究姿势呢?
我想劝告这些同学,要努力纠正不正确的读书姿势,讲究正确的读书姿势。事实早已证明,有的同学因为马虎大意,缺乏正确的读书姿势,以致身体已经出现了一些严重的不健康状态,如近视、驼背等等。如果许多青少年都戴上了眼镜,岂不令人惋惜?现在只要努力纠正,他们之中除了极少数由于先天性的原因以外,一般是能够逐渐好转,或者停止发展的。希望教师们、家长们,配合同学们自己,共同创造条件,形成风气,促使每个青少年都具有正确的读书姿势。
有的人说,姿势问题只是外表现象,与内在精神无关;我们有饱满的精神,努力钻研学问,顾不上什么姿势问题。这种论调,似乎很有劲,精神可嘉,而实际上是非常有害的。姿势问题在本质上说,恰恰是精神状态的一种反映。试想一想,如果摆着东歪西斜的凌乱散漫的种种姿势,这算得是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呢?
明代薛岗的《天爵堂笔余》中有一则记载,可以说是谈论读书姿势问题的。他写道:“读书、作文俱要一副真精神。坐则神奋,卧则神驰,此常情也。然卧常可以作文,而必不可以读书。曹操有欹案可卧读,杨盈川有卧读书架,二君不知何见。今之对书而睡者当效之。”
薛岗的意见照我们现在的观点看来,也应该承认他基本上是正确的。不管是读书或者是写作,不拿出真精神就一定搞不好。坐着比较容易提起精神,这完全符合生理规律。即便我们现在不一定都要强调象古人那样“正襟危坐”,但是,能够坐得端端正正,也决无害处,只会有好处。而且坐的地方还必须注意光线,不要阳光直射,也不可背光。如果能够做到“窗明几净”就更好了。
至于躺着看书等等,固然不必绝对反对,可是的确不应该当做正确的姿势。对于一般健康的人来说,如果认真阅读重要的书籍,最好不要躺着。所谓“卧常可以作文”也只能是思索文章的若干要点,或者是病人口授文章的内容而已。三国时代的曹操和唐代的杨炯,虽然都是有杰出才能的,特别是作为初唐四杰之一的杨盈川,在儿童时期就被称为神童,这两人可能有独异于常人之处,但是他们卧读的例子也仍然不足为训。
如今青年同学们读书的风气很盛,大家对于读书的姿势问题,就越来越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昨天刚好有几位青年同学座谈这个问题,因此,我愿意把这意见公布出来。
观点和材料
这是讲在写文章的时候,怎样处理观点和材料的关系。因为有的读者来信提出这个问题,并且反映了不同的意见,所以要谈一谈。
观点和材料的关系,也是虚和实的关系。近年来常听到说“要务虚”、“也要务实”、“以虚带实”、“就实论虚”等等。这里所说的虚,大体是指的理论、原则、思想、观点方面的,而所谓实则大体是指的实际情况、具体材料方面的。
据读者的反映,对于虚与实,即观点与材料的关系,在一些人中间曾经有不同的意见。那些意见归纳起来不外两种:一种强调要重视观点,而比较不重视材料;另一种却强调要重视材料,而比较不重视观点。持这两种意见的人,虽然也都承认观点和材料必须统一,但是实际上往往各执一偏,统一不起来。
的确,把观点和材料割裂了的现象,在目前并非少见,而是相当普遍的。读者反映:“有的文章只讲概念,讲观点,缺乏具体事实,既不能令人信服,也不能启发人的思考。”这是一种情形。另外一种情形是:“资料堆砌,缺乏必要的分析,看起来杂乱无章,茫然无头绪。”这两种现象反映了两种片面性。把这两面正确地结合起来,才能产生我们所希望看到的好文章。
要结合得好,当然也不容易。有的人思想水平不低,就是没有掌握资料;也有的人搜集一大堆资料,就是缺乏概括的能力,提不出什么观点。要取长补短,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到的。因此,在实际工作中,首先应该提倡有观点的提供观点、有材料的提供材料,互相帮助,谁也不要看不起别人,不可沾染“文人相轻”的恶习。
在这一方面,前人已经有了不少的经验教训。如明代的陆楫,在《蒹葭堂杂抄》中说过一个故事:“成化、弘治间,刘文靖公健,丘文庄公浚,同朝,雅相敬爱。刘北人,在内阁独秉大纲,不事博洽。丘南人,博极群书,为一时学士所宗。一日,刘对客论丘曰:渠所学如一仓钱币,纵横充满,而不得贯以一绳。丘公闻之,语人曰:我固然矣;刘公则有绳一条,而无钱可贯,独奈何哉?士林传以为雅谑。”
刘健和丘浚这两人友谊并不差,这一段“雅谑”也还不能算做“文人相轻”的典型。然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用了钱和绳的关系来做比喻,这一点对我们颇有启发。我们常常把一篇文章的中心思想,比做一根红线,贯穿全文;他们当时也以一条绳和钱币为比喻,这同我们现在的比喻一样,具有很强的形象性。
这个比喻当然也有缺点。因为我们说观点和材料相结合,虚实结合,是要把观点和材料融会消化而为一,这只有经过创造性的精神劳动才能成功,决不是生拉硬凑、加减乘除就能成功的。在这个意义上说,绳和钱之类的比喻则不够完善。
不过,每一篇文章如果都有一根思想红线,把最重要的材料贯串起来,总是好的。我们起码的要求应该如此。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慢慢锻炼,切勿要求过急,对于有偏缺的人,无论他是偏重于观点而缺少材料,或是偏重于材料而缺少观点,都不应该加以责备;只要他有一点进步就应该给以鼓励。如果有人互相提供观点和材料而合作得很好的,更应该给以鼓励。
古人合作写文章也有许多很成功的例子。千万不要以为只有我们现在合作写文章才是可能的。为什么古人就不可能做到呢?请看《晋书》卷四十三《乐广传》载:“(广)累迁侍中、河南尹。广善清言,而不长于笔。将让尹,请潘岳为表。岳曰:当得君意。广乃作二百句语,述己之志。岳因取次比,便成名笔。时人咸云:若文不假岳之笔,岳不取广之旨,无以成斯美也。”这样的事例,在我们的眼前不是仍然存在吗?不过我们现在合作的范围比古人要大得多,写作的内容更非古人所能比拟的了。
大家知道,我们现在的合作形式,远不止是一个人授意,另一人写作,更有集体研究,一人执笔,或者一人拟稿,集体讨论修改等各种形式。这些合作的形式当然是古人所不能设想的。但是无论任何一种合作的形式,都可以说是观点和材料相结合,即虚实结合的一些形式。通过这些形式,逐渐锻炼和提高,一定就会出现新的更好的合作形式,更完善地体现出观点和材料的统一。
当然,虚实结合的最根本要求,是同时掌握观点和材料,既要了解实际情况,又要随时研究理论原则问题,做到两方面如水乳之交融。这才算达到了我们的理想境界。
文章长短不拘
看了这个题目,也许有人不了解是什么意思。文章的长短问题不是早有定论了吗?为什么又要提起它?维道它还没有解决不成?是的。文章的长短问题从表面上看好象已经解决了,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解决。
文章爱看短的,怕看长的,这是一般读者的呼声;近来许多作者写文章,力求短小,适应读者的要求,这是应该受到普遍欢迎的一种好现象。由此看来,似乎文章短的总比长的好,问题不是已经解决了吗?
然而,有些读者来信说:“翻看近来报刊上发表的短文章,有一部分不能令人满意。它们有的内容还不错,也有些新鲜的观点;但是,有的内容十分空洞,既无新材料,又无新观点,看了毫无所得。这一些短文章,仅仅是比其他文章短一些,但是,不能认为它们是好文章。”从读者的这种反映看来,仅仅要求文章写得短还不能真正解决问题,或者说,还没有完全解决问题。
本来,文章无论长短,关键是要看内容。如果内容很好,即便文章写得长,读者还是愿意看的。如果没有什么内容,写得很长固然没人爱看,假使分开写几篇短文章,是否有人愿意看呢?也不见得。因为内容空虚的文章,纵然作者费尽心机,化整为零,把一大篇改成几小篇,表面看去,文章似乎很短,但在实际上不过是为短而短,内容仍旧换汤不换药,而且篇数更多了,不仅骗不了读者,反而会更加引起读者的反感。
晋代的陆云,寄给他哥哥陆机的信中写道:“有作文唯尚多。而家多猪羊之徒,作蝉赋二千余言,隐士赋三千余言,既无藻伟体,都自不似事。文章实自不当多。”在这封信里,陆云骂尽那些以多为胜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