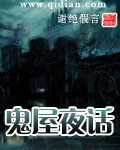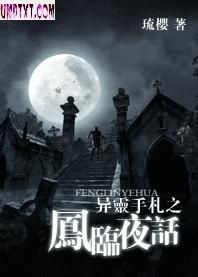燕山夜话-第1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应该承认,这许多选本的编者用意都是好的。他们煞费苦心,研究了以前各家选本的得失,斟酌取舍,并且详加注释,确实花了很多工夫。在这许多新出版的选本中,有的水平很高,优点多而缺点几等于无。读到这种选本,心里有说不出的喜悦。但是,也有一些选本,缺点尚多,有待商榷。在这里,不可能一一论列,只想提出一个普遍的问题来谈谈。
一般地说,诗和文应该有一个界限,完全可以划分得清楚。然而,这个界限却不是断然分开不能逾越的鸿沟。所谓“诗”,所谓“文”,究竟应该如何区别?它们的体裁和形式又应该怎样分类?实际上这是自古迄今争论未决的问题。《书经》的《舜典》中说:“诗言志,歌永言。”这似乎是大家公认的最古的定义。但是,我们要问:难道文章不是“言志”的吗?《国语》的《楚语》中说:“文咏物以行之。”这又是一个古定义。我们也要问:诗难道不也是“咏物以行之”的吗?
由此看来,诗和文的界限可以区别,又不好区别。《论语》的《学而》篇说:“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这个“文”字是指的什么呢?是不是光指的文章呢?显然不是。据汉代郑玄的注解说:“文,道艺也。”宋代朱熹的注解说:“文谓诗书六艺之文。”这个范围就很宽广了,差不多把诗、书、礼、乐等以及各种典章制度都包括在内了。
事实上,古人所谓“文”是泛指一切文学,包括诗歌在内,范围很大。这是有道理的。因为古人认为文学的作品必须文字非常精练,结构极为严密和紧凑,决不是我们近代人文字松散的长篇大论所可比。这并不是说,我们的长篇大论一定不如古文,这是文章的体裁和形式的发展,趋向复杂化和多样化的必然结果。问题是我们应该怎样确立一种新的关于诗文分类的方法。
明代万历年间的进士江盈科,在他所著的《雪涛谈丛》这部书中,写过一个故事。
“吴中张伯起,刻有文选纂注,持送一士夫。士夫览其题目,乃曰:既云文选,何故有诗?伯起曰:这是昭明太子做的,不干我事。士夫曰:昭明太子安在?伯起曰:已死了。士夫曰:既死不必究他。伯起曰:便不死也难究他。士夫曰:何故?伯起答曰:他读得书多。士夫默然。”
的确,《昭明文选》所包涵的各种文学体裁,十分完备。在这一部文选中,不但有诗,而且有赋,有骚,有赞,有铭,有颂,有辞;也有史论,有符命,有碑文,有对问,有奏记;还有书、启、笺、序、檄、令、表、诏等等。总计《昭明文选》分诗文为三十七类。其中,就以“诗”这一类来说,又分为二十二目。这样的分类到底是科学的呢,还是不科学的呢?我们应该认真地再加以研究,不要以为这都是老问题,而一概加以抹煞。
我们现在的诗文分类,看起来好象比古人科学化得多了。其实有的人却很象江盈科描写的那位吴中士夫,对于诗文的界限似懂又不懂。我们至今还不能提出一个关于文学的正确的科学的分类法。这是最大的遗憾。
由于分类分目不详细和不完善,势必影响到文学的教学和创作等方面,也不免会发生一些混乱。比如,有的明明不讲平仄、不讲韵脚的五言或七言的作品,也被当成了旧体诗。有的是很好的散文诗,却被人当做普通的散文。有许多比最坏的散文还要糟糕的破碎短句,却被看成是一首新诗发表出来。这样的笑话不应该再任它胡闹下去了。我们要拿出比古人更详密的分类法来。
新的诗文分类法,自然要在古来各种分类法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加以提高。比如,就“诗”而论,我们要批判地吸取昭明太子的二十二目,加以取舍和提高,并且要使新的分目完全符合于我们时代的需要。再就“文”的分类来说,自从昭明太子分类之后,清代姚鼐的《古文辞类纂》又把文章分为十三类:到了近代,福建人吴曾祺的《涵芬楼今古文钞》又把十三类细分为二百十三日。对于他们的分类和分目原则,我们也要加以批判、吸收。
有人说,我们曾经把文学作品分别为诗、赋、词、典、骈文、散文、小说、戏剧等几大门类,这就够了,何必自找麻烦,搞什么详细的分类分目呢?这种说法不值得赞同。我们不主张过于烦琐的不切实际的分类分目的方法,但是也不能满足于几大门类的粗糙分法,而要提倡一种新的切合实际需要的比较完备的分类法。
这种新的分类法,不必用开会表决的办法来确定,也不可能一下子就达到完善的地步,它只能逐渐形成。因此,文选或诗选的编者无妨自己提出一种分类法。尽管彼此各有不同,慢慢地就会有一种公认为正确的分类法产生出来。
错在“目不识丁”吗?
重视文化学习,这当然是好事情。可是,怎样才算重视?能不能定出一个标准?
一位老年的文化教员向我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我不懂得这问题从何而来。问他,他说,他教的文化班有几位学生,常常笑他是老书呆,不听他的话,他们总是念错别字,他指出他们的错误,他们也不改。因此,他很苦闷,认为他们对于文化学习太不重视了。他举了许多例子。我表示对他抱相当的同情,同时,又对他的固执己见提出了适当的劝告。
的确,一般人平常都不免会读错别字,读别字比读错字的更要普遍。比如姓“费”的,别人往往叫他“老肺”,而不叫他“老闭”;甚至于他本人也把“费”字念成“肺”的音,而不念“闭”的音。同样,许多人对于姓“解”的,总是把他叫做“老姐”,而不叫做“老械”,他自己也不例外;甚至于“老姐”、“老械”都不叫,而叫做“老改”。同类的例子还多得很。乍听起来,你会觉得非常别扭,但是,久而久之,也听惯了,不觉得有什么错误,似乎怎么念都可以了。
我们的这位老教员就看不惯这种现象,他认为必须立刻全部纠正这一切读别字的现象,才算重视了文化学习。这样认真负责的态度是很好的,不应该因此而笑他是老书呆。然而,我们又必须劝告他不要过于固执。因为对待语言文字,毕竟还要按照“约定俗成”这一条规律办事。
语言文字本来只是传达人类思想的符号,每个符号当然要有一定的声音,大家才能听懂它的意思。一个字的读音是否正确,主要应该看大家是否听得懂。如果人人都这么读,都听得懂,你又何必一定要怪他们读别字呢?即便一个字最初不是这个读音,可是现在大家都不按最初的读音,而读成另外的声音,并且反倒成了习惯,那末,肯定新的读音是正确的,或者肯定几种读音都是正确的,难道不可以吗?
这当然只是关于读别字的一种解释。至于读错字的又该如何呢?最普通的例子,如“目不识丁”这句成语,明明知道读错了,应该不应该纠正呢?
这就句成语的来历而论,读错的责任不在今人而在古人。大家知道,这句话是唐穆宗长庆年间幽州节度使张弘靖说的。据《旧唐书》列传第七十九载:“弘靖……谓军士曰:今天下无事,汝辈挽得两石力弓,不如识一丁字。”同样,《新唐书》列传第五十二也写道:“弘靖……尝曰:天下无事,而辈挽两石弓,不如识一丁字。”这两部书的字句几乎完全相同,可见宋代的宋祁在编写《新唐书》的时候,大体上是照着五代刘昫的《旧唐书》抄的。他没有想到,这一抄就以讹传讹了。
但是,宋代另一个学者孔平仲,在《续世说》中却认为:“一丁字应作一个字。因篆文丁与个相似,误作丁耳。”还有一位鼎鼎大名的宋代学者洪迈,在《容斋俗考》中也说:“今人多用不识一丁字,谓祖唐书。以出处考之,乃个字,非丁字。盖个与丁相类,传写误焉。”问题很明白,唐书原文如果是“不如识一丁字”,意思显然不够通顺。为什么不说“一天字”或“一人字”呢?其实,不管用什么字都很牵强,只有说“一个字”才最为妥贴、最为通顺。有的人自以为很熟悉古代的汉语,却不一定能够辨别“目不识丁”的错误何在。反之,读惯了“目不识丁”的人,你能说他是错误的吗?
这样看来,现在一般人公认的成语“目不识丁”分明是错了。那末,是不是就应该加以纠正呢?而且,这是不折不扣地读了错字,比念别字还要严重,岂可用“约定俗成”为理由,而轻轻地把它放过去呢!
从前面所引的材料中,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读错这句成语的责任应该由古人承担。近千年间,人们既然以讹传讹,变成了习惯,大家也完全懂得了这句的含义,那末,这在事实上难道还不是“约定俗成”了吗?如果勉强地加以改变,岂不会使大家反而觉得很别扭吗?
当然,我完全不反对我们的文化教员,把每个字句的原来意义,都向学生讲解得清清楚楚,让他们知道有几种读法,并且懂得它们的演变过程。但是,我们却不能因为学生读了“目不识丁”等等,就批评他们的错误,相反地,应该承认他们这样读也是可以的,不能算做错误。
自固不暇
前次谈论了“目不识丁”的例子以后,得到了各方面的反应。多数朋友都赞成,有个别的仍然表示不大同意。这是很自然的。对于这一类问题的看法,不一致完全没有关系,而且永远可以保持不同的意见,不必强求一致。也许过一些时候,个别同志也想通了,我们的认识就会一致起来。
赞成的朋友们要求多谈大家日常熟悉的成语,指出它的来源,介绍历来都有哪些不同的解释,辨别什么是对的和什么是错的。这种要求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把普通词典的内容搬到“夜话”中来,似乎大可不必。因此,这里只能举出平时不常见的例子来谈谈。
大家常常会听见“自顾不暇”这句成语。谁会想到这四个字里头有什么问题呢?实际上,问题恰恰最容易发生在人们以为无可怀疑的因而不加注意的地方。如果认真考查起来,“自顾不暇”终于要发生问题了。
究竟这个成语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流行的呢?查了许多古书都找不到确切的答案。《书经》上虽有“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之句,《诗经》上虽然也有“心之饮矣,惮我不暇”之句,但是显然都不是“自顾不暇”的出处上。
有人说,这句成语的出处,在《五代史》附录契丹传中。原来唐末五代时期的契丹王朝,在“大圣皇帝”安巴坚死后,由元帅太子德光继立,大举南侵,逼使晋少帝投降。德光摆驾入汴京的时候,据《五代史》附录契丹传载:“德光将至京师,有司请以法驾奉迎。德光曰:吾躬擐甲胄,以定中原,太常之仪,不暇顾也。止而不用。”这一段记载是否能够算做“自顾不暇”这个成语的出处呢?恐怕未必。
因为德光的本意无非表示谦逊一些,不要过于盛气凌人。他之所以不暇顾,仅仅是由于他亲身率领着军队,打平了中原的石晋王朝,直下汴京,不好意思就摆起帝王的銮驾,所以借口说顾不上用那十二面飞龙日月旗的“太常”仪节。这里边根本不包含任何消极和被动的意思,与“自顾不暇”这句成语的意思又有多少共同之点呢!
比较起来,这句成语的可靠出处,应该是《晋书》的《刘聪载记》。刘聪是两晋时代前赵刘渊的第四子,继其父自立为帝,攻陷洛阳,生擒晋怀帝,鸩杀之;又陷长安,执晋愍帝。当时晋将赵固攻河东,扬言要活捉刘聪的儿子刘粲,以赎天子。这一场战斗很激烈。晋兵企图偷渡洛水和汭水,袭击刘粲的部队。这时刘粲部下的将官王翼光看到晋兵要想渡河偷袭,把情况报告给刘粲。刘粲分析双方的形势,以为晋兵在河的那一边,惟恐地位不稳固不可能渡河偷袭,因此满不在意。《晋书》上的这一段文字是这样写的:
“王翼光自厘城觇之,以告粲。粲曰:征北南渡,赵固望声逃窜。彼方忧自固,何暇来耶!且闻上身在此,自当不敢北视,况敢济乎?不须惊动将士也!”
刘粲因为轻敌,后来终于被晋兵打败,不在话下。光说这一段文字,乃是迄今为止我们能够找到的“自顾不暇”这句成语的唯一出处,这大概是比较可靠的了。
然而,这样追根究底的结果,却使以往所谓“自顾不暇”的成语发生了动摇。看起来这句成语恐怕是弄错了,应该改为“自固不暇”才对。宋代张君房的《云笈七签》中有句云:“神之无形,难以自固。”这里说的“自固”,与刘粲说的意思也很相近,可见后来有更多的人采用这种语气,久而久之,就慢慢地变为成语了。
从此以后,我们是否应该把“自顾不暇”这句成语,普遍地改成“自固不暇”呢?当然没有这种必要性。我们还可以按照“约定俗成”的原则,继续承认“自顾不暇”是一个成语。而对于“自固不暇”,只要知道它在历史上有过这么一回事就可以了。
北京的古海港
古代的北京有海港吗?回答:有海港。
那末,什么地方是古海港呢?回答:就是什刹海和积水潭的那一片水面。
这个海港现在虽然已经不存在了,但是,这一段历史却很值得我们研究。
大家都知道,当着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即公元一二九一年的时候,精通天文、地理、历法和水利的大科学家郭守敬,奉了元世祖忽必烈的命令,负责修通元大都(即北京)到通州的运河,使往来于江南的漕运船舶,能够把南方的粮食,直接运到大都。
为了完成这一项巨大的工程,郭守敬做了艰苦的努力。他根据他的父亲郭荣和他的老师刘秉忠传授的知识,再加上自己实地调查和测量的结果,制订了细密的计划,并且亲自指挥施工,经过一年多的工夫,终于修成了从通州到大都的这一段运河,命名为“通惠河”。这在历史上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件事。
据《元史》《郭守敬传》载,修建“通惠河”的主要经过是:“中统三年,……北祖召见,面陈水利六事。其一,中都旧漕河东至通州,引玉泉水以通舟,岁可省雇车钱六万缗。……至元二年,……又言:金时自燕京之西麻峪村,分引庐沟一支,东流穿西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