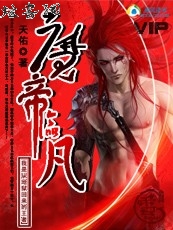花煞 作者:叶兆言-第1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有一天下午,是漫长雨季就要结束的日子,杨希伯和一名心爱的小妾欢乐以后,深深地陷入梦想,当他被一场恶梦猛然惊醒。他又被正在手淫的小妾不可压抑的呻吟声吓了一大跳。一时间他不可能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小妾忘情忘形地动作着,人像一只龙虾似的弯拢起来,她的脚突然一伸,也就是在这时候,她发现杨希伯迷惘的眼睛,正死死地盯着自己。
杨希伯从心爱的小妾身上真正明白了衰老的含意。他没有暴怒,没有大惊小怪地说什么,甚至都没有生气。杨希伯毕竟八十岁了,人到了这个年纪,有些想法和年轻时截然两样,他把小妾的举动当做是一种天意,一种神的暗示。他顿时领悟了自己一种新的享受的可能性。没有子嗣是老天爷安排的,杨希伯没必要去和不能战胜的东西对抗。他意识到自己已没必要吃辛吃苦,亲自像牛马那样为女人干活。一个不懂得保存自己精力的老人真是愚不可及,杨希伯决定放弃力不从心的体力活动,而转为纯精神方面的享受。他从女人的陷阱中,知趣地跳了出来,成了一位处于高度自由境界中的超人。
杨希伯的后院一如既往地充满着淫荡的气氛。但是杨希伯已由实干家,上升为无动于衷的看客。他让自己的小妾们从硬着头皮,到习惯成自然地赤身裸体在他的眼皮底下走来走去。从烈日炎炎的夏天,一直延续到了大雪纷飞的冬天,他别出心裁地让小妾们该干什么干什么,金钱已麻痹了女孩子们的羞耻心,她们在他的唆使下,毫无顾忌地尽情放纵自己。他终于变得越来越老,变得真正地老了,当杨希伯尝试着让人牵来一只心情急躁的小公羊,和他的那些爱妃们一起游戏,自己仍然不能感到兴趣的时候,他突然心灰意懒,重重地往地上吐了一口浓痰,然后十分果断地遣散了后院中所有的尤物,过起了老和尚一样的独居生活。他开始真正地相信起上帝来,每当听见教堂的钟声,他便不由自主在胸前划起十字,口齿不清地念着祷告词。由于耳朵变得越来越聋,他的耳旁常常响起纯属错觉的钟声,因此在濒临死亡的那些日子里,家里的负责侍候他的仆人,老是看见他没完没了地在胸前乱划十字。
〃阿门!〃他时不时会冒出这么一句,拖长了语调,冷不丁吓人一跳。
6
储知县深知只杀一个胡大少,不足以平息朝廷对梅城教案的盛怒。洋人也不会因为杀了一个为首的带头人,事情就此便算了结。妥善处理好梅城教案,是储知县如何走好险恶官场这条钢丝绳的关键。他必须赢得朝廷的充分信任,必须获得洋人的充分谅解,除此之外,他还不能太得罪梅城的老百姓。举人出身的储知县,做候补知县已经许多年,好不容易有机会扶正,他不得不小心翼翼,把教案遗留下来的难题一一解决。首先自然是进一步地缉拿凶犯,胡大少虽然已经擒获,可这毕竟是前任知县的功劳,储知县明白自己若想讨上峰的好,必须亲自去抓获几个凶犯才行。大牢里已在押了好几位所谓的凶犯,经过严刑拷打,储知县发现除了大名鼎鼎的胡大少,其他全是莫名其妙的替罪羊。在这些替罪羊中,有老实巴交完全无辜的老百姓,也有教案前就关押在大案里的囚犯,这一发现成了储知县的前任革职充军发配新疆的重要契机。储知县亲自审案,一发现蛛丝马迹便紧拉住死死不放。和昏庸无能的前任相比,储知县身先士卒事必躬亲,很快在毫无头绪的混乱中理出了线索。
老二是继胡大少之后落入法网的又一名要犯。为了查出老二隐藏的地方,储知县派人将老二的媳妇牛氏捉了来,不问青红皂白,先是一顿沾了水的小竹板子打手心,打得皮开肉烂,再带到大堂上。储知县厉声喝道:〃本县也没时间一趟趟上你家去捉人,今日将你捉了来,对于你男人的下落,你招也得招,不招也得招。我不相信就凭我一堂堂知县,治不了你这一刁妇。〃早在当候补知县的时候,储知县对如何用刑,就有一番很深入的研究,他知道重刑之下无勇夫,只要用刑用得狠,任你是铁打的汉子,有什么都得乖乖地说什么。储知县让手下拿出一铁熨斗来,又吩咐升起一盆炭火,将熨斗搁在炭火上烧着。那铁熨斗是特制的,有一个长长的把子,熨斗底端有十几个凸出的铁奶头,一个衙役蹲在炭盆边上用扇子扇着,不一会,那熨头上的奶头便烧红了,储知县不耐烦地说:〃大胆刁妇,你睁大眼睛看好了,到底是招,还是不招?〃牛氏吓得魂飞魄散,连连喊冤,喊青天大老爷饶命。储知县说:〃饶你命有何难,老老实实供出你那该死的男人藏在哪儿就行。〃牛氏还不肯说,一口一个自己实在不知道。储知县大怒,喝令剥去她上身的衣服,叫一个人提着她的头发,两个人架住了她的膀子,同上在了天平架上一样,另一个人手执熨斗站在她的前面,气势汹汹地等着县太爷的进一步指示。
储知县最后一次问起招不招,牛氏一泡尿已吓了出来,地上立刻湿湿地一大滩,哭喊着又叫了一声冤枉。手执熨斗的那位差役,回头看了看早已不耐烦的储知县,储知县板着脸说:〃冤枉不冤枉,我却没有这好耐性和你磨蹭,替我先拿她的两个膀子熨起来,我倒要看看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执熨斗的只轻轻将熨斗底下的铁奶头,在牛氏的左边的膀子上搁了一搁,牛氏立刻杀猪一般大叫起来。一阵青烟吱吱叫着升起来,等那熨斗拿开,牛氏左膀上被熨过的地方,一个个指头那么大的烫伤,都发了黑了。储知县又命令在牛氏右边膀子上,照样也来这么一下。牛氏又是一声惨叫,连声叫:〃我招,我招,我全招。〃
〃果然是大胆的刁妇,不是不知道吗,怎么吃了这点点苦头,就要嚷着招了,〃储知县怕她还会有所隐瞒保留,吓唬说,〃光是膀子上还不行,来,烧烧红,再给我烫烫她的奶头子。〃
牛氏不顾一切地大喊大叫,储知县明白她这是真打算招了,吩咐手下先把熨斗搁一边。牛氏如倒蚕豆一样,把男人老二现如今藏在什么地方,一五一十毫无保留全都如实招来。储知县立刻领了人去捉拿老二,这一次是瓮中捉鳖,不费吹灰之力,便把藏在亲戚家的老二擒拿归案,老二知道是媳妇牛氏出卖了自己,在押解去大牢的途中,以及后来在刑场上被砍头前,都扯足了嗓子大声咒骂牛氏。〃你这个不要脸的娼妇,老子做了鬼,也不得放过你的!〃在打入死牢的那段日子里,老二把他的宝贵时间,都花在了对媳妇牛氏的仇恨上,他觉得自己和杨希伯之间的个人恩怨已经了结,正因为如此,他更觉得天底下,自己唯一不能饶恕的人,就是自己的媳妇牛氏。他想象自己有朝一日出了大牢,先把牛氏挂在大梁上一顿抽打,然后三天不许她吃饭,凡是吃饭的顿头上,便用棍子好好地收拾她一番。
储知县乘胜追击,将老二痛打一顿扔进大牢,继续马不停蹄地去捉拿杨氏二雄。杨氏二雄所在的七里村离梅城不远,然而储知县领着人马已扑了好几回空。为了擒获杨氏二雄,储知县每次去,一定抓几位杨氏二雄的家属回去大刑伺候。杨氏家属竟然一个个都是钢筋铁骨,男人的屁股都被板子打烂了,女人的身上被熨得伤痕累累,硬是咬紧了牙关不肯招。储知县也不心急,三天两头派人去七里村抓人,和杨家沾亲带故的,只要被储知县打听到了,有理无理,一律带到大堂上大刑侍候,往死里折腾一番。
杨氏二雄中老二杨德武眼看着耗下去不是事,好汉做事好汉当,老这么拖累家人也说不过去。他的一条腿在攻打教堂的时候,被打断了,弟兄俩商量了一番,决定让杨德武去投案自首。头掉了碗大的一个疤,他反正已是个废人,于是和家人痛痛快快喝了一顿告别酒,由哥哥杨德兴扶着,向祖宗的牌位磕了几个头,让族人将他抬到县衙门去。储知县喜出望外,但光抓到一个弟弟还不过瘾,对断了一条腿的杨德武依然大刑伺候,逼着他交出哥哥杨德兴的下落。杨德武一口咬定哥哥已经死了,储知县当然不相信,活着要见人,死了必须见尸。
〃别跟我来这套,〃储知县冷笑着说,〃见着了你哥哥的尸首,你再说他死了也不迟。〃
于是用轿子将杨德武抬到所谓埋着他哥哥的一座坟前,挖开来一看,果然用极薄的木板做成的棺材里,埋着一具腐烂得面目全非的尸首。杨德武暗自得意好笑,储知县捂着鼻子上前看了半天,不相信地对杨德武说:〃凭什么你说这尸首是杨德兴,他就是杨德兴,大胆刁民,什么下作的事情做不出来,我凭什么要相信你?〃储知县让忤作仔细检验,不得出任何差错。
忤作遇到一位如此顶真的县大爷,不敢有半点马虎,用不了多久,就判断出这是一具冒充的尸首。杨德兴正当壮年,而尸首已是个年近花甲的老人。身高也完全是两回事,杨德兴人高马大,尸首却生得十分矮小。储知县很得意自己料事如神,又从七里村抓了两个人走,临走,冷笑着留下一句话来:
〃从今日起,本县每隔一日,就到你们这逮两个人去过过堂。杨德兴喜欢和本县捉迷藏,本县就奉陪他好好玩玩。〃
过了没几天,杨德兴由族人五花大绑地绑着,像押贼似的送到了储知县的面前。正赶上储知县那天心情不太好,问了没几句,便大喊一声:〃拉下去,打!〃左右衙役轰的答应了一声,立刻把杨德兴拉下按倒,劈劈啪啪一五一十实实在在一顿小板子,把杨德兴打得血肉横飞死去活来,然后再押进死牢,和弟弟杨德武关在一起。兄弟相见,英雄气概也没了,抱头痛哭了一场。知道是死罪,哭完了,轮流说了一番互相鼓励和打气的话,砍头只当风吹帽,二十年以后又是条好汉,只要那该死的储知县,少打几顿令人生畏的小板子,死倒不足惜了,又相约来世还做兄弟,想造反照样造反,不想造反的话,就本本分分种田,老老实实过日子。
7
阿贵自从亲手砍了洪顺神父,陡然间也成了平湖村的人物。他的胆小原来出了名的,然而既然连和洋人差不多的神父都敢一刀砍了,大家不得不刮目相看重新认识。首先最拿他当回事的是红云,这女人天生喜欢强悍男人,嫁给了阿贵以后,最咽不下的一口气,就是赚男人太窝囊,嫌他不敢和别人吵架和打架。在胡大少第一次睡了裕顺媳妇的那个晚上,红云兴冲冲赶到家里,挎着一个鼓囊囊的大包裹,里面放着抢来的城里人的杂七杂八的东西,从装细软的首饰盒,到吃饭用的锅碗瓢盆,应有尽有琳琅满目,黄黄的油灯下,红云陶醉在意外的欢喜之中,她逐个地试戴着首饰,对着一面有了裂纹的小镜子横看竖看。
从那面有了裂纹的小镜子里,红云一边在穿着一对银耳环,一边注意到了阿贵木然的表情。在初十庙会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阿贵的面部表情,常常就像是戴了一层面具。这是一种让人看了不知所措的神态,阴沉麻木而且暗藏了一股杀气。真好像是完全变了一个人,阿贵无所事事地看着红云的背影,下意识地摸着自己的耳朵。红云感到更吃惊的是,就像用大刀砍了神父一样突然,阿贵突然第一次不经允许,把戴好耳环又正在试着衣服的红云,像扔一袋粮食似的,扔在了床沿上,当着一大一小两个儿子的面,用最快的速度把事给办了。这是他第一次对她这么粗野,而且也是第一次一边干活,一边肆无忌惮地喊起了他侄媳妇的名字。
侄媳妇的名字叫阿玉,虽然辈份小了一辈,却比阿贵还大一岁。阿玉是阿贵懂事以来,看中的第一个女人,记得还是在她刚嫁到平湖村的那一段时候,有一次,阿玉在茅坑边倒马桶,阿贵从一边走过,一眼看见了正弯着腰的阿玉的那两只大奶子。女人的奶子阿贵已不是第一次见到,然而这一次阿贵却心驰神往,脚生了根粘了胶似的,再也挪动不了。阿玉手不停地刷着马桶,白晃晃的奶子像一对不安分的兔子,在大襟衣服里蹦来蹦去。那一年的阿贵正好十八岁,阿玉那硕大无比晃动的一对奶子,从此就一直是他的梦想。娶了红云以后,阿贵在做爱时,常常会不由自主地想到阿玉,一想到那对白晃晃肉鼓鼓的大奶子,他的兴致陡然便会好起来。红云在阿贵粗野的动作中,甚至都没来得及思考他所喊的〃阿玉〃意味着什么,所有的一切发生得都太快,太不是时候,她忍受着男人强烈而短暂的冲击,脑子里还在想着她的首饰。随着阿贵一声拖长了的〃阿玉〃,红云总算在身底下摸到了那面带了裂纹的小镜子,她小心翼翼地拱起身子,摸出了小镜子,举在手上,照了照自己的耳环,又十分好奇地照了照阿贵拖着一条大黑辫子的后脑勺。她注意到突然有只苍蝇飞到了阿贵的后脑勺上,连忙用另一只手拍苍蝇。
初十那天梅城所发生的暴力,经过民间的口头传播和渲染,很快有了各色各样的传奇色彩,平湖村的重大议论焦点,从夸张描述初十那天杀洋人烧教堂打教民,发展到仅仅谈论阿贵如何如何,谈论阿贵怎么样怎么样。人们相信初十那天,阿贵夫妇趁火打劫发了大财,所有的金银财宝都在家中的角落里埋藏着。有人发誓说亲眼看见红云天天在家穿金戴银,像城里人一样涂脂抹粉,把个脸打扮得跟猴子屁股一样红,红得像是在舞台上做戏。随着风声一天天紧起来,暴乱首领胡大少缉拿归案,大家对阿贵暂时的刮目相看,开始不复存在,对阿贵的鄙视重新恢复,那种发自于内心深处的嫉妒,很快被普遍的幸灾乐祸所替代。
各种对阿贵不利的消息在平湖村到处流传。人们相信官兵随时随地都会前来捉拿钦犯,因此在阿贵落入法网之前,尽快地把他的金银财宝分光,无疑是一件最得人心的痛快事。人们从好言好语的暗示,到明目张胆的威胁,各种能想到甚至不能想到的话都脱口而出。既然杀头对阿贵不过是迟早的事,他就有义务把自己的不义之财,捐献出来供族人享用。金银财宝生不带来,死不带走,与其被官府抄了去,趁早留给自己人起码是个聪明理智的善举。
当储知县以大刑侍候,马不停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