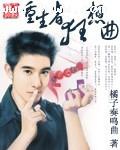茶人三部曲-第7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所谓“我心相印“亭,乃“不必言说,彼此意会“之意。此亭立于岛之南端外堤,在此驻足晚望,亭亭三塔,便尽收眼底了。
亭内有桌子一张,配以几把方凳。但见周二变戏法似地取出一把热水壶来,又拎出几只青瓷茶杯,冲了配配的茶放在桌上,说:“少爷小姐,请用茶。”
就见那楚卿把已经到了唇边的茶杯轻轻移开,却问:“你怎么知道我们就是少爷小姐了呢?”
周二微微一笑,说:“别人我不敢说,这几位我却是知道的。杭家少爷,大公子,二公子,还有小姑奶奶。“这边杭忆才喝了一口茶,便道:“这茶不是我们家的。”
“也不是翁隆盛的。”
杭汉补充说。
见楚卿有些惊奇,寄草说:“那小姐不用太奇怪,实在也就是吃哪一行就精哪一行罢了。像我们家和他们翁家的茶,一到茶季,都是每天收了龙井新茶,然后当夜下锅复炒的,还要筛簸,去掉茶叶末屑,第二天再加以包装,放入石灰缸。等到卖时,还有一道筛选、拣别与拼合的过程。况且,杭州城里,喝茶的谁不知道,杭家和翁家的龙井茶,一过了立夏,就停止收购的。我们现在喝的茶有股苦味,况且杯中茶片也不齐整,一看就知道不是春茶了。““那,姑娘你倒不妨说说,此茶是姓什么的呢?”
寄草就笑了起来,指着东南面湖边,道:“老周你还真要我说啊,你可是我们杭州茶人的生意对头啊。你不是对面上海江裕泰汪家的吗?”
说得周二也笑了起来,问:“姑娘你好眼力,怎么看出来的?”
“谁不知道啊,“杭忆也笑了起来,指着杯子下面刻的字说:“你看这不是个'汪'字吗?”
这一说倒是提醒了楚卿,连忙问:“听说汪庄被日本人飞机炸了,有这样的事吗?”
周二这才叹了口气说:“要说没炸,其实也和被炸了差了一口气。茶庄生意早就停了下来,汪家人避难回了上海、香港,下人们也都作了鸟兽散。留下我们几个人守着这一摊子。你看那些唐琴来琴的,从前江老板何等地当作性命,如今晾在那个'今蜡还琴楼'里,也是没有人来过问了。”
“你怎么就跑到这里来了?”
“一开始也是到湖上来避飞机的。后来想,那么干熬着,还不如重操旧业。你们也不是不知道,我们汪家卖茶,从前最占便宜的便是湖边的那个茶号'试茗室'。买主亦是茶客,三杯过后,茶叶包好了,就放到了你的眼面前。我呢,就是那个卖茶的。”
楚卿连连地点头,“我明白了,你是到岛上来卖茶的。”
周二脸就红了,说:“兵荒马乱,什么卖不卖茶的。不过一带两便,也是避飞机,也是煮点茶,有人来喝,能给几个铜板就给几个,没有,不给也无妨。都什么时候了,说不定一颗炸弹下来,尸首就飘到西湖里去了呢。我们也是做了半世人的老杭州了,倒是真正没有想到,还会有这样一天。“周二说着说着,眼睛就红了起来,赶紧就给在座的各位沏茶,边沏边说:“你们几位也是茶行中人,我今日也是诚心请了你们喝茶,千万不要提个钱字。有缘相会,说不定今生今世也就是这么一遭了呢。“看来这周二果然是个平日里跑堂的,能侃。只是今日说来,都是凄凄惶惶之语了,众人听了,大有不忍之意。首先便是杭汉从口袋里掏出钱来说:“真想多给你一点,没了,对不起。”
“打起仗来,说不定花钱更多,趁现在日本人还没进来,你能赚还是赚几个。实在不行了就赶紧撤,留在城里,也不是个事情啊。谁知道日本人会怎么样呢?”
寄草一边往小皮夹里掏钱给那周二,一边说,“罗力说了,日本兵真正不是人,平湖、嘉善那里一路杀过来,多少老百姓死掉,看了眼睛都要出血,你还是早作打算吧。”
周二一边感激不尽地收着钱,一边突然咬牙切齿地骂道:“日本矮子,都不是人,没一个是人,一看就不是人生父母养的。什么种操,畜生洞孔里钻出来的。从前拱震桥多少日本人,没一个像人的,统统都是畜生。你们看我们江庄后面的雷峰塔,都说是孙传芳部队进来的时候倒的,是孙传芳造的孽。哪里是这回事!孙传芳再坏,是我们中国人的种操。中国人再坏也是人生的,日本人再好,娘卖匹也是畜生生的。雷峰塔就是前朝手里日本倭寇烧掉的。日本人不要落在我们中国人手里,有朝一日落在中国人手里,有他们好吃的果子。要我说,杀得他们再没人能生儿子才好,免得他们三日两头来,让我们中国人做不成人。“那骂人的,固然是无心,也是激愤。可是骂到种操上去,在座的几个,就不可能不往杭汉身上想。要是平日里,谁敢说杭汉半个不字,寄草姑姑也是不客气的。今日却由着那周二骂,一时竟也想不出来怎么去对话。
这些年来,杭州人骂日本人,嘴皮子上,也是越来越厉害的了。骂得那么凶,日本人还是长驱直人,进了中国。杭家人围着吃饭时,也骂日本鬼子,但是从来不骂种操。所以杭汉猛不了地听到这些话,脸就立刻红了起来,装作不经意的,就用茶杯盖住了自己的脸——不知是为自己的那一半血统羞愧了,还是因为有人骂他的母亲的种族而尴尬;掩饰这样的情绪实在不容易,他对着茶杯憋气,憋得呛,吭吭吭吭,全身就抖起来了。
周二却全然不知,换了笑脸说:“少爷你慢慢喝。等日本佬赶走了,我周二还要在此专门等着你们来品茶呢,你们可都记住我的话了。“几个人都点头道谢。杭忆好像是漫不经心地对周二说:“老周,麻烦你再替我们烧壶水来。”
老周刚刚走开,杭忆便对楚卿说。”
那小姐,你不是有话要对我们说吗?”
寄草盯着楚卿,轻声说:“我听说你要把我的这两个侄儿都带走。家里其他的人,还没有一个知道的,他们先告诉我了。““我晓得。”
楚卿把目光移到了寄草脸上,想了一想,补充道:“不过还得更正一下,不是去两个人,是在两个人当中选择一个。另外,是我建议让他们先告诉你的。““你看,这一来我们俩就想到一块去了。我也跟他们说了,得让我先和你谈过了,这事才好作数。我这一道关过不了,家里的那道关就更别想过了。“楚卿就淡淡地一笑,寄草深知那笑意何在,于是她也淡淡地一笑。这两个女人,一见面就知道了彼此的分量。
“我十六岁那年就离开家了,家里人要把我嫁给一家阔少。我一跑,我父母在杭州城里捞了三天三夜的井。““我知道这件事儿。真没想到,事隔多年,你又回来了。听说你爹妈一直不认你。““不,是我不认我爹妈。”
楚卿更正道。
杭忆杭汉两个人坐在旁边,听这两个女人谈闲天一样的唇枪舌战,暗地里就递着眼色。杭忆就插话进来:“虽说编辑部只要一个人,但我和汉儿已经商量好了一起走,总不能让我们跟在老弱病残身后逃难吧。”
“谁说要逃难了,至少妈和大哥都不走。”
“那我们也不能留下来当亡国奴啊。”
杭汉说。
楚卿看着杭汉,灰眼睛一闪:“我正要通知你,你得留下来!”
杭汉看看杭忆,嘴都结巴起来:“怎么——我、我、不能走了,不是说我懂日语,用得着吗?怎么……怎么…·”杭汉为难地看着杭忆,心里一急,却说不出话来了。
“你不能走。”
楚卿把刚才的意思又重复了一遍。
“为、为、为什么?”
杭汉的浓眉,就几乎在额头连成了一片。
“这是组织的决定。杭忆跟刊物撤,你留下。“杭汉站了起来,两手按着桌面:“因为我、我是日本人?”
他觉得这么讲不够准确,连忙强调,“因为我是半个日本人?”
杭汉是一个不长于表达的人,他急成那样了,还是不知道怎么说话。
寄草的脸有些挂不住了,说:“你胡说什么,谁把你当日本人了!”
杭汉很茫然地又坐了下来,他看看杭忆,杭忆又看看楚卿。他和杭汉虽是堂兄弟,却好像跟一个人似的。杭汉话少人憨,一身好功夫,他们平日里分工合作也很好。油印传单,从来就是他刻蜡纸,汉儿油印,他们是形影相随的一对。他从来没有想到过,上面会真的不同意杭汉和他一起去抗日。
楚卿不表达,不表达就意味着她的确是把他当作日本人了,这使杭汉又开始猛烈地打起哆啸来了。一边打着哆噱,一边就朝杭忆说:“你说,这是怎么一回事?你说,这是怎么一回事?“楚卿看着这几个人的紧张,这才淡淡一笑:“怎么那么沉不住气,把我也当日本人了?”
见他们脸上的表情都松了下来,她才对杭汉说:“你别急,把你留下,是因为以后要派你大用场,你不知道你自己的身份有多么希罕?”
“难道你要他去当特工?”
寄草的脸也白了。
“不知道。”
楚卿看着西湖,“不知道再过一个月,杭州会是怎么样的景象。也许日本人就进来了,这个亭子里,就站着日本兵了。你们看湖上的水鸭,它们现在飞得那么自由自在。也许那时候,它们就成了侵略者的猎物了,湖上会漂满它们沾血的羽毛……
“楚卿眼睛一亮,盯着杭汉,“也许那时候需要你杀人,你敢杀人吗?”
她的声音低沉,几乎不像是从她的瘦削的身体里发出。杭忆激动得气都透不过来,仿佛要去杀人的就是他。
“敢!”
他就替杭汉先低低地叫了出来。
寄草脸白着,口气却依旧是一向的轻松:“就是,有什么不敢的。日本兵又不是人,都是畜生,杀言生,有什么不敢的?”
杭忆知道,这句话是小姑妈专门说给杭汉听的。小姑妈被楚卿刚才的神情震惊了,现在她需要掩饰这种震惊。她一边往茶杯里续着热水,一边说:“来来来,平日里我们也是从来不喝人家上海汪家的茶的,今日碰上了,我们也不妨牛饮一番。以后想喝,也未必能喝得上了。““怎么会喝不上呢?”
杭忆说,“不出三年两载,我们就会把日本佬赶回东洋去的。到那时候,我们再到这里喝汪裕泰。““到那时候,这张桌子前,不知道少的是哪一个呢。”
楚卿突然说。
寄草放下手里的杯子:“我说女革命党,你怎么老说丧气话呢?”
楚卿就低低地回答:“我说的是丧气话吗?”
大家就都默默地喝茶,都晓得,这女人说的不是一句丧气话。
寄草把声音就压得更低,“那小姐,我能不能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为什么选择了我们杭家人?”
“你们家族,有过林生。”
“就那么简单?”
“还有——”
楚卿想了想,“我们是最坚决抗日的组织,我们也需要最优秀的青年!”
寄草显然是想和楚卿拗着来,她大声说:“我觉得在这样的时候,整个中华民族,无论何党何派,都在真正抗战。所有在前方流血牺牲的将士,都是最优秀的青年。““我没有说将士们不优秀,但我必须强调,我们是抗战最为彻底的。”
楚卿斩钉截铁地说。
“罗力他们,也是抗战最为彻底的。”
寄草突然站了起来,她开始不能接受这种谈话方式了。
楚卿也不知因为什么,突然失去了耐心,她也站了起来,说;“需要我从'九一八'开始举出实例,来说明我的观点吗?”
“不用了,当学生的时候,我也到南京请愿过。我有我的头脑。““你以后会看到我说的事实的。”
“你这是干什么,是到这里来和我论党争的吗?”
“我只是想告诉你,我们是抗战最为彻底的。”
现在,楚卿的灰眼睛,几乎灰无人色,灰得像一块寒铁了。
寄草想了想,气就粗了起来,她不能接受这个叫楚卿的女人。这个莫名其妙的女人,她有什么权力变着法子来贬低罗力他们。罗力是她的心上人,枪林弹雨,出生入死,她不管罗力的上下左右怎么样,她只知道,罗力是最抗日的。因此她一字一句地说:“你看,我到这里来,可不是来和你争什么是非的。我只是来看一看,我侄儿跟你们走,放不放心。日后我对他们的父母也好有一句交待。可是你非得和我争什么谁最抗日,我真不晓得这有什么意思。不过你一定要和我争,我也只好奉陪。我不管你们是不是最抗日,反正我的罗力是最抗日的,他的父母兄弟都让日本人杀了,他是最最最最最抗日的。我不能让你说他比你们不抗日。我不能让你那么说他,我受不了。“杭忆和杭汉都愣住了,这两个女人突如其来的战争,超过了这两个少年人的人生经验。两个侄儿都很尴尬,只好站了起来,一人一只胳膊拉住他们的小姑妈的手说:“小姑妈你别在意,那小姐不是这个意思。”
“我不知道她是不是这个意思,反正我听到的就是这个意思。我还是走的好,要不再听下去我真不知道会怎么样。你们,你们都大了,请便吧。“小姑妈杭寄草站着,想用那最后的一句话暗示侄儿们和她一起行动。可是侄儿们愣着,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却没有一个动弹。小姑妈晓得再站下去也没有用了,头颈一别,扬长而去。
两个少年看看在九曲桥上远去的小姑妈,再看看坐在眼前的那小姐,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还是杭忆灵机一动说:“汉儿,你陪小姑妈去,那小姐这里我负责送到岸上。”
见杭汉一跳又到了柱上,风一般地飘去了,杭忆才坐到了楚卿的对面,小心翼翼地说:“那小姐,你别在意,我的小姑妈,有时就那么任性,家里的人都让着她。”
楚卿摇摇头,突然说:“对不起。”
杭忆看到她的眼角突然出现了泪花,他吓了一大跳,心情激动又不安,只好怔着不说话。然后,他听到她说:“对不起,我刚从里面出来,也许还有点不适应。”
“里面,里面是什么?”
杭忆不解地问。
“里面,就是许多人再也出不来的地方。”
楚卿突然朝他笑一笑,泪花不见了,杭忆几乎怀疑刚才是他看花了眼。
“三年前我和一个人在这里喝过茶,也许喝的就是你家的茶。我不懂茶,真可惜,记不住那滋味了。我们那时候就知道说话——真不能想,三年了,他不会再回来了。“她朝杭忆笑着,倒退着走向湖边,杭忆担心地站了起来,跟着她走。而她,一边走一边就说:“今天我没有把握好,说得太多了,意气用事了。你不会对任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