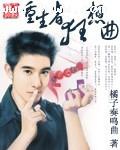茶人三部曲-第14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立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给了他个人一个重生的机会。在这个机会中,他有望成为一个彻底的革命者,一个革命的第一号种子选手!
但他依旧担忧,唯恐自己落后于革命了,因此这个对政治实际一窍不通的大孩子,成为一个有高度政治敏感性的人物。否则他不会为了一篇社论花几小时等着他的堂哥。6月1日运动正式开始的那天夜里,他是在得茶的宿舍度过的,可说彻夜不眠。当时还与得茶同室的吴坤对形势也有着巨大的关注,这种热情甚至已经超过了他多年来对爱情的穷追猛打的热情。他把他的新娘子扔在一边,自己则一口气拿出一叠报纸:《资产阶级立场必须彻底批判》、《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是修正主义的反党口号》、《揭穿用学术讨论掩盖政治斗争的大阴谋》、《揭露吴晗的反革命真面目——吴晗家乡义乌县吴店公社调查材料)},等等。实际上杭得放没有一篇是读懂的,但又可以说是已经领会了深意。他问大哥哥们,中学生有可能介人这场运动吗?从那时候他就看出得茶和吴坤的区别了。但他把这种区别理解成得茶的斗争性不强。他是烈士子弟,他斗争性不强是觉悟问题,没关系,但有的人斗争性不强就是立场问题了啊。杭得放也不清楚自己若出了这样的问题,是划在觉悟上,还是划在立场上。他想关键的关键是不能出现这样的问题。第二天一早他从江南大学出来时,一路上眼前晃来晃去的仿佛尽是那些暗藏的阶级敌人的。撞憧鬼影。
事件发展甚至超过了他们对运动的估计,停课闹革命了,成立红卫兵了,贴大字报,斗老师了。得放一样没落下,但人家偏要落下他。昨天他骑着自行车赶到学校,一见学校里挤满学生,就有一种不祥之感。到班级教室门口时,看见了教室里已经一群群地拥着了许多同学。董渡江眼尖,已经看到了得放,她先跑了出来,声音有些不太自然地说:“你到哪里去了,怎么现在才来?”
杭得放不知道班里发生了什么,但他决定先发制人,热火朝天地喊道:“哎,到江南大学去了!”
一下子就拥上来许多同学,杭得放用眼角扫了扫正在讲台旁的孙华正,立刻就开了讲,原来江南大学造反派给毛主席党中央拍电报了,有近两千人署名,还到省委大院去静坐呢。他的消息够惊天动地的了吧,但同学们看他时都有一种奇怪的神情,仿佛他是条恐龙化石。他花了好长时间才明白,一夜之间,他已经失掉了民心,也就是说失掉了天下。你想他甚至不知道今天班级聚会的原因——原来是选上北京的代表,他当然没份。他问了一句为什么,孙华正冷冷地说,问你爷爷去吧,大字报上都写着呢。顿时就把杭得放问得哑口无言。那天上午从教室出来,他跌跌撞撞,热泪盈眶,怒火万丈,全然没有杭保尔的半点影子。他出乎意料之外地不在第一批上北京名单之中,理由是这样的显而易见,他的血液不纯粹,离无产阶级远着呢;小心你的爷爷被揪出来吧。
如果不是因为受到了严重的挫伤,杭得放不会注意走在他前面的那个长辫子姑娘的。他满肚子的理想计划,从来也没有真正注意过班上的那些不是班干部的女生。此刻他走在学校的大操场上,目光发直地盯在了走在他前面不远处的那两根甩动着的长辫子上。长辫子的发梢上有着两个深绿色的毛线结,它们轻轻地磨擦在那件浅格子的布衬衣上,突然停住了。
杭得放和这个名叫谢爱光的同班女同学,没有说过几句话。在他眼里,她和他的妹妹迎霜一样,都属于一般的女孩。况且,他还听说这个谢爱光有一个背景十分复杂的家庭。班长董渡江曾在一次公开场合上声称,谢爱光能进他们这个学校,完全是一个疏忽,她是条阶级斗争的网箱中的漏网之鱼。这个比喻如此深刻,以至于他一看到这个苗条的姑娘,眼前就出现了一张破了一条口子的大网,一条真正的鱼,缓缓地悄悄地从口子中漏了出去。
现在,这条鱼儿静悄悄地等在了他的身旁——这条长辫子的鱼。
他走到她的身边,看看她。她也看看他,朝他笑笑,像一条鱼在笑。一片碎叶的树影村在她的脸上,她的脸就成了一张花脸。
“干什么?”
他生硬地问。
她显然有些吃惊,脸一下子红了,半张开了嘴。她的嘴很小,像小孩子的嘴。杭得放也有些吃惊,怔住了,说:“你怎么先走了?”
班里的同学还在表决讨论,有许多事情需要立刻作出决断,杭得放被自我放逐了。
她的红云退了下去,她轻轻地说:“我和你同路。”
她的脸又红起来了,她又张了张嘴,像鱼儿在水里吐气,她真是个黄毛丫头,额上颈上毛茸茸的,松软的头发,亮晶晶的,长长的,她同情他吗?那么她为什么要同情他呢?因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吗?因为他也是一条漏网之鱼吗?
他的心尖子都惊了起来,他的一只眼睛警惕万分,另一只眼睛委屈万分,除此之外,他必须保持自己的杭保尔的一贯风度。他干咳了几声,说:“我没关系。”
说完这句话他吓了一大跳,他怎么说出这句话来,这是什么意思?这不是不打自招吗?
她却突然抬起头来,坚定地同时也是张皇失措地表白:“我选你的!”
她的眼睛并不亮,直到说这一句话的时候,她的眼睛才突然亮了一下,然后立刻又黯淡了下去。她的眼睛,和她的头发一样,都是毛茸茸的,不是油亮油亮的。
杭得放不知道为什么,竟然像外国电影里的那些人一样,耸耸肩膀。他只有一张嘴巴,却同时想说两句话,“我不在乎“是一句,“谢谢你“是另一句,可是他没法同时说,所以他只好沉默。在沉默中深入了话题,问:“为什么?”
现在她不再脸红了,她缓缓地走在了他的身边,看样子她也是一个杭保尔迷,只是隐藏得更深罢了。她依然激动,但注意控制自己,她说:“一个人应该公正。”
他看了她一会儿,出其不意地问:“你们家也有人被贴大字报了吧?”
她显然没有想到他会这样说话。她怔住了,脸白了下去,他亲眼看到她的脸从鼻翼开始发白,一直往耳边白过去,甚至把她面颊上的浅浅的几粒雀斑也白了出来;然后,他又看到她的浅浅的眼窝里水浮了上来,像是小河涨水一样;他看到她的眼睫毛被大水浸泡了,有的竖了起来,有的倒了下去,这是他第一次发现女孩子的眼睫毛。最后,他看见她像电影里的慢镜头一样,缓缓地,倒退着,走了。她走过了操场边的那排白杨树,走过了白杨树外的沙坑,走过了双杠架子。阳光猛起来了,晒得操场泛起了白光。杭得放先是看不到她的绿辫梢,接着就看不见她的长辫子,再接着,就看不见她的人了,她仿佛整个儿的,都被耀眼的强光吞没了。
生活所呈现出的奇异瑰丽的一面——那些瞬息即逝的一瞥,那些游离在主旋律外叹息一般的副调,那些重大事件旁的琐屑细事,原来正是它们,像被树叶倒影切碎的阳光一样,闪烁在我们度过的时间深处,慰藉我们的生命。然而,在阳光没有被切碎的岁月,往往在我们把它称之为青春的那个阶段,我们看不到世界对我们的体恤,我们看不到那双注视着我们的眼睛。
总之,中学生杭得放的心思被眼神微微拉动了几下,眼神就断了,很快就又被挫败感吞没了。他万分委屈,失去常态,找不到更痛切的词儿来诅咒人们的背信弃义。他又痛恨自己掉以轻心,没有做好思想准备——是的,他应该有落选的思想准备,他应该有!别人只把他看成一只小公鸡,那是不对的!是看走了眼!他要比一只小公鸡深刻多了,复杂多了!忍辱负重得多了!后来他开始伤感,孤独,那天夜里辗转反侧,脑海里一片毛泽东诗词——啊,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而早晨起来时,他已经进人惶恐。他越想越不对头,越想越害怕,他不能没有集体,不能失去战斗……
他本能地又朝江南大学飞奔而去,他还是需要他的哥哥杭得茶给他打气。爷爷已经开始受到冲击,偶像已经倒塌,但他相信,杭得茶是不会倒塌的。
江南大学门口停着一辆宣传车,有人在车上的大喇叭里反复喊: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黄军装,标语,口号,糊糊桶,高音喇叭,宽皮带,再加上一个朗朗夏日——够了,青春就这样立刻进人颠覆期,几乎成了一种生理反应。十分钟内,三好学生杭得放完成了人类历史上最迅猛的脱胎换骨。在他的青春期,有着许多难言的痛苦,以往他从来也没有想到过要通过外力来解决,更不要说是像当下那样的暴风骤雨般的外力了。现在好了,一切摧枯拉朽,一切荡涤全无,一切正常的和非常的苦恼如今都有了一个借口,一切的秩序都将彻底砸烂——我们迄今为止所经历的心事都将有一个宣泄口——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他把他那辆飞鸽牌自行车随手一扔,就跑上前去打听:中国发生了什么?世界发生了什么?嗅!嗅!嗅!原来是这样,竟然有人敢反对毛主席,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竟然出现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要让中国人民受二茬罪,吃二遍苦,红色江山从此变黑!这还了得,我们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向他宣传革命真理的是女中的赵争争,杭得放去年在夏令营时见过她。那时她梳着长辫,辫梢也有臭美的蝴蝶结,而今迈步从头越了,两把小板刷,英姿飒爽。杭得放一开始还问她,她们这么出来,是谁组织的。赵争争气势磅确地反问他:革命需要批准吗?造反需要思许吗?克伦威尔是有了批准才进行英国革命的吗?巴黎人民是有了批准才攻打巴士底狱的吗?阿芙洛尔巡洋舰是有了批准才有了十月革命那一声炮响的吗?革命者失去的是锁链,得到的却是整个世界!不用理论来证明什么——你只要走出校园,从你那些棺材板文化中抬起头来,举目四望,你就知道,全中国都已经沸腾了。从中央到地方,从工厂到学校,从城市到农村,人民已经最大限度地被发动起来了。海燕在天空飞翔,它在迎接暴风雨,它在呐喊——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杭得放看着她,简直就如看着一个天外来客:这种说话的腔调、词汇,走路的直挺腿与八字脚,红袖章和扎着牛皮腰带的腰,同样是一身旧黄军装,穿在赵争争身上却显得气宇轩昂。这才是革命!这才是生活!这才是理想!什么推选——让一切推选之类的鸡毛蒜皮见鬼去吧!他拿眼前的这一位比较起他自己学校中的那几位来,真是有比较才有鉴别,两下里一对照,他们学校的什么董渡江什么孙华正,简直就是小儿科,就是杭谚里的“蟑螂灶壁鸡,一对好夫妻“。杭得放的脑海里像是在过电,胸膛上仿佛在滚雷,真是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他面孔煞白,双目发呆,他仿佛在思考着什么,其实什么也没有思考。他只是强烈感受到,一定要和眼下的革命者在一起,只有和他们在一起,才有出路,才有前途,才有未来。杭得放就这样跟着赵争争进了大学门,谁知被他的堂哥泼了一盆冷水。
杭得茶决定从事他选定的专业研究时,少年杭得放就有些不理解,他自己是对那些所谓的食货之类的东西一点也不感兴趣的。他的心向往未来,希望有感受新事物的狂喜。但他尊重茶哥,把这疑惑藏在心里。他不能接受的现实是,时至今日,如火如某的形势,茶哥怎么还要到湖州去考茶事之古,还要去接什么新娘子,婆婆妈妈的怎么就到了这个地步!他怎么会对局势发展保持这样一种少有的冷静,在他看来,这已经是近乎冷漠了。甚至在听到他亲爱的弟弟没有被推选为第一批上北京的红卫兵之后,也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忧心忡仲。他说,文化大革命究竟怎么搞,搞成多大的规模,还有待于时间定论。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中国共产党的天下,事情并没有发展到一夜之间人头就要落地的地步,他总怀疑,有些人把局势估计得那么严重,是有其自身的不可告人之目的的。
杭得放用一种不可思议的目光盯着他的茶哥,他甚至认为他的思维是不是出了问题,他怎么还会得出这样大错特错的估计,一个崭新的世纪就要开始了,旧世界砸个落花流水奴隶们起来起来……
得茶真的不知道得放的这种激情究竟是从哪里来的:什么是旧世界?为什么要砸个落花流水?谁是奴隶?得茶在攻读史学中的确已经养成了吃猪头肉坐冷板凳的习惯,凡事不务虚,他对那些大而无当的口号,本能地就有了一种抵触和警惕。
“这一次你肯定错了!”
得放盯住了得茶的眼睛,说,“你肯定错了!你看着吧,你会为你的错误路线的立场付出代价的。”
“我不要你的结论,我要你的论据论证。”
“你错了!错就错在你给我设置了一个理论的圈套,可是我不会去钻!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克伦威尔是有了论证才进行英国革命的吗?巴黎人民是因为有了论证才攻打巴士底狱的吗?阿芙洛尔巡洋舰是因为有了论证才有了十月革命那一声炮响的吗?不用理论来证明什么——你只要走出校园,从你那些棺材板文化中抬起头来,举目四望,你就知道,全中国都已经开始沸腾了。从中央到地方,从工厂到学校,从城市到农村,人民已经最大限度地被发动起来了。海燕在天空飞翔,它在迎接暴风雨,它在呐喊——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海燕在呐喊,杭得放也在呐喊。他在得茶的斗室中来来回回地走,形如困兽,怒气冲冲;鹦鹉学舌,豪情万丈。他接受这些言论与思想,不过是在刚才,但仿佛这些言论和思想的种子从来就生在他脑子里,只是一场春雨把它们催发了出来罢了。他的口才、他的学识、他的勇气和魁力,像原子核突然核裂变,放出了人们根本无法估算的能量。
比他大七八岁的哥哥大学助教杭得茶,虽然被他依旧大而无当但毕竟如暴风骤雨般的演讲镇住了。他紧张地看着得放,心想,会不会是我真的错了呢?人民群众正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