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容青史尽成灰-第5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景时代对匈奴小规模战争里成长起来的他,手里有一支足够与匈奴骑兵抗衡的骑兵部队,可以通过以机动对机动的方法,击退匈奴的入侵。其他几位就比较惨了,比如在平定七国之乱中立下战功的韩安国,奉命驻守河北地区,被匈奴人攻破渔阳,仅依托右北平苦苦支撑。从公元前134年马邑诱敌战失败,到公元前129年,这6年时间,是汉匈战争里汉朝最惨的6年。匈奴几十万骑兵部队在汉朝边境声东击西,纵横驰骋,焚毁杀掠城池无数,掳掠人口数万,汉朝北方边境的生产遭到极大破坏,汉军伤亡也极其惨重。仅以军事主官论,辽西一地两任太守相继阵亡,雁门两任太守殉国,主将伤亡如此,军队伤亡更不必说。这5年的固定剧本,就是匈奴人袭扰、破城,汉军赶来迎战,匈奴人跑,汉军撤回,匈奴人又杀过来。偌大的汉帝国,在几千里漫长的北部边境上,被匈奴人牵着鼻子走,打得气喘吁吁,败绩连连。
直到公元前129年的这一战,汉匈战争具有转折意义的一战,不是胜利,而是一场空前的惨败。
这一年的秋天,匈奴集中近10万骑兵,对汉朝边境改为重点打击,打击的对象,就是北部的重镇上谷郡。匈奴一如既往地连战连捷,杀掠无数,汉朝一如既往地顾此失彼,丢城失地。此时的汉武帝刘彻,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不再是被动地派兵救援,而是派重兵以攻对攻,杀入匈奴境内进行反击。这是汉朝建国历史上,乃至中原王朝历史上,中原军队第一次深入草原,进行长途奔袭。即使是当年横扫六国的秦军,都不曾有这样的胆气。
仅仅有胆气是远远不够的,汉武帝这次动用了四路大军,分别是李广、公孙贺、公孙敖、卫青。前3个都是多年以来对匈奴战功卓著的名将,唯独卫青是个菜鸟,沾了韩安国告病的光,补了他的缺。而他也是4个将军中公认“被鄙视的”:他是靠了姐姐卫子夫得宠才飞黄腾达的,原本的身份就是个骑奴,很明显是4大将军里凑数的。战斗开打后,汉军的表现还是惨,尤其是3位名将,李广遭遇了匈奴单于的主力,被匈奴人以3倍兵力合围,一万骑兵全军覆没,其本人也惨遭俘虏,被俘路上夺马逃回。公孙敖在代郡遇到了与自己兵力大致相等的匈奴军,一番硬碰硬地厮杀,被匈奴人一口气消灭了7000多人,还好跑得快,总算避免了全军覆没的下场。公孙贺部更是胆小鬼,率军在边境上吆喝了几声,一枪没放就返回原地,连敌人的影子都没见到。为惨败的汉军挽回面子的,却是“菜鸟”卫青。趁匈奴军重兵合围李广的机会,卫青率部大胆穿插,长途奔袭800里,直捣匈奴人祭天的圣地龙城,一口气歼敌700。这场战果看似一般的胜利,在当时的汉朝,却有非同一般的意义:这是汉军自建国以来,对匈奴战争的第一场野战胜利。
刘彻这次愤然发动的主动反击战,并非是心血来潮。相反,是汉朝对匈奴作战方式的一次调整。作为深谋远虑的军事家,汉武帝刘彻早就意识到,靠着长城的被动防御,是无法战胜匈奴的,相反整个汉帝国的战争机器都会被匈奴人牵制住,要化被动为主动,只能采取主动出击的政策,在草原野战中摧毁匈奴的据点,重创匈奴的主力。但谁能担负起这样的使命呢?公元前129年的上谷反击战,其实就是汉武帝对汉军将帅的一次“考试”,成绩单上,李广不及格,公孙敖不及格,公孙贺不及格,而成绩优秀的卫青,才是唯一的人选。
【二】
卫青在公元前129年的这场胜利,表面看确实有运气成分,毕竟他躲过了匈奴的主力,且成功找到了匈奴人防守最薄弱的龙城,但运气从来不是天上掉馅饼,在匈奴人大兵压境的局面下,能够穿过匈奴人的防守空隙,避实击虚,打击敌人的薄弱部位,这本身就是一个帅才的能力所在。其他的几个人,李广足够彪悍,公孙贺足够谨慎,冲锋陷阵或者掩护撤退都可以,但是想统筹全局,却远远不够。
事实上,上谷之战,是一场全方位打出汉军差距的一战。以公孙敖部为例,在部队数目大致相等的情况下,汉军在骑兵战里输得一塌糊涂,伤亡率远远高于匈奴。即使是卫青反击龙城的胜利,1万汉军骑兵包围1000匈奴骑兵,依然无法做到全歼,让300多匈奴骑兵突围出去。在汉匈战争的早期,汉朝士兵在战斗力特别是骑射战斗力上的差距,与匈奴人相比依然是明显的。
此战之后,汉朝的边境局势非但没有改观,相反却有持续恶化的趋势:公元前128年,匈奴人再次入侵,这次重点打击的对象换成了辽西。辽西太守殉国,辽西汉军几乎全军覆没。之后匈奴人兵锋南转,又对雁门地区展开了大规模的扫荡。一支8000人的匈奴骑兵部队,竟然深入到了雁门腹地。危急之下,还是卫青抓住了战机,提出了主动出击,聚歼这股匈奴骑兵的建议。依卫青奏报,汉朝命距离雁门最近的李息火速出击,以其劣势兵力缠住匈奴人,同时命令卫青率领3万骑兵火速驰援雁门。李息部浴血奋战,以所部3000多人大部分阵亡的代价,终于成功拖住了匈奴军,等来了驰援的卫青。结果,汉军以绝对优势的兵力,终于全歼了这股骄横的匈奴部队,斩首6000多人。这是自汉朝开国以来,对匈奴作战斩首数目最多的战斗。这时期的汉军,虽然在个体战斗力上仍无法与匈奴相比,但是集中优势兵力以攻对攻打歼灭战的思路,终于开始收到成效,而执行这个思路的最佳人选,就是卫青。他没有李广百步穿杨的武勇,却有高出众位悍将一筹的卓越战略眼光。这才是此时的汉军最需要的。
也正因如此,在雁门之战结束后仅数月,卫青又演出了他军事生涯里的第一笔光辉之作——收复河套。
汉朝对匈奴反击战开始后,整个北方战线,其实是分成东西两段的,早期匈奴的入侵,主要是集中在东线地区,即河北和右北平、辽西一带。但对汉帝国威胁最大的,却是西线匈奴盘踞的河套草原地区。这是一颗匈奴人插在汉帝国北部边境的毒牙:有了河套地区,匈奴人就有了一个距离长城最近的立足点,他们可以源源不断地得到兵马补充,进可攻,退可守,汉匈战争6年来牵着汉军鼻子走,根源就在于此。要打赢,就要拔牙,能拔牙的,只有卫青。
雁门之战后,认为自己蒙受了耻辱的匈奴,再次发动了对汉帝国边境的报复。他们打击的重点,依然是早已被侵扰得残破不堪的东线地带,然而汉朝出人意料的反击开始了。公元前127年,卫青从云中出发,沿黄河北岸高速疾进大迂回,一举攻入河套草原。这场进攻出乎匈奴人意料:以匈奴人的理解,汉军从未发动过如此长途的骑兵奔袭作战,即使发动,他们也应该从南方进攻。然而卫青却大胆穿插,从匈奴人的背后直插河套,猝不及防的匈奴守军登时大溃。卫青先占领黄河北岸的高缺等地,切断匈奴军退路,再以重兵合围,发起总攻,匈奴人几乎无法做出像样的抵抗,就全线崩溃,整个河套草原就此落入了汉军之手。这是汉匈战争里的一个重要拐点:夺取了河套草原的汉王朝,在当地修筑营垒,设立定襄郡,屯守部队10多万人,河套,从此成为了汉军北上草原、反击匈奴的主阵地。河套丰美的水草和丰厚的战马储量,更成为汉朝骑兵的主要来源地。
河套的丢失,引起了匈奴方面的震怒,从公元前127年汉军夺取河套开始,至公元前124年,短短3年间,匈奴人至少发动了10次反击河套的战役。这3年也是汉朝经营河套的关键时期,汉王朝发动民夫10多万,在河套修筑长城,驻守兵马,将其真正纳入汉王朝治下。卫青更率部数次击退匈奴人的进犯,以成千上万将士血的代价,汉朝终于在河套草原扎下了根、站住了脚。而战争的天平,从此倾向了汉王朝。
让匈奴彻底断送收复河套希望的,是公元前124年的漠南之战。
这时期对于河套草原威胁最大的,就是直接暴露在河套眼皮底下的匈奴右贤王部,作为匈奴汗国的“右臂”,右贤王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在这3年河套的拉锯战中,右贤王更是急先锋。在河套铸城工作业已完工的情况下,汉朝终于可以放心地发动对右贤王的歼灭战。公元前124年,汉军兵分两路,李息、张次公主动出击右北平,牵制匈奴左贤王部,卫青则率主力骑兵3万人再次长途奔袭,出塞700里直扑右贤王大营。毫无提防的右贤王顿时崩溃,其所部10万余人大多逃散,汉军斩首上万,俘虏1万5千多人,匈奴的“右臂”几乎被打残了。这一战之后,原本作为“统一汗国”的匈奴汗国,被汉王朝切割成几段:原本被匈奴汗国直接统辖的河西走廊,从此断绝了与匈奴本部王庭的联系,右贤王的部落也因此北迁,匈奴对汉帝国边地发动大规模侵扰的难度大大增加,说此战是汉帝国掌握战争主动权的开始,毫不过分。另一个值得一提的是,以往汉军与匈奴作战,特别是野战里的胜利,都是通过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方式实现。但漠南之战,卫青以3万骑兵,对10万之众的右贤王部发起进攻,以寡击众,最终大破之。汉帝国士兵在个体战斗力上的素质,已不在匈奴之下。
这正是卫青的贡献,如后来南宋军事家岳飞所言:战法革新破匈奴,卫青始。
说到这条,还要说到汉匈双方的优劣对比。汉人在骑兵素质上的先天差距,与匈奴相比是巨大的,毕竟汉人是农耕出身,骑马需要后天学习,而匈奴人是马背上长大的,这个差距是天然的。从白登之围开始,历代汉朝臣工们都在开动脑筋,考虑如何弥补这个差距。比如平定七国之乱的周亚夫,就在弩箭的使用和战车的改装上有过尝试,而汉景帝时代的名臣晁错,则主张用招募匈奴人从军,教习汉人骑射的方法来提升战斗力。汉武帝之前,在骑兵战探索上最有成就的当属李广。李广是一个完全“匈奴化”的将领,他个人的骑射水平不在匈奴名将之下,他的军队是一支具备匈奴人彪悍特点的军队,甚至连日常的行军打仗、纪律管理,都是学习匈奴人“逐水草而居”的特点,全无汉朝军队的繁文缛节。但相比之下,卫青更进一步,在着力打造一支精锐骑兵的同时,并没有抛下汉人本身的军事优势,即汉族士兵的高科技优势以及高度的纪律性,正是这两点,成为卫青成功的关键。
与现代人的想象不同,卫青的军队,并非纯粹骑兵军队,其军队的重要特点,就是配备了大量战车。战车的作用,一是行军中作为营地,二就是在战斗中摆成防御工事。卫青的战车主要是弩车,即配备精良弓弩的战车,其弩箭的射程与杀伤力,远远强于匈奴人使用的马弓。比起李广单纯以硬碰硬、以骑兵对冲的作战方式,卫青的战法往往比较复杂。在野战遭遇敌人时,首先采取战车固阵,用密集的弩箭阻遏匈奴骑兵的进攻,并且在战斗中,战车作为移动的堡垒,有时候更能起到合围匈奴人,断绝匈奴人退路的作用。比如在漠南之战中,卫青就是以战车断绝右贤王逃路,射杀大量匈奴骑兵,迫使匈奴残部投降,一举俘虏1万5千多匈奴人。而卫青的另一个贡献,就是轻重骑兵的配合作战。卫青的骑兵部署里,有专门用作冲锋的重装骑兵,也有作为掩护和侧翼包抄的轻骑兵,战斗之中,轻重骑兵相互配合,先以轻骑兵射杀,重骑兵中央突破,战局相持时,又以轻骑兵包抄,切断匈奴骑兵队形。这种轻重骑兵加战车协同作战的战法,成为骄横的匈奴骑兵的噩梦。也正是从这时期开始,面对人数相等甚至人数占成倍优势的匈奴骑兵,汉军不但不再躲避,相反可以勇敢亮剑,甚至战而胜之。
然而作为横扫草原的强军,以战争为生命的匈奴人也不是傻瓜。漠南之战的结局,不但成为汉匈双方作战态势的转折点,更成为匈奴人对汉朝作战方式的转折点。漠南惨败后,匈奴人改变作战方式,不再大兵团袭扰汉朝边境,相反是小部队骚扰汉朝边境村庄,采取叼一口就跑的游击战术,消耗汉军防御。趁汉军疏于防范时,再发动大规模的入寇。这一战术起初收到了效果,公元前123年,匈奴以1万骑兵进入代郡,大肆烧杀抢掠,汉朝一如既往,采取以攻对攻的策略,以卫青率领10万大军出河套,直扑匈奴单于王庭。但这一次,汉军却碰了“软钉子”:匈奴人不再以大兵团阻击汉军,相反且战且退,一旦战事不利,就有组织地节节抵抗后撤。结果卫青虽然累积斩首匈奴军1万多人,却始终无法捕捉到匈奴主力,反而前锋赵信部的3000多人,在孤军深入后遭到匈奴重兵围困,全军覆没不说,赵信本人也在被俘后投降了匈奴。这场损失不大的挫折,成了汉军的新问题:在匈奴转守为攻的情况下,其骑兵的机动性,完全可以诱引汉军深入匈奴境内,趁汉军兵力分散时予以围歼。他们不再是彪悍的战狼,相反变成了狡猾的毒蛇,表面缩头,你不注意的时候,突然咬你一口。
匈奴战法的改变,是汉军“新形势下的新问题”,在“正战”难以占到便宜的情况下,匈奴人也开始学会“诱敌深入”、“聚而围歼”。卫青原本提倡的防守反击,避实击虚,有限度长途奔袭的战术,固然可立于不败,但给敌人毁灭性打击却是难。汉朝现在需要的,是一个能够更加以机动对机动,对匈奴人有纵深打击能力的悍将,这个人选在当时也只有一个——霍去病。
【三】
作为卫青的外甥,霍去病很长时间以来,也是个颇受争议的人。比如他年纪轻轻就获得重任,被人诟病成“裙带关系”;又比如他性格骄狂,贪图享乐,甚至为报私仇杀死李广之子李敢。这些“私德”问题很长时间以来也为史家诟病,但无可争议的是:他在当时汉军中的身份、地位、战功,与他的能力是绝对匹配的。在匈奴转攻为守的战略局面下,卫青是巩固既定战果的人物,霍去病,却是能给予退缩的匈奴持续毁灭性打击的唯一人物。
在汉朝抗匈名将的排名里,世人往往以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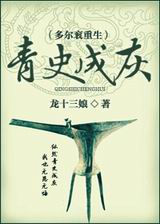
![[死神]活着不容易封面](http://www.8btxt.com/cover/47/47621.gif)
![[三国]空余青史颂玄机封面](http://www.8btxt.com/cover/51/51689.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