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容青史尽成灰-第3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税。至于杂赋,一般都是在遭遇战争的时候临时征调的,现在天下太平,老百姓的负担,表面上看也不会太重。与此同时,货币、度量衡、文字,也都在这一时期统一了,秦国的法律《秦律》也颁布全国实行。分散的中原六国,渐渐被秦始皇捏成一个统一的力量,观这些行为,我们必须承认,早先的秦始皇,还是很有励精图治一面的,在捏合整个国家合力,加强中央集权方面,他都做得很不错。
【二】
秦国国事的恶化,通常的说法是“暴政”,暴政的内容,主要包括大兴土木营造宫室,修筑秦始皇陵墓、阿房宫等。但真正劳动百姓最甚的,是三项重大工程,一是修筑长城;二是修筑国内的驿站道路;三是整治国内的河道。
这三项大工程,几乎都是前后脚展开的。秦始皇开凿运河,范围非常广。在平灭六国后的第二年,就曾经发动10万民夫整治江南的邗沟,以及山东的济水运河。与此同时,秦始皇派30万大军收复河套平原后,又一口气征发了40万民夫整修长城。公元前219年,秦始皇又再次征伐40万民夫,整顿国内的驿站,以关中平原为中心,修筑了连接中原以及南方的驿站道路。这三项大工程,从作用上来说,都是对国家未来发展有好处的,修筑长城可以起到抵御外敌的作用,后来作为封建王朝盛世的汉朝就从中受益颇深。开凿运河,有利于促进农业生产,这也具有长远的意义。而修筑驿站,更可以促进国家交通,加强各地的联系,保证国家的统一。这三条从出发点上是好的,但是就在这短短几年里,秦始皇连续征调了90万民夫,要知道,当时全国的人口才不过2000万人。这90万民夫,大部分都是青壮年,也就是说,全国至少有三分之一的青壮年,都被秦始皇拉出来干工程了。
这样的结果也就很简单,生产当然遭到破坏,老百姓家干活的,就剩下老弱了,生产能力自然大打折扣,生产能力打折扣,国家的财富税收当然也要打折扣。与此同时,秦始皇还在进行着征讨南方越族的战争,不断向南方越族地区征兵,打下地盘后,一面要修筑中原通向南方的驿站,一面又要修筑南越地区的水利工程。这样,原本刚刚在中原地区干完活的民夫,一下子又尽发到了南方地区,中国人从来都是恋家的,离乡背井永远是最痛苦的事情,怨声载道也就很自然了。当然,我们也同样可以说,开发越族地区是有积极意义的,比如说促进了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融合,但这些后来的伟大意义,当时的人是没感觉的,士兵们只知道,他们被派到一个艰苦的环境下作战,常年得不到休整。老百姓只知道,天下好不容易统一了,皇帝却又逼着我们干活,拿着我们当牲口使唤,对秦始皇的愤懑,也就这样一天一天地积攒起来了。
而秦始皇最大的错误,不是在于他做了这些事,而是在于他同时做了这些事。看看当时南北方的分布就知道了,在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的最初六年里,秦国30万大军压在北方对付匈奴,50万大军压在南方对付百越。这一南一北就是80万大军,等于两线作战,即使是一个现代化国家,两线作战也往往是兵家大忌,何况是一个立国不久、经济凋敝的新兴封建制国家。军队的事情还不算,民夫的使用却更触目惊心,在南方越族地区平定后,秦始皇陆续调动了40多万民夫南下开凿运河,打通驿道,这些人大部分都没有回来。也就是说,秦国在立国之初,最需要休养生息的时候,却一直还在做着大动作,一直在折腾。这些原本没错的事,却偏偏超过了这时期中国的承受底限。
但问题是,秦始皇为什么会犯这个错误?有说他好大喜功的,有说他不知下情的,有说他性格残暴的,然而从根子上,我们不得不说,秦始皇做这种事情很正常,因为这就是秦国国君的习惯。
看看战国时期秦国的历史就知道了,秦国在秦孝公改革后的130多年里,就一直处于折腾中。从秦孝公到嬴政,秦国除了有过短暂的罢兵外,几乎是无岁不征,年年打仗,但是秦国的国民经济不但没有拖垮,反而越来越强。秦国历代国君在使用民力上,从来都是不吝啬的,比如秦昭襄王时期,就曾下令全国16岁以上的男子全都从军,开赴长平战场,也因此一下子奠定了长平之战的胜利大局,这一场战争让秦国伤亡过半,但是仅仅一年后,秦国又以50万大军包围邯郸,却遭到了魏国、楚国的联合夹击,大败亏输。即使如此,秦国也很快地恢复过来,不管每次他们付出的牺牲有多大,伤亡多惨重,他们这种迅速的疗伤能力,是六国里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及的。
秦国之所以有这样的疗伤能力,不是因为秦国人觉悟高,而是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商鞅变法后,经过两个阶段的持续推行变法,确立了秦国人对法律的绝对敬畏感,这种敬畏感,制造了秦国令行禁止的特征,几乎所有出使秦国的六国使臣,都曾羡慕过秦国官员的严谨守法。但这样的条件,是无法短期内复制给其他诸侯国的。另一个重要条件是,当时秦国有奖励军功的政策,发动战争,本来就是给草根们出头的机会,而秦国人天生彪悍尚武的性格,使他们从来不惧怕死亡。但是那些新被平灭的六国,却不是这样的,拿着对秦国百姓的政策对待他们,只能说是找错了对象。
但秦始皇显然认识不到这一点,当年,以秦国区区一二百万人口,就可以发动百万人的军事行动,七八十万人的大型水利工程,现在我手里有2000万人,又怎么能说滥用民力呢。但问题是他手里的2000万人,来自于五湖四海,他的百姓也不止包括关中平原。在国家刚刚统一,人心思治的情况下,却依然继续在折腾,任谁也不会满意的。
当年秦国变法的实质,就是动用国家机器的力量,树立严格的法律,建成一个高效率的专制国家。在统一了六国之后,秦始皇也打算这么做,但是无论时机还是经济条件,都不成熟了。
偏偏秦始皇自我感觉好得很,折腾的事情越来越多,至于他这时期被人指摘的各类劣迹,比如修阿房宫,修秦始皇陵,整日骄奢淫乐,其实这些都是做皇帝的“小节”问题。大节问题是,他没有搞清楚这个国家建设的主次问题,需要先做什么,后做什么。而且这不是他突然犯的错误,而是一个经常有的软肋。
秦始皇这个人,具有果敢的性格,顽强的精神,豪气干云的做派,确实是一个天生的王者。但是秦始皇的一大毛病,就是他的战略选择问题。早年在灭六国的时候,为选择一个什么样的顺序,他曾经辗转反侧,举棋不定,最后还是在尉缭的帮助下,才找到了国家统一最后一步的钥匙。秦始皇具有坚决的执行能力,狂热的工作欲望和权力欲望,但是他最缺少的,恐怕就是有的放矢的素质。这一点素质的差别,使他演出了在登基之后的这一出闹剧。
秦始皇犯了错误,但更大的悲剧是,他的这个错误从他即位之后就一直在继续着,秦始皇从公元前220年起,就开始营造富丽堂皇的阿房宫,而在公元前218年起,他的骊山墓葬群也开始修筑,一个秦始皇陵,又调动了70万民夫。全天下的青壮年,都要绕着他来转。他忘记了一件事:六国灭亡后的中国,最需要的不是大工程、大面子,最需要的是要医疗战争的创伤。平定越族的战争,原本是可以暂缓的,秦始皇偏偏想几手都要抓,既要恢复经济,又要上马工程项目,最后长城修起来了,秦朝却摇摇欲坠了。
秦始皇的错误,他自己在世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相反还很是洋洋得意。在他登基之后,曾多次出去巡游,比如东巡、南巡,劳民伤财更是无数。但巡游同样也是有理由的,此时国家初定,各地人心惶惶,巡游可以起到安定人心的作用,稳定国家大局。理论上说是没错,但中国老百姓的要求很简单,他们想的是安安心心地过日子。秦始皇晚年的另一个搞笑事,就是他开始信任方士,到处求神仙,甚至还出了徐福东渡的典故。统一大业完成后的秦始皇,其表现做派,和他统一六国的征战时期判若云泥,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改变呢?
其实在中国历史上,像这种国家结束分裂后迅速陷入战乱的典故,不止秦朝这一家。比如西晋,比如隋朝。而且西晋和隋朝,都是经过了几十年修养生息后完成国家统一的,国家的财政储备和人口数量,都要远远好于这时候的秦朝。但即使如此,一旦使用民力不当,国家内外政策失调,就会立刻陷入分崩离析之中,无论是古代王朝还是现代文明国家,他的内外政策都好像是天平的两端,只有天平保持平衡,国家才能保持长久的稳定。而在秦始皇时期,他的政策是在天平的两端,都拼命地加砝码,结果就是整个天平的断裂。
为什么会犯这样的错误?
其实所有关于秦始皇的评价中,或许有一个人的评价,是一针见血的,就是曾经在秦始皇手下做过国尉,中国历史上的杰出军事家:尉缭。
尉缭这个人,在辅佐秦始皇时期,最出色的地方,就是他卓越的战略眼光。在确定灭六国的方案时,正是他制定出来正确的政策,保证了秦国顺利完成国家统一。然而尉缭却还有一个能力:看人的眼光。当年秦始皇还只是秦王的时候,他就一眼看穿了秦始皇最大的弱点:“缺少恩德,心似虎狼;在困境中可以谦卑待人,得志于天下以后就会轻易吞食人。”当时的秦始皇听到这个评价,反而对尉缭非常赏识,因为在他眼里,这本身就不是什么缺点。
这正是秦始皇的悲剧所在,一个心似虎狼的人,也许在沙场上是一个出色的将军,但是在皇位上,却注定不是一个出色的皇帝。同样和秦始皇一样有暴君称号的隋炀帝,当年也是一个出色的将军,可是在成为皇帝之后,照样干得稀里糊涂,心似虎狼不要紧,缺少恩德也不要紧,中国历史上那些名垂青史的好皇帝,心似虎狼的也不在少数。但秦始皇最大的弱点,就是尉缭那番评语里的最后一句“得志于天下以后就会轻易吞食人”。这句话被尉缭不幸言中。说到底,秦始皇不懂得压制自己的欲望,一旦志得意满,就立刻露出了虎狼的面目。
在秦始皇活着的时候,各地对秦始皇的反抗就开始了,秦始皇一生最不缺少的,就是“被刺杀”。而且刺杀的次数日益增多,但是他自己却到死也不悟,之后四处巡游,耀武扬威,泰山封禅,炫耀荣光,秦国的气数,也在这股过程里日益被他透支干净了,同时被透支干净的,还是他个人的气数。到了公元前210年,秦始皇病死于东巡路上的时候,一场巨大的抗暴运动,已经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三】
在秦始皇的悲剧中,似乎还藏着另外一个原因,一个后人关注不多的原因:秦国的法家传统。
众所周知的是,秦国的强大,来自于商鞅变法。商鞅变法的思想,主要是法家的思想。在乱世争天下时期,通过严刑峻法,外加残酷的外在生存条件,只要树立起足够的国家威严,就可以确保国家迅速集结战斗力,取得对外战争的胜利,并且日益走向强大。但是当国家走向统一,开始和平建设的时候,法家思想却暴露出他致命的缺陷:至刚而无柔。
法家思想的主要特点,就是严刑峻法,让整个国家,都笼罩在恐怖的刑罚监督中,用严苛的刑罚来镇压一切反对者。但是随着国家主要矛盾转移,法家思想在休养生息时期,却完全失去了它本身的积极作用,相反成了消极作用。与此同时,法家常年压制所造成的怨怒,一旦出现风吹草动,就会发生从民间的彻底反弹。引发巨大的抗暴动作,就像马背上打天下,马背下治天下的道理一样,法家思想可以打天下,但是法家思想却难以治天下,一个缺少温度,用冷漠和刑罚来约束的王朝,他的生命力也注定是僵硬的,即使强悍如秦军,即使气吞万里如秦始皇,都不能挽救它的衰亡。
秦朝二世而亡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法家思想在到达历史顶点之后,迅速走向衰亡的历史。事实证明,单纯的法家治国,在乱世或许立竿见影,但在太平盛世,反而会成为国家动乱与衰亡的催化剂。百家争鸣的各类思想中,法家注定已经完成了他的使命,而真正有资格成为中国之后2000年封建社会传承的学说,是后来的儒家学说。那时候的法家,也只能将其核心要义化入儒家思想之中,成为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法家思想在战国时代的风光,也只能留存在战国时代了。
这就是秦始皇的悲剧所在,他在得天下后的种种暴政,有他个人性格使然,却也有法家思想的影响使然。作为一个在法家文化环境里成长起来的少年,更兼带有祖上法家的代代传承,要求他主动地在得天下后转换思路,实行仁政,这是一个何其高难度的动作。对于秦始皇来说,做到这一点是不现实的,所以秦国的持久强大,也因此是不现实的。
第三十章 苦命的好人——秦末帝子婴
作为中国历史上大一统后迅速败亡的短命王朝,秦朝在历史上的得分一直不高,从秦始皇往下,满朝文武数下来,除了仁厚的秦始皇长子扶苏,立功河套草原的名将蒙恬外,真貌似是“洪洞县里无好人了”。指鹿为马的宦官赵高,愚蠢无能的秦二世胡亥,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丞相李斯。一个个挨个看,可以说是一个比一个可悲,历史上各种类型的反面角色,在这个倒霉政府里似乎全齐了。
然而,到了秦朝灭亡后近百年的汉朝,无论是西汉修史的司马迁,还是东汉历史学家班固,在淘尽岁月的泥沙之后,都不约而同地对这时期,秦朝体制内的一个人,做出了崇高的评价。司马迁说这个人有拥主之才,如果给他机会,足够守住秦国的基业,东汉的班固更赞叹他“死生之义倍”,是个对得起秦国祖先的好男儿。这个得到两汉历史学家不约而同高评价的人,就是秦朝末帝子婴。
有关子婴的身份,现代资料留存下来的不算多,唯一可知的是他是秦国王室宗族,具备继承秦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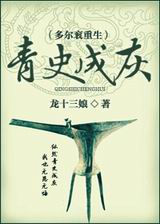
![[死神]活着不容易封面](http://www.8btxt.com/cover/47/47621.gif)
![[三国]空余青史颂玄机封面](http://www.8btxt.com/cover/51/51689.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