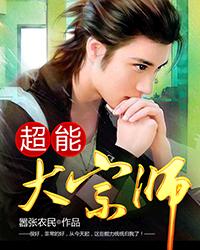唐玄宗-第20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哦,原来是他。算来他的年龄也不小了。竟然还活在人间,他如何又成了绵郡太守?”
“臣见齐瀚来此,也觉奇怪,就多问了几句。他当初因过被贬为县尉,此后又任两道采访使,再迁汴州刺史、润州刺史,后来不知如何得罪了李林甫,再迁为平阳太守,终为绵郡太守。”
“呵,想不到他的宦途如此曲折,能存留至今,实属不易了。嗯,让他进来吧,如今天色已晚,就留他共进晚膳吧。”
齐瀚入内,此时也是银髯飘飘,李隆基见之不免感叹道:“岁月如刀啊,齐卿昔在中书省之时,何其俊雅飘逸,不料今日也成为一老者了。”
齐瀚礼毕后,忽然老泪纵横道:“臣入蜀多年,本想再难见陛下之面,不料陛下幸蜀,臣……臣感叹由之……”
李隆基打断他的话头,上前携起齐瀚之手,说道:“罢了,不要再说这些感伤的言语。人言老来念旧,我今日见到故人,心里很高兴,我们要好好叙话一番。走吧,我们先去进膳,待膳后再来这里坐地饮茶赏月。齐瀚呀,你此次不要急着回去,在这里多陪我数日吧。”
他们入室坐定,齐瀚举盏祝酒,却见到李隆基面前没有酒盏,脸上有不解之色。高力士见状解释道:“陛下此次幸蜀至于巴西郡,群臣以为蜀中气候温瘴,因而数进酒,陛下不许,并宣旨今后再不饮酒。齐太守若饮酒请自便,就不用再劝陛下了。”
齐瀚知道李隆基酒量甚宏,嗜酒成性,不料入蜀之后竟然断酒,心中顿有感触,遂将酒盏放下,说道:“既然陛下不饮,臣如何能独饮?臣随陛下进膳便了。”
李隆基笑道:“蜀中气候确实温瘴,饮酒有利身体。我不愿饮,齐卿何必相随?你可随意呀。”
齐瀚闻言,顿改拘谨之状,举盏祝道:“如此,臣祝陛下身体康健,这就先饮一盏了。”此后齐瀚边吃边饮,共饮酒六盏,李隆基这日确实有异乡遇故人之感,其瞧着齐瀚畅怀饮食,心中甚觉惬意。
成都较之长安似水汽要多一些,虽一样为天上的明月,坐在成都地面赏月,似乎月轮要温润一些。李隆基与齐瀚膳罢,又携手来到竹溪旁,只听周围流水潺潺,虫鸣蛙声一片;再观水中的月轮随着流水而影影绰绰,与空中的明月群星相映,更添四周的静谧之感。
齐瀚酒量不大,饮了数盏酒后,话语不免多了一些。李隆基今日有了偶遇故人之感,少了一些昔日皇帝的威严,无形中又拉近了二人的距离,他们此时说话渐无拘束。
话题还是从齐瀚当初评价姚崇、宋璟时聊起,李隆基笑问道:“齐卿当初品评姚、宋二人,他们果然心服口服吗?”
齐瀚道:“臣实话实说,他们心中就是有些不满,终归无话可说。”
李隆基闻言,不禁哈哈大笑。
姚崇当时志得意满,某日向齐瀚问道,自己与贞观名相房玄龄和杜如晦是否能够相比,齐瀚断然答道:“不如。”姚崇之所以如此问,其实自诩与房、杜相若,闻言后不免沮丧无比。齐瀚此时又补充道:“然姚公不失为救时之相。”姚崇闻言大喜道:“虽救时之相,亦属不易啊!”后来宋璟又谦虚问道:“我不敢与房、杜相比,若与前任之相相比如何?”齐瀚率然答道:“不如。”自是说宋璟不如姚崇。
李隆基叹道:“不错,姚崇果然为救时之人。如今亨儿令房琯为帅兵至彭原,此人不足以破贼也。若姚崇在,贼不足灭也。”
李亨近来在灵武大集士马,又从回纥借兵,就东至彭原,令房琯为帅率兵东进。房琯向为文臣,没有带兵的才能,李隆基由此不看好他。后来房琯与叛军战于渭水便桥,结果大败,由此可见李隆基识人眼光未失。
李隆基现在怀念姚崇,可惜姚崇已逝去三十余年。李隆基现在忽然明白了姚崇当时让他三十年不求边功的深意,又叹道:“姚崇当年不求边功,我当时还以为他是基于国家需要恢复生机之因。现在看来,其还是大有深意,姚崇如此不轻易在边关开战,实想形成威慑之力,使四夷畏惧大唐之势不敢轻易启衅,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是也。如今安贼叛乱,朝廷不得已自西北等地调兵,吐蕃与南诏又趁乱掠地了。”
齐瀚见李隆基如此怀念姚崇,遂笑道:“陛下如此器重姚崇,为何匆匆将他换下相位,以宋璟代之呢?”
李隆基叹道:“是呀,现在想来,我当初失于匆促了。你品评宋璟不如姚崇,此评甚是,宋璟成为丞相,少了姚崇的赞襄之能,此后多以直言换其名耳。”
其实李隆基当时以宋璟代姚崇,是因为他看到姚崇为相数年后渐有结党之嫌,且其纵子贪赃,难为天下标杆作用,遂选有正直之名的宋璟代之。
齐瀚见李隆基现在贬宋璟而赞姚崇,心中不以为然,说道:“陛下,臣当时品评宋璟不如姚崇,主要是因吏才而论,今日看来,陛下用宋璟取代姚崇,其实长远对天下有益。若让臣今日再品评二人,姚崇实不如宋璟也。”
“呵呵,齐卿为何有了现在的思虑?”
“陛下于开元之初倡贞观故事,罢酷吏之风,姚崇虽有吏才,然己身不正,万难实现陛下之志,而宋璟吏才稍逊,却能开贞观之风。”
李隆基呷了一口茶,叹道:“想不到齐卿颠沛边鄙之地,还能凝思天下大计。好哇,我们今昔就开怀畅谈,好好叙说一番。”
齐瀚也微笑道:“若陛下不嫌臣说话絮叨,臣就信口开河了。其中若有妄言,还请陛下恕罪了。”
“嗯,你还是先说宋璟如何能倡贞观之风?”
“陛下,贞观之初曾经有过一场争论。那日太宗皇帝召集群臣和学士在弘文馆议事,封德彝等人倡言治乱世须用严法霸道,而房玄龄与魏征等人却建言用教化之策。两帮人争论不休,太宗皇帝最终决意以教化治天下。”
此为贞观时期很著名的故事,李隆基知悉甚细,便说道:“我之所以倡言依贞观故事,正是欲依教化之策治天下。”
“臣后来细思这场争论,愈加钦佩太宗皇帝的高瞻远瞩。秦代专用法律,汉代杂用霸道,到了董仲舒建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此后历代视儒家为治国大道,唯有太宗皇帝身体力行,所以出现了‘贞观之治’。陛下此后依教化之策治国,也就有了开元盛世。”
李隆基叹道:“什么开元盛世?如今山河破碎,却与盛世扯不上干系。”李隆基说话时语调黯然,可知心中有无比的悔恨。
齐瀚谈兴正浓,继续言道:“陛下,人心叵测,孔孟圣人察知了人心幽暗之处,因而有了仁心君子之说。其努力使人心向善,较之秦始皇与隋炀帝的严法苛政相比,可使国家政治清明、人心思善和谐,使君权长治久安。陛下当初倡言去除酷吏之风,行清明政治,宋璟为相实有标杆作用。臣之所以妄言宋璟优于姚崇,实缘于此也。”
李隆基在月影下摇摇头,说道:“我当初禁毁《罗织经》,不料到了天宝年间,‘吉网罗钳’又复盛行于世,唉,此事颇为自嘲啊!”此前的日子里,李隆基不知道天下有“吉网罗钳”的名号,此次入蜀途中方才得知。
齐瀚宽慰李隆基道:“李林甫为保相位,方有了‘吉网罗钳’,却与陛下无涉。酷吏之行向为去除异己之手段,李林甫为了翦除李适之、王忠嗣等人,不惜罗织大狱。陛下,法律为国家公器,若沦为权臣打击异己的手段,则国家实属危矣。”
李林甫迭施机谋罗织刑狱之事,将朝中许多大员相继拿下,若非李隆基认可,其事难成。李隆基现在不愿意承认这些事儿与自己有关,仅仅说了一句:“是子妒贤嫉能,举无比者。”
齐瀚是夕多饮了几杯酒,说话时就少了一些拘束,听到李隆基如此说话,就追问道:“陛下诚知李林甫如此,为何任之久耶?”
李林甫任宰相十九年,其算计张九龄后独专宰相位十六年。此前李隆基授宰相之期多为三年左右,李林甫任期之长实为异数。究其原因,李林甫为政时确实能掌控天下,且李隆基怠政放手,方有如此局面。李隆基现在见齐瀚如此来问,心中百感交集,不知从何说起,只好黯然以应。
齐瀚又道:“李林甫嫉贤妒能,确实无敌于天下。然天下凋敝如此,臣以为李林甫实为始作俑者。”
李隆基想不到齐瀚对李林甫如此看法,心中不以为然,说道:“李林甫虽有小过,毕竟能掌控天下,使朝政井井有条。齐卿如此说话,有些太过。”
“陛下,李林甫与前任宰相相比,其不同处何在呢?”
李隆基认真地想了一遍,说道:“不过任期稍长而已,并无太多不同。”
齐瀚摇摇头,说道:“此前相者如姚崇、宋璟、张说、韩休、张九龄等人,他们虽各有所短,然皆有相同之处,即他们胸怀圣人仁之理想,愿以己身之力为国劬劳。以张说为例,此人既有功劳,又逢迎陛下,倾轧同僚,然其终以圣人理想治世,如此就与李林甫有了根本区别。再观李林甫,理政时能条理众务,增修纲纪,大唐天下由其手而得到驾驭。然其常怀妒忌之心,打压同僚,不重科举,使天下后继无人;其行事皆以保位为要,使朝政看似有条不紊,实为庸政;他还上瞒陛下,下绝诤谏言路,使百官沦为‘立仗马’。李林甫心无圣人理想,整日盘算己身之利,看似他掌控天下大局,不过尸位素餐罢了。”
李隆基说道:“若论个性,张说与李林甫确实相似,齐卿为何还要推崇张说呢?”
“陛下,张说在众人眼中,其优劣之处可谓鲜明;而李林甫似无迹可寻,这样的人儿其实最为可恶。”
李隆基笑道:“我知道了,你之所以推崇张说等人,再贬李林甫,缘于你与张说他们皆为科举出身,由此鄙夷李林甫无文,不过党同伐异罢了。”
齐瀚摇头道:“臣刚才说了,臣等之所以与李林甫不同,在于臣等常怀圣人之心。只要常怀圣人之心,有文无文其实并无差别。譬如某人科举出身,然他抛却圣人理想,专爱如李林甫那样混迹宦途,这等人一样可恶。臣听说陈希烈累受皇恩,如今却投奔安禄山了吧!”
陈希烈未曾逃离长安,他端坐于家中,待叛军攻入京城后即率领一帮官吏向安禄山投降。李隆基后来得知此事,不禁感叹良久,此时切齿说道:“是呀,此人为左相时在李林甫、杨国忠面前唯唯诺诺,危难当头又降了贼人,真正是一个软骨头!齐卿,看来还是我识人不明,如此就看走了眼。”
齐瀚想起李隆基于开元年间时择相甚严,往往以三年为期另择新相,李隆基由此掌控国家大局,再令那些专任而不久任的丞相发挥所长,就将国家引领至富强的路上。孰料到了天宝年间,李隆基不肯再逞心力,让李林甫长期为相,就为帝国崩塌埋下了隐患,则皇帝的怠政实为主因。齐瀚这日说话已然直接凌厉,现在又想为尊者讳,不想直斥李隆基,就将话儿闷在肚中。
李隆基此时也许想到了自己的过错,遂叹道:“我昔为天子,任人不明,实为我之过错啊!齐卿,我将国家引入富强的路上,天宝年间的广运潭之会,天下珍货集于京师,则天下之富、庶民之康,实为有史以来的极盛之貌。我有此财富,将朝政之事交予臣子襄理,我持渐老之身享一些清福,难道不可吗?”
齐瀚道:“臣此前读魏征的《十渐疏》,起初觉得魏征确实有些吹毛求疵。太宗皇帝戎马取得天下,又励精图治,取得贞观之治,魏征为何对太宗皇帝接受了外藩的赠马和赠物横加指责呢?臣后来方才明白,天子之行昭于天下,其细微之行可以传递至百官乃至庶民,若奢侈风起,势必耗费巨大,由此用度加剧,而臣下为满足天子日益增加奢求,必想法增加赋税来搜刮百姓,由此荼毒天下。”
李隆基听出了齐瀚话中的深意,遂笑道:“齐卿这是在怪我啊!我在天宝年间重用王鉷、杨国忠二人,当时觉得这二人颇有吏治之能,听了齐卿一席话,方知他们能替我敛财,于是大称心意。唉,奢侈之风既害人又于国不利,天下人长期追求奢侈之乐,再不思习武应乱,结果叛军袭来,瞬间便土崩瓦解了。”
齐瀚觉得这日说话过于大胆,遂起身躬立道:“臣仅是思虑前事而已,万万不敢责怪陛下。”
李隆基令其坐下,说道:“你叙话前说过,今日若说错了话儿,不许我加罪。你刚才说的皆为至言,并未妄言啊。嗯,齐卿,我致力于国殷民富,然民富之后就忘了战乱之事,那些募来的兵丁毫无战斗力,往往遇敌即溃,实在不堪啊。”
“陛下,安禄山之所以叛乱,缘于陛下给予他的权力太大。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当初张说废除府兵制,李林甫继而全面实行募兵制,其实埋藏了安贼起乱的祸根;此后陛下大力任用番将,使边将势力日重,京师无制约之力,遂有此乱。府兵制虽笨拙,毕竟天下兵事集于朝廷之手,边将不敢有异心;如今天下皆行募兵之举,中原少有战事,就不堪为安贼对手了。”
李隆基听到此处,身子后躺仰望空中,双目直视月轮,似入定了一般,许久不再答话。齐瀚先是等待,继而怯怯地问道:“陛下,莫非臣又说错话儿了吗?”
李隆基长叹一声道:“你没有说错话儿。你的这番话又让我想起了九龄。唉,只悔当初未听九龄之言,使安贼终酿今日之乱啊!”
安禄山当初恃勇轻进招致大败,被张守珪解送京城,按例当斩。李隆基却觉得安禄山骁勇善战,可将之免职再回前线,容其戴罪立功。张九龄是时任中书令,数劝李隆基道:“禄山狼子野心,面有逆相,臣请因罪斩之,以绝后患。”李隆基坚决不许,安禄山因而保命。
其实张九龄当时不能预测到安禄山后来果然谋反,仅以安禄山的面相猜测而已,不料一语成谶!
李隆基起身时已是满脸泪痕,其啜泣着说道:“悔不用九龄之言啊!齐卿,两京终有克定之日,待返京之后,你代我前去韶郡曲江祭奠九龄,并持币恤其家人。”
齐瀚连声答应。
李隆基此时悔恨不已,忽然放声大哭道:“齐卿啊,今日我们共叙往事,让我深悔己过啊!我此前自诩开元之治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