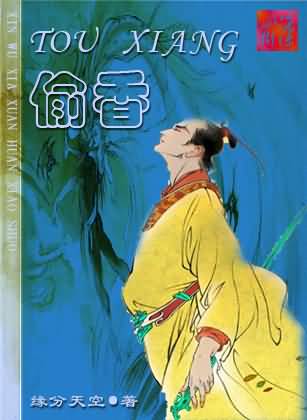�Ե���-��70����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Ժ�������Ц���߽����������ݴ��۶��ߵ�������Ȼ����������Ҫ�����ҳ��������֪��ҪΪ����ָ�����ۡ���
���ۣ��Դ�ǰ���ݴ��۶��ԣ������������Ѹ��Ĵ��ۣ��ֻ���ʲô���赲��Ϊ���Ͼ��ҽ�����
�����������ʲô���������������ң�����Ϊ�������������˵�Ѫ��������������Ѫ��
��Ȼ����ˣ���Ѫ�����ˣ�һ��Ҳ���Ի�����ô��
����
��ҹ���ݴ��۱��������ҵ�ʯ����ϡ�����ײ�������ϵ��������͵����ڹ��ϣ�����Ȼʹ�ѡ�
���������Ƶ�ʹ�༱����ȴ�ò���һ˿ů�⡣ʧѪ���������������ֱ�����������������������������鴤һ�¶���������
�����ԡ�������ѡ�������Ѫ��������������ȴ�ƺ��ŵ�һ���������ֵİٺϻ��㡣������ȥѰ��������������Ӱ�ӣ���Χ���Ǻ���һ�㡢����������ӵĻ���������
��Ȼ�䡢���۽�����һ���ᣬ��Ϊ��ʹ����Ϊ������ֻΪ��Ҳ���మ��һ��
����
����������ҹ���ܿ�㵽�˵����գ��ݴ�������ֱ�����Լ������尾�������յ����С�������ʯ����ϣ���ĬĬ�ؽ�����Ц�ջ�����һ������������ƽ������������һ�����Σ����ڡ����ܼ��������ˡ�
���������Ѿ�Ѱ����硢���������ˡ���Ӧ�������£����Ѿ��쵽�ˡ�
������ǰ��ǹҸ�磬��Ȼ���һ�а��ã�����Ӧ�ò������ѹ���Ҳ�����ٹ����ˡ�
����֪Ϊ�Σ���һ��ʼ��û������������ȥ���С��������Ϊ���Լ��ֲ���ʱ�����������뵽�������Ժ�Ҳ���������������С��������ӹ����ճ���֮��ʹ�ˡ�
����һ�����������������Լ����弫�̡�ѪҺȴ�ּ�����ʯ����е������������ͨ����һ��һ�εش̽����Ĺ�����
���ķξ��䡢ֹ��ס���ȣ���������������ʬ���⡢���ܿ��ƣ������ȳ���̵��ֻ�Ǽ����ķ�֮Ѫ����ӿ�ϡ��������������
ǿ���ſ�ʹ���˼���֮�գ����Ŵ������ƺ��������˵ĽŲ�����������ͷ��ʲôҲ��������
�������ݴ��۱������������űߣ������ڵ��ϡ�
����ȡ�乳���������Ѫ�⡢������ǰ���������һ��һ�����������һͷ�����������еIJ��ޣ����������ʸ�û�У�ֻ�Ǵ������ﲻ�Ϸ����������ĵ��ƺ���
��������ȫ���γ����������������ֵ���Щ���ơ�������������ſ�ڵ������Σ���Ȼ����һ����������������һ�䣬���ݴ��ۡ�����
������һ���������ز��ͷ���ڳ�֮ǰ���ŵľ���������ϡ�������ɫ���࣬ѹ���������������������ǰ����ū���ͻϮ�Ծ������ȹ���Į��������Ҫ�������������Ч���ھ��С�նɱ������������ū������Į������
�ݴ����������ɣ�̫����û��˵��һ��һ�ʡ���ʱ������������˵����������
�����η����ڣ��������������顢����������ϡ���������Ҫ˽���ﳼ����
����������ĬĬ�ش�����Ѫ�����ƿ�����Į�����������ݣ��Ƿ�����
����ॡ�һ�����죬�������ڳ���ǰ������һ�����ɱ������ڵ��ϣ��ݺ�����һ�䣬
�����Ȼһ����������ȥΪ����ս����ɳ���ϰգ���
����
һ�Ժ����������ݴ����ķ���ȴ������һ���ƻ�����⣬�����д���һ�������
�����������սʿһ������ɳ���ϣ�ȷʵ�������ܸ��������ʴȵľ�����
�����ﳤ��Զ��������������м�����û�����������Ļ��������Ծ����ٸ�ս����
�����������ٿ���������һֻ���յ�ӥ��������һ�㱻��������ǿ���ٱ���
���ο�����ǰ������ֻ��Ҫ��Ī���سǡ�Īɱ���ˣ�������ȥĮ����ս�����������ض�����ͬ�ĵ�����ū�������㲻��Υ�˸���������Ը��Ҳ�������游������֮�飬�������ٴ����Ծ������ս����������
û�뵽�Լ�ǧ����������߾�Ȼ��������˫ȫ�ij�·�����Ĵ�������һĨЦ��˫�۳����Ŷ�ס��ǰ�DZ�������
��������ǰ�������Ǹ�����δ��������꣬��ʱ����һ����ս����������������ɱ�������������ɱ�У���������������һ�θ�ս���Ļ��ᣬ���ǵ����ͽ�����Ŭ������֣���ץס�ǽ�������Ȼ���̫Զ��
������ȫ����ʣ��������ǣ�Ž����Ѿõ�����һ��һ�������DZ�����ȥ�������������Ƶ��˿��ڵ����ϳ�������Ѫ�ۡ�
������������һ˲�䣬������һ����ס�����յ�һ������ϣ����
��������ϣ�������ƺ����ŵ�һ˿�����İٺϻ��㣬��������ͷȥѰ��ȴ����û������Ӱ�ӣ�����̫��˼������Գ���á�
�101����ɳ��
�þ���ҽ�����Ρ��ݴ��۵����ƽ������ͣ�Ҳһ���ָ���һЩ������ֻ����������Щ���ӣ���ʪ�缲�����������ϵ�ʱ��̫�ã�����˫ϥ����ʹ�����ޡ�
�������������������ϡ�����������˫�Ȳ�����·��Ҳ����ֻҪ˫�ֻ��ܾٽ��ֶܣ����ͻ���������սʿ��
����
�ܿ������ʦ�����䣻�����˾���Χ�ڼ���IJݳ��ϣ����ƺƴ�Ϊ���µ��ӵ��ǹľ�������
�ݴ����Դ���֮���������ְ֮��Ҳ��������ʿһ���ѪΪ�ˡ�����Ϊ�ġ�����ҫ�����죻����ױ�����ɷɷ��������Į��ս����ȥ��
����ū��ս��������ݴ���ÿս����ǰ���������ɱ����ǰ�ص�Ѫ������ʬ�������������ֱ��ÿ�춼�������������һ�ۡ�
��η����֮�£���������֧��ȴ��������ԽսԽ��ħ��
��ū�˾�������ھ������������������ﵱ����ս���ϵĻ���ħ����������������������Ҳ����Ϊ��������ֻ����ͻ��Ϯ�����ѷ�����
������һ�ӵ��Ծ���������н�٣������Ͼ��Ǵ���֮�������һ���ͨ�еĴ������ֻ������������Ҫ����������������˽��
���������̽��Ϣ������й���飬ͬ��ʿ��ҹ�ﲻ��������ЪϢ�����Ӫ��Ӫ����������ÿһ��ҹ�ͽ�����������������߶���
��ʼ�ղ��Բ������˳�ܣ�ֻ���Լ��Ǹ��������ư͡�
�����ճ�Ϊ��������Ϊ������ʱʱ�̶̿�ֻ����ս��˩��һ�𡣶�Į����ҹ�ĺ����Х�絶����ҹ�����������ߣ��ü��μ������������Һ����������������������ߣ�Ϊ���ڵ�һЩ������
ֱ��һ�����ٵж�Ŀ�ս�������������˺���ĵ��ˣ����ٰ����������������ϣ������Ϳ̽����˿ڣ�Ѫ˳�����������ʪ�������������
��������ָ��ָ���ף���֪��ʿ���ɷ�������ȥ���Ľ��ϡ���ʱ����������������ȵ�����������Dz��̣�������������һϢ���㲻����������������Ӫ�ʡ�����Ъ��һ�ǡ�
û�뵽��һ������֮�������ǻ��������������Լ������ò���˼�顣
�ݴ��۱㵱���������������Ÿ��п��ս��Ҫ��ȥ����
�˺��ֽ�����������ս�ۣ�ͬ��ս�����������������Ǻ�����ϧ�Լ���ֻ��ʤս�����������������Σ�������ʼ�Ѻõس��������䣢��
��һ�գ����˴�ʹ��������ЩѪ������˺�˵��²��ݲݰ�����һ�£����̲�ס���𡢴�ǰ����������Ҳ����˺��ȹ������ϸ�ع�������ϥ���ϡ�
˼���糱��һ���߶������ʱ�����̰ӡ������������ơ���͵͵ȥ��Ҳ�Ĵ��������һҹ����Ҳ���ڳ���ʱ������æ���ϣ�ֻΪ����������һ����
�������ձٵ���Ϣ������˵�����ã���
��Ҳһ㶣������ϲ������ӵ�ģ�����������������ˡ�
������������Ҳһ����ɣ���ԥ�ش���������ӡ����ң��Ҳ�δ�յ����ֵ����š���
�ݴ�������ʧ�䣬���ɱ�������������ס��Ҳ������֡�
����Ȼ̧�ۣ������ع�����������дһ���Ÿ���磬������������Ҳ���ʡ�����һ�пɺã�
��һת����Ը�뻹�����˰ա�
�α�ȥ������ǵ����˭����˭���������ף�Ҳ��ν�ø�絣���������
���ο�����ע��Ҫս��Į��������ɳ������ʱ�������κ����ţ�ֻ�������˽���ͽ���˸С�
��ҡҡ�������Ӫ�������������������ߣ�����������ദ��һĻһĻ�������������С�������죬�����Ũ��ʱ�֡�
���������У����ӪӪ�����˼���ʿ����������Ѱ����ԭ��Į�������ȶ�����ū���ˣ���˧Ҫ�غ�����ְ��˵���������Ҫ�����������֮������غ������Թ����ض����
Ӫ���Դ�Ǹ�����ʿ���������°��𡢽���ȥ��˧���С��������������£�δ��һ˿����
����
�䱻Ѻ�غ�������������������������Ϊ�ֻᱻ��ȥ���ȴ��������ֻ�ǽ����������ݸ���
�ݴ���������Ϥ��������ε�ǣ��һЦ�������������������ࡢ��ȴ���ǷѾ��Ļ�Ҫ˽������������߹���һ·������������
�Ǽ����У�������ܿ�������Ӱ�ĵط���������ȥ��ɽ������ȥ��ͤ������ȥ����¥��������ȥ�����᷿��ֻ��ÿ�ս��Լ�����ƫ���
ֱ����һҹ��ҹ�λأ����������Σ�������ǣ����ҡҡ�λε������˽����᷿���ƿ��ţ����������ż��Ͻ���һ������ˮ����
�����߹�ȥ����������齱ߣ�����������һ�����ڱ�������������һ�㿩����Ц�����ֹ�����
�������̧��ͷ������ȴ�����������¹��ϡ����IJ�ȹһ��һ�������ع��ţ�ÿһ�����ؾ�����������ÿһ�����ơ�ÿһ�����졢����ͬ�ϸ��ͼ������ӡ�������Ժ��
���߽����������ָ�����Щ��ȹ������ɢ��һ������������������ʧ�䡢�ݺύ������������ġ�
������Ȼ�е�һ˿������ȴ��˵�����������������ѡ�������������ʯʱ���������ģ���ô�����������
����ָ�ң�һ��һ���ù�������ȹ���ƺ���Ҫ��������ʹ�ȴֻ�Ǹ������ɡ�
��Ȼ��������һ�����죬��һ������������ȹ����������ݴ�����æʰ����һ��˿����ϸ������ϸ�����¡�������˿���������ӳĿ�ġ�ȴ������������������ת����������֧��¹�ѡ�
��������������һ�ֲ���ĸо�������С��֪���¹�ѳ��Դ������ң����������������������������һʿ���Ե�ִ�ⶥײ�����������������ȱм���ʱ������һ����Ҫ���������ȫ���������ô���������ع���ȴ��������ھ����У���
���������䣬�ƺ�����Į���ķ�ѩ�и�������ǡ�������������ѣ�����ֻ��һ����ͷ��Ҫȥ�ع��ҵ���硢�������������������к�Ȼ����������ʯ������ء�
����˼Ʈ����ȫȻ�����Լ��DZ������ڸ��У�ֻ���Թ��Եس忪���ű�Ҫ���ⱼȥ��Ȧ�ش��ŵ�С����æ�������ȡ�һ�����ơ�ȫ���˱㽫������Χ�����С�
�ݴ��۵���ʶ��ȫֻ���ع��������������ϣ���Χһ��ȫ��ֻ������������͡�����ͷ��ֻ��һ�ɾ�����ͻ����Χ��
�����ϱ������ѱ����ߣ������ֿ�ȭ�뼸ʮ����ì������һ����ūս�����ܵĵ�����Ȼ���ѣ���ѪȾ���˺��
��˫�۷���Ѫ˿�����ǹ��ģ���ʶ�������л�㱣������ҳ�ȥ����Ҫȥ�ع�����ҪȥѰ������
�����ͱ���������й¶�����������������ʿ�������ع���������ۣ���Ȧ����Χ������ͷ��С�����������������е������������ӽ����������֣��������ܵ�˲�䣬�͵��չ����ʡ������������ϣ�����������һ����Ŀ���ʱ��ɢ���������ڵ���
����
�����������ѱ���Ѻ���������ȫ�������á������ϵ������Ծ����ˏh�h��˺����������
��Ų��Ų���壬������ָ����������������
���ڣ���һ������������Ѳ���ݴ���һ�ٿ������Ҽ�����Ҳ�����Ҽ���������ֻ������������һ���¡���
���˽���æ�������䲢����������ת��������ʧ��ʯ�űߡ�
�������ң��������ʣ�ÿһ��ÿһ�̶��Ǽ尾��
�����˵ڶ�����䣬���ź�Ȼ����Ҳ��ű�һǰһ�����µ��Σ�ü����dz�š�����˲�����ֻ�Ǿ�Ĭ�ع����ݴ�����ǰ����
�ݴ�����æŬ���ع���������ǣ����������Ҳ������һЩ���Ȳ��������ʣ�
����Ҳ�������Ժ��ձ�һ������͵��ع��ĶԲ��ԣ������ۿ��������˷������Dz��ǣ���
��Ҳ��ɫ���Ӱ�����˫ü������ȴһ����Ҳ˵��������
����Ҳ����������һ�����ǿ���֮�⣬��ֻ����һ������'�֣�����û�лش��ݴ�����ʱ������
�ű�����Ҳ�����˿ڣ����Ǻ����Ĵ����
�����ӡ�����ʱ�������ӱ�����������ʹ�IJ��ѣ�����Ҳ��ȹ��ӣ������ڹ���һ�����ֻ��������⣬����˿������ת御�������Щ��ҡ����ӳɵľɲ��ϳ�����������ֱ������������������裬��ظ��ǽ�����ͨ�еĴ��ﲻ�����֡��������������ء���ʵ���Dz����ѣ����Բ��뵽������
�ű��Ļ����ں�����˵����ȥ��
�ݴ��ۻ�������������ȥ�����κο��ܡ�
�102�����м
�ű������˿�����һ��ȭ�ּ�������
�����Բ��뵽���ѳ���С����ؼ����ݺ����г������ʹ������һ����������Ϊ��Ұ������֪���ӶԳ������������������Ϊ����ȥ��˧һְ��ֻΪ����ɽˮ֮�䡭�����ϰٹٶ��������Ѻ����˹��ӣ�����ڿ�þ�������桭�����Ϻܾ���ǰ���������������֤�ݡ�����ָ������ȷ���ع���������ԡ�
���������ϲŵ���ƽϢ��Ұ����ͣ�ڳ����Թ��Ӳ�δ�������顢ʵ�˱�Ů�����֮�ɣ�Ϊ���ӿ��������Ҳ�������˹���ֻ���º�֪������Ϊ��ά���İ�֮�ˡ���Ը�������Ϊ�������������Բ���ǿͬ�������ϻ������̡������������������ū������
�ݴ���ֻ����ǰ��Ӱ����Ӱ������ҡ�Σ��ص����壬����������ű����ֻ�ܼ���˫����ϡ�������û����������˳��أ�ȴ����Ʈ�ѿأ����Ƽ���ʧ��֧�š���һ�����ģ���Ҳ������ס���͵�ˤ��б���ڵ��ϡ�
�ű���������Ȼ��ֹ��������˵ʲô���ݴ���������������������ŭ����
������Ͳ������ع����������й���ܣ����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