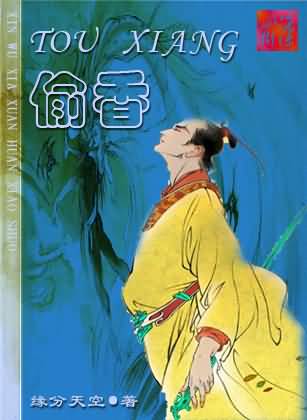�Ե���-��61����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ɫ�Ұף�һ�Բ����ؼ����븮����ȥ�Ǹ�ɽ�������������붴�������ѣ���������ȥ��ȴֻ��һ�ſ�ʯ������ȫû������Ӱ�١�
�ݴ�������һƬ�հף�˼�����ң�ȫȻ��֪��������롣
�ű�������˵�������ӣ������㲻��������ƭ�㡢ֻ���������ˡ���������ѵ������˽�ҩ�����Բ��з���ʩչ�Ṧ����������©���ʱ��ӳ���ȥ����
��ô˵���Ѿ����˽�ҩ�ˣ������ϵĶ���ʱ�ý��ˣ��ݴ����������˿��������٣������ڻ��ǰ�ȫ�ġ�
�������ŽŲ���Ӧ���뿪�ɣ���Ȼ�����ڶ��С���ȥ�����ġ���û���ɵġ����������㷲�����
��ת���������ܣ�����Ŀ�ĵش�������Ȼ������һ����������齵�֧���ϡ���������ǰ������ϸ��������ɫ���ѷ��֣�������ȫ�Ƿ�ɵ�Ѫ����
�������ֿ־�ľ�ѹ�����������ܼ�������Ȼ������������ס������ֱ��������Ȼ���ⶴ������е��ٴ�������Ѱ��ȴʲôӰ�Ӷ���������
�����ӣ�����Ҳ��������Ź֣����ŵ���������
���������ⶴ��������ˡ����ݴ�����һͷҰ�ް�̵ֻص�ૣ�Ŀ�⼱���ڶ���ɨ�ӡ�Ϊ��ֻ�����һ����Ѫ������������ʲô������ͷ��ȥ��������ʪ����������ˮ���������ϵ�Ѫ������ʯ��ĵ�ˮ�ܵ��ˣ�
��һ�Ѷ����Ҳ���л�ѣ���ʯ���б���Ѱ�ң��ܻ���һ��ۼ����ܻ��еġ����ڶ����ܹ��Ǹ��ප����ʱ����Ȼͣ��ת����ֻ������û��Ѱ�����ѵ���
��һ����������ප���ű����˶����ù������з�ħ���������ô������Ե�ʵ�����Ǹ������У�����Ϊ������
������Ҳ�����Լ�̫����ħ�ˣ���පԽ��Խխ����ʯ���裬�������У��������ֽŲ��ã������������������ȥ������ô��������������Լ�����̫�ң������˷��磿
���������ɶ�����Ҫ��������֫ȴ������ǰ������
��֪��������ã����������������������ʣ���»��ε��������ǻ�����������һ�𣬸�����һ�е���ǰ��ȥ��
�����ප��ͷ����������˶���ʯ�ڣ�Ҳ�ռ�һ��Ѫ��������Ӱ��������һ���ʯ�£�û����־�ؾ��Σ�û��������������һ�����¾���Ⱦ�죬����ʯ����������Ѫ���ʡ���������أ��ץ��ʯ����������һ������������֮�ݣ�ʹ������ɭɭ�ؿ������С�
һ�۴��ģ������ֽ����飬�����类��������������ǣ��������֮����Ų�������塣
�����Ƕ�ʹ�����������Ż�������ô����ô�ڵ�ʯ���ף�Ѱ������һ��ӻ��������һ���п���
����������������·����������ʯ���¾��ܿ��ʱ����ȴ�ڸ��в�̽����������������
�������������˵������ߡ�����������ģ���������������ϵ���Ϣ��������������Ϥ�����������������ֱ�ϲ���������
��˫�ֲ����Ž���Ѫ�˶��������У�ȴ�����������������ѵ�������
�89˺���ѷ�
�������������۶�ʱ�������¡�������ȥ�룻ȴ��ֹ��ס���룬�⼸��������ʼ������һ���˹���������������ޱߵ���������У��ڰٳ�ʯ�£����Ŷ���һ��һ����ҧ����������Ψһ�ܽ赽һ�������ģ�ֻ��һ�������������������գ���������������������Ϣ���ںڰ�����ʯ��Ѩ�ﻯ��һ̲ŧѪ��������֪��
������ˮ���䡢���������ϣ�˲�������˿ڣ�ɳʹ֮�������۶۵������˼������ַ���һ����ʶ��
�������ۣ����ڳ�Ѫ��������������������һ�����ϳ�����������
���о���������Ȼ����������һ�£��Խ���Ƭ�̣������̵�Ʋ����ȥ��
���������������ݴ���ֻ�����п���ľ������˵����������
�����С���ʹ���������ƺ������ӿ�����������ɰٶΣ����Ѷ�������֪���Լ���ʱ��һֻ���϶����硣
�־�Ͳ̶ֻ����ܴ������롣�����������ģ�˵��
���ܲ��ܡ�����
��������ɳ���ѱ棬���Լ��������������ȳ�һЩ����Ѫĭ��������˵��
���ܲ��ܡ������ҡ�����
һ��ʹ������������������ü������������������ž���죬������һ˿�������²���һ���֡�
����Ҫʲô����Ҫʲô������ȫ��ȥѰ����������ֻ����ʹ����һ��һ��������������ϡ�
���������ƺ���Ʈ���˼��֣��鴤��ֹ����Ϣ������
���������ۣ�Ŀ���У����ְ�������ʹ��������ȴ�ǣ�
�������ܲ��ܡ�����һ��ʹ�죿��
�������纮ʯ���������·�һ����ˮ���ż����������ļ䡣����һ��֮�����ӵغ�������һ����ʱ�����գ����ܸ����ģ��ѵ�ֻ�С�
����������������ʵء�������������彣����¶�������������������ܾ���ĥ��������������һ�����ѣ�������ɱ����������ô���õ���
��̧�ۿ��˿���������ģ���������������ݡ�
���ڵȣ�ȴ�Ȳ������ش��������ر����ۣ���Ц��˵��
���ǡ�����ɲ����ԡ���������֪�����ⶾ��������Ҫ�ö�ã��Ҳ���������
���ۻ���һ�������������У���������Ϊ�������Ǹ������¶����ˡ���������Ϊ������ǣ�ȴԭ�����Լ�ֻ�������������¿־�������������������У��Լ���һ�����������ڵصĶ�ħ�����кβ�ͬ��
��˼�����ڣ������ʶ������ʧ�˼��䣬���ǵ��Լ�����ʿӪ�еľ���������������֮ǰ���������������ڴˣ������������Ƿ������ع����䣬���������µ�ʳ����������˷�����ɽ���С�һ����������������Ȼ�����Ѹ�������������Ҫ������֮������������
����Ȼ���ף�����������ˣ�����ʹҲ���ϳ�������������������ȣ���Ϊ����Ϊ������Ҫɱ���������㺰�����ˣ�Ҳ���������ø���Щ��
�����������������������ҵIJප����������һ��ϣ�����ⰵ�������ͨ������������������̫�ң��ڰ�̫�����ǰ·δ��ת�������Ǿ�����
���������µĶ�������������������ͷ������һ��������ڡ�����һ���ڷ����뵽����ʱ��˵��Щ����ʲô���塣
�����������ȴ�ӹ�һ���⣬�ɻ��˵���������㡭����
������������ǰ���ع���ʿӪΪ�˱�������ʿ���������������⡮����֮������ʧ��ǰ����Ϊ���������������û�н��ҳ������ٵ��ľ��鴫�����ˣ�����������ɱ����ò����������Ľ�ҩ������һֱ��������㣬ȴ��֪�����Ǹ�������Σ����Խ��Խ����ˣ������������Լ�����
��ֱ��������������������������ͷ˵�����·�һ�����硢�������ڵİ��������յ�ͨ������Ȼ��ҫ������������ڡ�
���֮�У���ˮ�����������Ѫˮ����һ��˳�������������һ�ε����¡�
����ȻЦ��Ц����������ȴ����Ȼ����������ɬ�ƣ����ȴ�������յļ������ģ�
�������Ҿ�֪������û����ô���ҡ����㡭����Ҫ������Ҳ���ᡭ����������ô�ݵĶ�����
������Ц�⣬����ʳ���Ѫ������ȴǣ��һ�����㡣����ѹ�ֵ�ֱ�����쳤Х�������������������������ԣ�
������ô���ܺ��㣿�Ұ��㣬����Ͱ�����ǡ���ֻ�����Լ�������
�������������ſڣ�˵�����������ϴ���dzЦ������ȴ�������ء�
�ݴ��ۻ�Ȼ���ѣ���ʣʱ�䲻�࣬��Ҫץ������С���������������£�����䣬ϥ��ʹ���������Ỻ��վ������������һ���ᱧ����Ȼ˺�������϶Ϲǣ���ʹ��������ະһ�������������ᡢ����������һ�۵������������ɣ�
����������һ��ȥ��ʿӪ���������������ǻ�����һ���������������Ѱһ����ҩ����
�����û������ҡͷ���ٴ���Ŭ�������ۣ���˵��
����Ҫȥ����Σ�ա�����
�����ղ������������������Ƕ���ǰ����ɱ��ô����������Ը����
������һ����У���������˳�Ų��Ƶ��۽��������������ᣬ
����Ҫȥ�������Ѿ�������
ʹ����˿˿���ߣ�������ÿһ�����ǣ�Ҳ������������ʶ�������ޣ����������һ������˵��
����ֵ���ˡ�����
������������ȥ��ʱ�����е��������Ĵ����������ߡ��ű���ˮ������������
��ֵ��ֵ�����������������������Ҷ�����һ�𡣡�
����
�ݴ��ۼ�����һ·������ֱ���ع���ȥ���е��������������еÿ�����̫�������������Ҳ���ܲ���������������ÿһ���ӵò�����
�������һ���ޱߵĻһƣ�ӳ����ɫҲ����������
��ؽ���֮������Լ��һ������������������������˰��°�멣����Ƿ��ɣ�������磬ȴ�������������Ρ�
��������һ���������ձޣ�����ȫû���뵽���ڴ�ʱ�˵ء���������
�����������е�����ǰ������һ�����������
����������������
����磿��
������ɫ�����������в��ݣ�����û���κα��飬����ֱֱ�ش�������һ�飬�������Ծ��̤���������������ֱ�ȥ����������һ����£�����ʶ����ȥ�������֣������������罣��ؽؽһɨ�����۱�����ֽž㽩��
�����ƿ�������Ȼ����Ԥ�ϣ������ۼ�����ȫ������ŧ��Ѫ��Ť�����ǣ��������������㸲��ݱ�����ġ���������ҡ�Σ�һ����ס�������䣬������ס�Լ���
���������������ꡣ�������Ȼ�������������ȴ��ִ�ؽ�������ʱ������˵�����Ụ�����á�����һ�겻�������ľ���������ʱ���Ӳ�����
����Ҫ����ȥ�Ķ���������������ɳ�Ƶ��ʡ�
���ҡ������ݴ��ۼ������ƺ�����֪�����ж�������ϸ˵�������������������ȥ�ع�����������һ����ҩ������
����ô�ٲŷ������ж�ô����ô�ٲ��뵽ҪѰ��ҩô������
����ŭ��ȼ����Ҳ���Ʋ�ס���������������˦ȥ���ݴ��������Σ�һ�����ҷ���
����һ��Ѫӡ���ɴ��۲����佥��������죬��������Щ��ϧ���۵�ʹ��������
��̾�˿�������������С������úܺã��Լ��γ����Ƕ���δ�죬�����ܾ��ִ��ۡ�
����������������Щ������˵�������̴������㸮�ϡ���
���۾����̧�ۿ��������۲��⡣
����һ��һ�ٵ����������н�ҩ��
����
ת���ݸ������۽������Լ��Է���С��������ϣ����������ŷ��¡�
���´ӻ����ó���ֻСƿ���ο�ƿ����һ����Ǻ֮ζɢ�뷿�С���ȡ��һ�룬������һƿ�����������С�
�ݴ����䲻��ҩ����������Һ֭Ũ����ī���������죬����һ�ɴ̱ǵ�ζ����������Ǿ綾������ʱ��һ����������ǰ������ס���µ���
���ⲻ�ǽ�ҩ��������Ƕ�ҩ������
������ɫƽ��������ָ�������۵��֣�ָ�����ж���˵�������Ǻ��죬������ָ����һƿ���������Ƕϳ��ݡ���
����Цһ��˵�������Ǿ��ݵĶ��������Զ������İ취����
ԭ����������Ҫ���Զ����Ծ�����Ϊ�˾�����������̫��Ϊ�������������ġ���̫���������Ը������������������Ϊ���ǵ�����������ǿ���ع������ľ�������̫���������Դ˸�����ʹ����ʧ�أ������ʼ���ռܿ�����Ȩ��������Щ��������������Ϊ���ػ�����̫����������ģ������ǹ�����˽��Ѭ�ģ������ڹ�����Խ��ԽԶ����������ʧ�����������������˷���֮�ǣ��϶���������������ʿ֮������������ʼ�������ʶ��������Ĵ����������������������Ƚ��Ĵ��س������ݻ��ҡ�
���¶ĵľ�����̫�����ݻ��ɡ������빫���ж������Ĺ��⣬ֻ���������������ڵй����������гл�ϥ�£���̫����Ȼ�Թ����и������Ρ�����������Խ���������Ŀ��ƣ���������������˳���������еijӸ˻������ĸ����ӣ��ಢ���Ѳ¡�
�����������һĻ���������ؾܾ�һ��һ��֮ҩ������������ԥ�����¾綾����ȫȻ����̫�����ţ����������ء�һ��Ϊ������ʹ��ҲҪ�����������¡���
����̧�ֽ��ϻ���൹�����У��������ܣ��Ձ����������˷���
�����п�Ц�����ƶ�֮�˵���ͨ�����ģ�������ϳ��ݽ�������綾����˭���������ԣ�����Ҫ˵��������������������������ҩ���������õ��Ļ�����ʿ���ֵ��ˡ�
�������ߵ�齱ߣ���֮�����ؽ�С�������£�����С���Ǵ������۶������������۽����絶���С�������û��֪����
�ݴ��۽���ԭ�أ������¶������Ҫ����֭����ι�£�ɲ�Ǽ仹��ʧ��һ����
����Ҫ�������顭���IJ��𡭡�
����Ŀ����£���ĬƬ�̵���
�����Ѿ��Թ��ˡ���
����硭����������ȫ��������˲��ʧ�
��羿��Ϊ������Щʲô���ѵ����������Լ�������ȥ�Ծ�����������Բ���������ȥ����������������ϳ��ݣ�
�������ŷ����˿������졢�����ƹ�����ĺ��С���û����ʶ�������廹�DZ��ܵ����˷�Ӧ�������������С��������գ����Ӻ���������¡¡�ط��������ƺ����ƺ���������Ҫ�ܿ����룬�����½���Ȧ�����������壬��ס�������������ѡ������ְ�ѹ�������Ѩλ����ֻ�ܼ���һ��һ�ڽ���ȫ�����¡�
һ�뾡������˫��ͨ�캬�ᡣ��̫��������е�ʹ�࣬�Լ��������ٴλ��룬ȴҪ�������ؿ���С���������ǰ��ͬ������ĥ��
��Ȼ��������Ҿ��Σ����촽��������ϣ������Ŀ���ȴ����硢���طΡ��������𣬼尾ȫ�������ѵ�Ƥ������˿˿��Ѫ���������̺��ס�����û�������ٿ�������ʹ�������һ���ֽ�����ͷ�����Լ�ǰ�ء�
�����������ز�����ͷ��ײ�����Ŀڣ���ʱ̱����Ƭ�̣���Ȼ�����ҽУ�˺���ѷΣ�DZ��ʶ����ҧ��������һ����ȴ����ҧס�˷��������µ�Ƥ����ʹ�����൹��һ��������
��Ѫ�ӷ��¼���ʳ�������С����Ŀ��С�������δ��ˮ������ʱ��˿˿������˹��ů����������̰������ʸ��˱�������з�����ʹ��֡�
����ͻȻ���˿ڣ��ƺ�������������Ѫ��ת��Ť����������࣬����ҧס����
����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