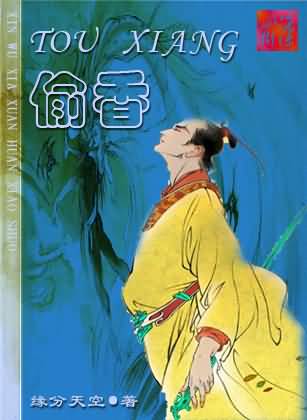迷谍香-第5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虞从舟只觉这房间四周皆起了电闪雷鸣,被她雷得险些翻下床去。他紧着鼻子嗅了嗅,好像闻到点儿外焦里嫩的糊味。
他一把将她抛在床上,站起身理了理衣裳,斜睨着她说,“既是如此,你肉身在这儿,我就更要牢牢抓着你。说不定她什么时候又穿回来了!”
他面上装得严肃,余光中、看见她对他做了个怪脸,吐了吐舌头。他心忖、这个小妖精真真是让他的心绪一刻不得闲
……
结了账,楚姜窈问道,“我们接下来去哪儿?”
“还是去塞外。”虞从舟答道,“一追不成,那些人定然以为我们是惊弓之鸟、不敢再走原定路线。但我们偏偏还是去塞外,出其意外。”
窈儿乐呵呵地点点头。虞从舟瞥了她一眼,好奇道,“那些人追杀的可是你。你不怕?”
“反正你不想杀我,我就跟着你。况且,”窈儿得意地甩着小眼神,“你昨晚还说,说你爱我。”她咯咯地笑声缭绕在他耳边,痒得很。
从舟翻了翻双眼,未成年的小孩子果然百般无忌,直爽得很,连装一下娇羞都懒得。
☆、氤氲良宵
见她笑得挑衅;虞从舟探了身体挡在她面前、挑着嘴角冷笑说,“我愈发觉得你早上说的有道理。我爱的、想必是从前附身在你身上的那个小公主。你不过是她的肉身罢了。”
她可怜兮兮地眨了眨眼睛,落下好几步外、跟在他身后。从舟暗笑了一小会儿,还是不放心她离自己那么远,回过身去又拉紧她的手。
两人寻了马匹,一路向塞外行去。午后翻过一座山丘;眼前竟豁然开朗,是一片极为开阔的山谷。远处重峦叠嶂;映在透蓝色的天边。
而碧青谷中,云波涤过;仿佛仙人行车,腾在空中。
楚姜窈欢喜地呼喊了一声,纵马向山谷中奔去。绿谷中;漫山遍野都是鲜花,姹紫嫣红,在艳阳下娇腻地绽放。她甩了马缰,跳下马去,在山坡上侧滚了几圈,快意地笑着躺在花丛中。
从舟拴了马,不知奔去何处。再回来时,他两手各拿着一束紫色的花。
他走到她身边,脸色微微染红。楚姜窈看见那花儿,呼哧坐起身来,仰着脸说,
“真好看!”
“我… 摘了两束迷迭香…”虞从舟囧得实在不知该说什么,一抬右手,把那花递到她面前,“这束花、送给你。”
“谢谢从舟哥哥。”她开心地接过,凑在鼻尖嗅了嗅,一抬头、乌黑的眼珠又盯着他左手那束,
“那,那束花难道是… ”
从舟低头一看,着急道,“这束花也是送给你的!”
楚姜窈嘤嘤一笑,握住花儿、踏着轻功,在谷中悠旋了几圈,惊起几只橘色的蝴蝶。她快乐地对着蝴蝶轻轻吹气,将它们吹到更高的空中,像点点落进天空的雨。
她从身后抱住虞从舟说,“满山都是各种鲜花,从舟哥哥怎么知道我最喜欢迷迭香?”
“我… 我猜的。”从舟正正其词。他觉得这也算得真话,虽然多年前,在悬崖下,她曾泄露谜底。
“我们真是心有灵犀!”她小嘴咬了一口小花瓣,甜甜的,另有一种舒神的香气。
“那,你最喜欢什么花?”她在他身后问道。
他侧过身低看着她,目光忽然深邃起来,“你不知道么?”
她摇头晃脑好一会儿,还是说,“对不起,我一点也想不起来了。”
“不怪你,是我从没告诉你。我最爱百合花,虽然没有见过,但百合香和窈儿身上的香气一样,那花定然是最美的。”
窈儿吐吐舌头,喷出两瓣花瓣说,“好酸好酸吖!”忍着笑意就往山谷西面跑去。
她在前面甩着两条小辫子,他在后面牵着两匹马。
虞从舟回想自己说的话,不由地觉得自己越来越开窍,甜酸话都说的越来越利索,舌头也不大了,他得意地想、原来爱当真能把呆子变聪明!
……
一直走到夜空漆黑、雀声渐起,还是没有走出山谷。二人躺在草地上歇息,让马儿在周围啃青草。
抬眼望向天空,松鼠在星座间跳跃往来。四周虽暗,却是一派与世无争、出尘出世之景。从舟笑叹,
“乱世之中,竟能享此宁静之地。我托了你的福了。”
她望着天上繁星,漱漱如雨,很惊讶地说,“比大梁的星星多多了呀!”又指着南方一颗星星说,“你看那颗,好红好亮啊。”
“那是心宿流火。”虞从舟温和一笑,双手枕在头下,“尝听闻,人间每一个人,都是天上的一颗星星。不知我会是哪一颗?”
窈儿一骨碌翻起身,下巴垫在他胸前说,
“从舟哥哥,你肯定是角宿啦。”
虞从舟一听,心花含苞待放。角宿二星是苍龙之角,天庭之门,七曜所行,日灵所藏,没想到自己在窈儿心目中如此高大。
她坐起来摘了两把草,学着从舟的声音压粗声线说,“‘我采了两株花,一株是给你的,另一株也是给你的’。”
这话好像下午自个儿说过… 从舟正摸不着头脑,她又捡了两根树杈,插在他发髻两边,摇头晃脑地继续学着他的声音说,“我是角宿,我有两只角,左角是天门,右角也是天门。”
“你!”她竟然嘲笑他下午的囧态,从舟抿着嘴,鼓着脸,她却愈发笑得酣畅抒怀。
从舟在她的笑声中眯起眼,撩起一勾坏笑,语声温腻却也凌厉,
“你太得意了!!”
窈儿甚至没来得及惊呼一声,已被他圈住腰,带倒在地。而他压住她身体,双眼隔着三寸空气俯视着她。他摄人的笑容越来越近,窈儿涨红了脸颊、忽然就闭了眼。虞从舟佞笑一声,却啊呜一口咬住她嫩嘟嘟的脸蛋儿。
“啊!”窈儿痛得叫出了声,睁大了眼睛瞪住他,半个‘坏’字咽在嘴里。
从舟松了口,看着自己一圈齿痕红红的印在她脸上,笑说,“那你闭上眼睛是等什么呢?这样 ——就不坏了吗?”
他在她零距离的注视中,轻轻吻上她的嘴。突如其来、似陌生似熟悉。山谷中清莹的露水润湿了他的唇、也沾湿了她的眼。
从舟解开衣衫,结实的胸膛在夜色中朦胧诱幻,窈儿微微打了个抖,从舟缓缓覆下,用温热的肌肤一寸一寸暖住她。
她忍不住一手圈过他的腰、摸上他的背,却惊讶地发现、他背上胸前四处都是残疤旧伤,触在掌心竟是憷心的痛。
多处疤痕似有半尺多长,摸着像是刀伤剑痕、新旧连横。没想到朝堂高位上、俊美如他、风姿仪表颠鸾倒凤之人,身上衣下竟会如此伤痕累累。难道,是他在战场上受的创、挨的伤?
但他全未在意,只是眯着双眼,温润的玉唇嚯吸着她的耳廓、颚下、胸前,掠夺她所有的思绪。她渐渐沉迷,他激情兴起。
不过须臾,他见她迷蒙了眼帘,即用双手轻轻拨开她的衣裙,抚上她的腰曲线、握拢她的丰盈。他的掌心似乎温存着魔力,一阵阵激荡作法、令她顿时像一个失了原神的小妖、不由自主地贴吻上他颈间的每一弯弧度。
他的手几番流连辗转,终是滑向她最细腻、最引人深陷的地方。她倏忽别过脸、似有退却、又仿佛不舍,咬着唇将酡红的小脸掩进翠草中。
他温润地笑着,一手揽过她的肩,让她能更舒适地躺在他的臂弯中,另一手渐渐探入、手指半进半濯。她在他怀中不由自主地蜷起了身,他伺机浸吻上她的唇,不让她再有转侧的机会。
她的红颊泛着三分羞怯、七分旖旎,他心中却是十分的狂热、十二分的神往。
他来来回回、她上下飘摇。仅仅是他指尖温柔的拨点、和指节棱峋的勾转,便瞬间化解她冰封太久的身体,令她在他的手中一点一滴地融化。
他的手指间润满液露时,他抽出手,将自己换入。“呃… ”她急抽了一口气,忍不住上身猛地弹起,紧紧贴进他的怀里。他连忙将她搂的更紧、口中轻呼着她的名字,她像得了安慰的孩子、渐渐放松身体,任他在她的身心中日升月移、潮涨潮撤。
从舟虽然动作略显生涩,但却极尽温柔。每一次云过留痕、他先以激情的身体令她沉醉,又用柔软的唇舌唤醒她的灵魂。反反复复、一昏一醒间,她每每忘了这是人间还是天上,只是控制不住地时而亢奋、时而堕落、在轮回中一再的深陷。
她被他融合消蚀,却没有一丝痛涩。明明像一只小猎物、被他俘获禁束、却又觉得满心从未有过的欣悦自由。
她眼角淌过一滴泪,但唇角弯起柔美的弧度,她这一生、从来没有想象过人间竟然可以有这样的享受。而今夜,却是如此真实。
她的身体在他的催动下越发的绵软、唯有心还飘在空中、以他的节奏浮浮沉沉。她此刻再无一丝克制,仿佛在这遁世的山谷间,她终于寻到一片岛屿,可以静憩、可以缠绵、可以全身全心的交付给他。
即使这只是海上暴风的风眼,她有过这一刻欢爱、再也不想记得其它。
他与她、欢喘连连,倒叫旁边的两匹马驹渐渐尴尬。它们回头瞅着他们、似乎颇有疑惑、又似乎全然理解,便慢慢悠悠地甩着马尾、向草坡另一边走去。
星月夜、翠草坡,一对人、一对马各自欢愉。远处、马驹的嘶喘声愈发豪放,相映成趣,倒衬得他们二人欢爱的好生斯文典雅。
山谷风回,四周淡紫色的迷迭香、就这般迎着氤氲,悄悄绽放。( 原本在‘她渐渐沉迷,他激情兴起’后面就只接了这一句‘四周淡紫’的话……是被77君连夜逼出中间这一段‘骨头汤’的 @~_~@)
……
晨曦照耀,姜窈睁开眼,发觉自己的侧脸仍是贴在他的怀里,他的锦袍裹在他们身周。朝阳的光透过锦袍照亮他结实的胸膛,他身上的伤疤或深或浅、益发明显。
她的手指慢慢划过他的疤痕、指尖不禁有些颤抖。从舟便也醒了,痒痒的笑,把脸探进锦袍中,萌魅万千地看着她。
她抿着唇、轻声问,“从舟,你身上为何有这么多疤?”
从舟愣了一会儿,瘪了瘪神态,“少年时,我剑艺不精就去了战场,难免挨刀……那时王上年少即位,可遣可信的武将太少了… ”
果真是沙场上的伤……她从前总把他当作是自幼顺风顺水、君王身侧长大的隽贵公子,却忘了乱世之中、越得君王信任,生命中便越多了难卸的重责。
“不过实战历练了几年后,我就剑法大进了。”从舟又重拾自信地笑。
她疼惜地瞧着他,原来他和她一样、身上的伤处新旧相叠,只是他们二人同像小刺猬一般,身披甲刺、便以为掩得住过往辛酸、和心中柔软。
但从舟只是一转眼神、忽尔邪邪而笑、睨看她道,“你嫌我?”
“呃?”姜窈连忙摇了摇头。
他眉眼一弯,笑得好生俊美,搂住她轻轻说,“莫告诉别人,我怕被人笑。但若是你嘲笑我,我就甘之如饴。”
姜窈眼眶有些酸,心中又翻起一丝甜,她轻轻拢上他的背脊。
原来不只是百合粉遮得住伤,默然负重、看淡创痛,亦可掩伤
……
同一夜中,秦国、咸阳。
范雎府邸,有人深夜求见。
那人披着斗篷,看不清眉目。管家领他至偏厅。推开门,范雎一身冰绿色长衫,已立于厅中。
门在身后一阖,那人解下斗篷,原来是苏辟。他向范雎拱手一揖,顺手从衣袖中取出一只暗红色小盒,双手递上,
“范大人要在下偷一枚‘命追’毒针,在下已取到,便在这盒中。”
范雎笑着接过,“苏兄果然诚意昭然,办事神速。”
“听说此毒甚烈,每年会在春分开始发作,肤烂骨断。若不得解药,则十五日后死于清明。但解药只由王稽掌控,极难偷到。”
“我知道。”范雎神色清冷,“你回去罢。以后每日申时来我府中议事。我明日亦会向王上保荐你。”
苏辟见范雎愿将他纳为帐下谋士,便欣然告退。
范雎慢慢打开那只小盒,里面一枚极细的银针、在毒汁浸润下早已没了银白之色,通体透黑,泛着点点墨绿。
一个身影从旁掀帘而入,急道,“公子你到底要做什么?!”
范雎沉默不语,连看都不看郑安平一眼。郑安平愈发心焦,“我知道公子想救小令箭。自从公子发现她脉中有此剧毒,就一直寝食难安。但公子你… 你绝不能以身试毒!”
☆、替我自由
范雎怆然一笑;答道,“若这世上只有一人应为她以身试毒,那也该是我。”
他眼中渐渐起了雾气,目光聚焦在很远的地方,
“当年我一心想入秦复仇,不惜利用他人陷害、领受死刑。那时我奄奄一息;小令箭为救我性命,苦求于王稽。虽然我算到王稽早已有救我之意;但我却没有算到,他会看中小令箭的身手;利用我的生死相胁,逼她做秦国死士。
“那时她还只是个孩子,却为救我;情愿以命换命,受死士营‘命追’之毒,自毁一生。
“七年了,她每年春分清明,都要受体肤尽溃之苦,每日每夜都活在被敌手杀死、或被死士处死的恐惧中,我却一无所知。若不是在从舟那里为她搭脉,我只怕一辈子也不会去探查当年那场变故。
“我曾怒骂从舟,为何对她用刑如此之狠。但那日在郑宅,我擦去她身上的百合粉,却看到她身上各处剑伤刀疤。是她为了救我、逼为死士的这些年中所付的代价。我才是累她受伤最深的人。
“所以这些年来,她不让我去赵国找她,也不告诉我她父亲姐姐家宅何处,只是和我相约,每年初春梨花开时在莫梨亭相见、以报平安。因为她知道初春时分,是每一年中她还能为我演最后一场戏的季节。每次与我分别,都是在春分之前。若她熬不过那一年的‘命追’毒发、死于清明,至少也能让我再安心一年,不到次年春天不会发现。”
郑安平无言相劝,脸上忧虑却更明显。此时一盏烛灯恰好燃尽,范雎起身点起另一盏灯。房中渐渐起了苦涩氲味,郑安平忽觉眩晕,不一会儿,已昏倒在地上。
范雎看着那盏灯,温暖的光晕摇曳间似乎晃映着小令箭孩童般的笑容。她向来都是这样,明媚盎然,就算鄙衣粗裹,也掩不了她的温暖亮色。只是温暖背后,凉苦都在她心里。
范雎淡淡苦笑着,望着那张若隐若现的笑颜轻声说,
“你骗了我,也骗了从舟,但骗得最深的人,是你自己。你的温暖只不过是烧着自己的芯。
“我已欠你七年,不想欠你一生。如果我的命可以换你一粒解药……你要替我自由。”
范雎从盒中取出那枚‘命追’毒针,翻起衣袖咬进齿间,又用小刀割开上臂血脉,未有一刻迟疑,已将毒针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