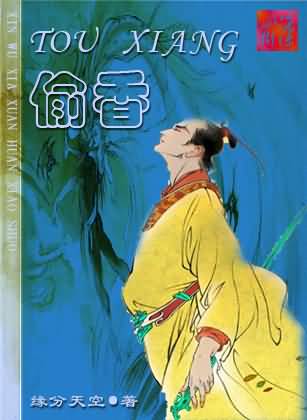迷谍香-第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小令箭一手慢慢摸进前襟,摸着摸着瞟了小盾牌一眼,两人心意暗通,下一瞬间齐齐转身拔腿又跑。虞从舟看她跑得那两步吧唧样儿,笑着摇了摇头。
他不慌不忙,两边袖口一掖,足尖略一施力,跃腾而起,身体旋圜飞出数丈,再落□来时,刚刚好欺在小令箭身前。
他并不顾她眼中惊诧,径直一探手,摸进她襟中,果然摸到一截竹管般物事,立时握进手中。随即又转身腾空,以轻功相辅,凌空几步后,他已稳稳落坐在自己坐骑之上。
此时却听几丈开外、小令箭颤着声音喊道,“把东西还给我!”
她也不再逃了,拖着步子又向他走回来,只是她脸色陡然煞白,倒令虞从舟有些惊诧。
“请把东西还给我。”小令箭走到他马下,语音仍微颤,神色却坚定。
虞从舟微有不解,摊开掌心,一看之下,神色遽变。
手中并不是那竹管密信,而是一支翠绿色的玉笛。这玉笛他最熟悉不过,竟然与娘亲生前最爱吹弄的那支一模一样,通管是满玉之色,为玉中稀品,笛身刻着淡淡桃花纹路,连笛尾所雕的抬足小鹿都神态相若。
若不是这一支玉笛比娘亲那支细了一整圈,他真的要以为是她从虞府偷去的了。
“这玉笛,你从何得来?”虞从舟神色微滞,定定看着她。
小令箭并不回答,始终执拗一句话,“请大人还给我。” 她一手紧紧拉住虞从舟的马缰,怕他走脱。
周围诸人看见那玉笛,知道价值不菲,都诧异这女扮男装的小丫头竟会有此贵重之物。
行过军的人最看不得主将的马缰被勒,此时樊大头见她拽着公子爷的马缰,立时怒从心起,挥起马鞭便劈到她手臂上,喊道,“敢扯俺们虞将军的马缰?!你丫个小骗子,偷东西上瘾啊?!说,到底是哪儿偷来的?!”
小令箭仍是不答话。她手上吃了鞭子,脸色更苍白了些,但依旧牢牢地拉住虞从舟的马缰不肯松手。
樊大头吃了闷,又抡起马鞭几鞭抽下去,小令箭的手臂上顿时染出几道猩红的血痕。她痛得哼出了声,但仍没松手。
她皱着眉头忍着痛,另一手摸到颈后的衣领里,摸出一截小竹管,递给虞从舟,说,“我拿了大人的东西,是我不对。。但请大人把笛子还给我。”
“这笛子,你到底从何得来?”虞从舟愈发起了疑心。
却见小令箭一抬头,倔强的眼神望着他说,“大人无权相问,我无须作答!”
樊大头又要抡鞭过去,虞从舟一挥手止住。他再好奇,她说的却并没有什么错。
他仔细看了看那截竹管,封脂并无破损。他一手将竹管塞进怀中,一手将那支玉笛递还给她。
小令箭得了笛子,立刻松了手,向后退了两步,趴在地上磕了个头,生涩地说,“谢过大人。”便也不理众人目光、起身和小盾牌一起走出那僻静胡同,转进人海中
……
秦国,咸阳。
这一日,云层低徊,雾气缭绕,秦王宫缥缈于云雾间,金碧辉煌时隐时现,如浸仙境。
而大殿之上,秦王心思百转,也难解今日之忧,剑眉紧皱,如陷绝境。
数月来,秦军中不知为何窜起一种流言,说如今秦王手中的统军兵符并非真符,乃是即位时模仿假造。仅此一谣已足以动摇军心、引百将质疑,更可怕的是传言中秦王失却真兵符、不得不刻意造假的幕后‘真相’……
秦人皆知,十几年前,先王秦武王在洛阳拜见周朝天子时,因与人比试举鼎,绝膑而亡。如今流言却说,先王自幼力大,那时二十二岁正当年,怎会举个鼎就气绝了呢,必是公子稷与公子市向来觊觎兄长的王位,与宣太后合谋,毒死了先王、弑兄篡位。公子稷虽然比公子市年长几岁,但他长年在燕国为质,所以那公子市原本仗着宣太后宠爱,对王位势在必得,没想到赵王半路硬插一脚,以赵军兵力逼迫,宣太后最后只得立了公子稷为秦王。
军中士兵都在传,当初公子市气不过,毁了兵符,好教刚即位的秦王骑虎难下。弑兄篡位秦王亦有份,小辫子被公子市抓得紧紧的,所以只得哑声咽了黄莲,着人秘密仿造了兵符,以假充真。
流言越传越真,秦王起先淡然置之、并不理会,等到情势愈急、秦王欲出面辟谣时,宣太后召他入见,一番秘密耳语,原来,事情虽然并非像流言所说,但那兵符还真就是个假造的!
秦王霎时白了脸色,自己坐了这十几年王位,不但权利始终被母后架空,连手里的兵符都是假的、还一直被蒙在鼓里,这傀儡君王做得、真可算是前无古人!
此时咸阳城外,王、吴、韩三员老将已陈兵数万,黑压压一片看不到头。假造兵符一事,已经败坏君威,更不要说当年先王之死,若真是被人毒害,秦国内乱必定一触即发。
“众卿家有何办法可解围城之困?”秦王神色萎顿,声音暗沉。
无人敢答。
众臣子们心里也不是没有疑惑,如今见秦王面色如灰,更是怀疑谣言是真、似乎秦王的确拿不出真兵符来辟谣。
大殿上公子市与穰侯魏冉分列群臣之首,秦王瞪了他们两人一眼,心中愤恼。穰侯魏冉是母后的亲弟弟,这事他肯定也早就知道。似乎只有他一人被蒙在鼓里,如今谣言四起,却又要他一人去面对天下质疑。
此时一个耄耋老臣颤巍巍出列道,“大王只须遣一名臣子、携了兵符前去城外三位将军的军营,三位老将军都是见过先王兵符的,若得亲眼再见,必然再无疑惑,则谣言自辟,危机自除。”
群臣纷纷点头,秦王欲哭无泪——老家伙你是故意来整寡人的吧,若寡人有那底牌可以辟谣,何至如此为难?
他冷笑着扫视群臣,“那,哪位爱卿愿担此重任?”
果然众人又沉默了。原来真的没有人相信他这个王,更不敢替他拿着假兵符往城外军营中枉送性命。
秦王心冷如灰。忽然听到大殿远处有一人出列朗声道,
“微臣愿往。”
这一声温和尔雅,在秦王听来正如一阵久违的和风,他心中的死灰随之簌簌而下。
秦王眯眼遥看,仍看不清那人面容,问道,“爱卿是……”
“微臣,张禄。”
这张禄正是范雎。他自从被王稽救入秦国,便隐去姓名,改名张禄,由王稽推荐在秦廷做了个小官。奈何秦廷人物众多,要引起秦王注意谈何容易。如今秦王内忧外患、众臣推诿,对范雎而言,若能帮助秦王化解这番危难,必可得到秦王信任。
秦王道,“近前答话。”
范雎遥遥走来,身姿修长,神韵淡雅。秦王左思右想,仍想不起‘张禄’这个名字。
见他不过二十多岁,秦王心里又凉了半截,或许他是出名心切,或许是不知深浅,这张禄当真能劝退王、吴、韩三员老将么?
秦王当然不能说出那兵符是假,只得试探道,“若三位将军见到兵符、却仍旧咬定寡人的兵符是假、意欲犯上作乱,卿当何为?”
“微臣既然应下,自有对策。只是此时不可泄露。”
公子市哼笑一声,睨了他一眼道,“好大的口气!若你不能劝退三位将军,秦宫堪忧,你可知该当何罚?”
“若微臣不能劝退三位将军,必不可能全身而退,定然会被三位将军处死祭旗。是以微臣并未想过能活着回宫领罚。”
☆、凤落枫扬
秦王不由惊异,此人竟抱着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心境?
此时秦王心中开始打着另一种算盘,还未想清楚,又听范雎娓娓而言,
“虽然穰侯有十万军队驻于咸阳城东三十里外,但三位将军要查清兵符真伪、无可厚非,因而现下他们占理得势,大王绝不能此时出兵。”
秦王愈惊,难道此人真懂读心术?
范雎静静仰起脸,目光清澈地望向秦王。秦王微微一愣,细看此人,眼尾斜挑,轮廓英挺,双唇丰美,姿仪绰约。这般面容,倘若见过必定难忘,为何他在朝廷为臣,自己却全无映像。
范雎丹唇轻启,“但若大王派微臣持兵符前去示恩,则显大王胸襟磊落,若三位将军仍咬定兵符是假,杀死微臣、进兵咸阳,则大王的兵符已然落入三位将军之手,是真是假再也难辨,大王只须称三位老将故意制造谣言,又私吞兵符,显是意欲谋反,大王便占理得势,与其易道。到时再派穰侯出兵讨伐,绝对师出有名。”
秦王彻底怔住。这末品小臣竟如此思虑缜密,他似乎并不在乎那兵符是真是假,倒已为他想好各种退路,甚至,愿为这几步棋牺牲自家性命。方才误以为他出名心切、或不知深浅,实在看低了他。
秦王点头诺许,着宦侍将盛着兵符的玉匣交给‘张禄’。
范雎低下头,恭敬地跪在地上,双手高举,接过玉匣。那一刻,他唇角微微上勾,牵起一个无人看见的诡秘笑容
……
范雎领命离开秦王宫,殿上众人犹自焦急议论。但不过两个时辰,却听殿外宦侍高声宣道“张禄觐见”,只见他体发无损、飘飘然地回了来。
“三位老将军已然退兵,并托微臣带言,自悔听信谣言,不日定当叩见大王,向大王请罪。”范雎将兵符交还给秦王近侍,一身淡然跪地陈述,眼梢带笑,面容泛着微光。
朝中众臣尽皆讶然。秦王亦是喜出望外,不过,初见已知此人绝非寻常,此时倒也不那么吃惊,当即赐张禄益爵四级,封为公乘,进御前参士。
秦王想问他到底同三位将军说了些什么、居然能够安然退兵,但想起他之前说过‘不可泄露’,料想或许有些事不便在众臣面前讲。秦王便散了朝,着他去书房密谈。
不料范雎仍是微微笑着,只说,“他人信与不信,只在于大王心中是否自信。三位将军见大王肯以兵符相示,已然信了一半。至于微臣,官微人低,大王敢派我去议谈,足见大王自信满满,心无芥蒂,三位老将军便信了我的那番劝退。”
秦王似乎也信了。范雎心中暗笑,其实他说过什么、做过什么、如何退兵,都只能在他心里,自然不会让秦王知晓。
秦王又仔细打量了他一番,忽然开口道,“今日之险,全靠爱卿周旋,寡人深记。如今寡人另有重任交托与你。”见范雎神色平和,秦王目光愈发深邃,“秦国间谍数以百计,网络密布天下诸国,但他们都只效命于母后。寡人想派你去赵国伏间,避开母后耳目,直接上报与寡人,你可愿意?”
范雎心中一怔,他本意借今日之事接近秦王,搏其信任,但不料、秦王似乎信了他,却又要将他派去赵国。他心中颇乱,面上仍镇静如常,当即称谢领命。
“你如今是御前参士,可直接入内殿见寡人,平日亦不须上朝,所以你即使不在秦国,也不会被人发现。不过,去了赵国,你这真名‘张禄’便不能再用,须换个名字。”
范雎微微抬眸道,“‘张禄’并非是微臣真名。微臣本名范雎。”遂将从前在魏国受诬,幸而得救逃入秦国的事向秦王讲了一遍。
秦王这一日间被他惊了数次,此时更不料他连姓名都有此一变,但想到他连这等欺君之罪都肯坦然道出,反而愈发相信他心中坦荡。
范雎离开秦王宫,在夜色中慢慢行走,心里略微有些失落。他拿出怀中一枚半圆形玉璧,感叹自己不知何日才能报仇雪恨。那玉璧上正面刻着两个‘毕’字,反面刻着一个‘白’、一个‘相’字,他想不明白,那究竟又是何意?
他轻轻抚摸着玉璧上的刻纹,忽然脸上漾起一抹欣悦微笑。可以去赵国也好,几年前、小令箭告诉他,她在赵国巧与父亲、姐姐相认,从此不再孤单飘零,而他在秦国潜伏、总是不能与她常见。这一回他奉命入赵,应该就可以寻见她
……
自从虞从舟见过小令箭怀中那支玉笛,回府便寻出娘亲生前总爱吹弄的那支,看了又看,的确很像,宛如一对,绞尽脑汁也想不明白那小令箭怎会有此物。
到了第三日,楚庄差人来送了卷信简,竟是江妍邀他明日在琮山相会、共赏红枫。虞从舟顿时心翔九天,其它的疑惑、好奇都抛诸脑后。数日来江妍两番邀约,着实令他受宠若惊。莫非王上那句“看来好事近”果然是吉言?
虞从舟抖擞精神,明日要衬得枫之彤色,更要衬得江妍之绝色,今日定当养精蓄锐。只是愈这么想,愈是一夜无眠,数完两千只羊,眼里还是晃着江妍的美颜飞扬。
总算天白放光,虞从舟揉去两片眼眶浮肿,挨到时辰,立刻热气腾腾地驰向琮山。
这一回他没再带樊大头,换成沈闻和晁也。这两人总还是斯文些。
几骑人行至山间小道的尽头,虞从舟一眼便看见一身黄色长裙的女子垂手静立于远处林间,她望向层叠的枫树,微仰着下颌,质傲如霜,姿妍胜雪。澄黄的衣裙掩在橘色枫林中,相映相合,更显妩媚。
虞从舟翻身下马,向楚江妍走去。晁也和沈闻相视一笑,遛到远处、以免打扰公子佳人。
满山的金红颜色熏得脸庞微暖,虞从舟脚下踩着厚软的落叶,口中轻轻呵出一声,“江妍。”
她回首看他,并无媚笑,但眉眼美艳得已似一抹朝阳的霞光,在林间闪耀。
二人在枫林间并肩而行。虞从舟摘了一片红枫,簪在她的发上,她微微一笑,略低了头。
“你喜欢秋枫?”虞从舟唇角弯弯、笑意酥酥。
“往年初春,你总约我赏花。我从没有去过。并非我故意拂你美意,只是,我素不爱花。”
“不爱红花,却爱红枫?”
“嗯。”一片枫叶飘落,江妍轻柔地抬起手,将那片叶子接在掌心。
“你总是与众不同。就好像。。你不喜艳妆,不喜珠饰,却又偏生生得如此美丽。。叫天下女子皆汗颜。”虞从舟在江妍面前总有些怯场,连说句赞美的话都大着个舌头。
江妍听多了他直白的恭维,已经不会再起麻意,只是自顾自地说,“这个季节的琮山,红得好看么?”
“嗯,红的很纯净、很耀眼。只是以你的妩媚英姿,怎会喜欢枫之萧瑟?”
江妍的眸光里闪过一丝凉涩,她垂下眼,看着满地凋谢枯干的落叶道,“春花烂漫,但我早已错过,注定不能回头。所以每当看到枫将凋零,我才格外不舍。就如同,夕阳西下,叫人最珍惜留恋的,就是那点余晖。”
虞从舟闻言顿住了脚步,不知江妍为何忽然起了伤秋的哀意,“你怎么了?”他边问边从腰间佩带上解下一只白玉雕的小葫芦,递给江妍道,“你尝尝这味‘锦秋酿’,毫无秋瑟之意,全是收获之季的丰闰口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