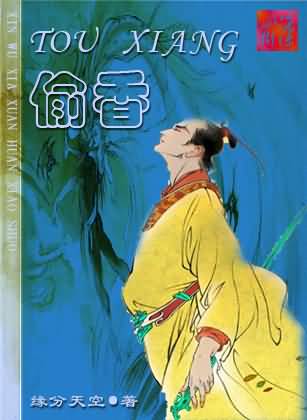迷谍香-第3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他对自己无奈地叹了口气,嘴唇摩挲在她前额发间,说,“你就无话同我说么?”
楚姜窈知道他说的是淮哥哥。她吞吞吐吐地说,“我… 范大哥……是、我早就认识范大哥了,在魏国就认识了。”
“他就是你的那个‘神棍朋友’、也是你梦里都会喊的‘淮哥哥’!”
怎么连这个都被他看穿了,这实在不大安全,姜窈身上一哆嗦,“你… 怎知……”
虞从舟冷笑一声,双手紧紧抠在她背上,不让她动弹,“‘范雎’?!… 这两字左右各大卸八块,合在一起就是你的‘淮’了!”
“你… ”姜窈听到‘大卸八块’,害怕地慌了神。
从舟看天边乌云密密压来,说,“不想说他。回房。要下雨了。”
她不敢多言,转身扶着他腰间,慢慢向他卧房走去。从舟说,“为何从前骗我、不让我知晓?”
“嗯… 范大哥不让我同别人说。”楚姜窈只好胡诌。
虞从舟想到范雎思虑诡秘,居然有些信了。
走到他卧房前,回廊上有几格楼梯,姜窈怕他吃力扯痛伤处,紧紧以肩撑在他侧胸。她这一撑一搂,霎那间竟叫从舟的心无所适从。一路行去,他愈发觉得这般场景似乎在梦中经历过:她拉着他的手,用肩膀抵在他的前胸,脸庞上蕴着少女的羞红之色,他随她一步一滑地走在冰上,彼时她的笑容如玉茗花开,暗淡了周围一片苍茫白色……
那真的是梦吗,只是梦么?但若是梦,为何在梦境中他亦闻到她身上的百合花香?
他怔怔望着她,神思漫离,脱口而出唤了一声,“小令箭…… ”
她抬起头,见他目光飘浮、眉宇间忽然换了温柔,不禁痴痴有些出神。
从舟愈发觉得那梦境过于真实。他心有冲动,想把她搂进怀中、或许那样、一闭上眼就可以再度入梦。
只是还未来得及,倏地听见一声响雷轰然袭来。她在他胸前微微颤抖,突然缩了双手,整个人从他臂弯中抽离,退到廊柱边、半晌无语,忽然却说,
“我、我最害怕打雷……我回房了,哥哥也早些歇着。”
她垂着长睫,不敢去看他,但依然掩不去她的目光闪烁。她绞着手指,转身跑进雨中,甚至没有给他多说一句的机会。
雨越下越大,这个傍晚太过沉闷。乌云集结、使天色犹如暗夜。而雷鸣声一浪一浪袭来,虞从舟在房内忍不住担心起她来。她如此怕雷,更不该让她一人独处,就像在山林那几夜,她也并未弃他不理。
他拿过一壶醇酿,忍着痛往她厢房走去。将到之时,却见一人身着黑色夜行衣,从她房中奔进雨里。此人轻功甚佳,在雨中仍如轻鸿破风,足尖三步点地,已腾起几丈,轻易翻过虞府高墙,又倏忽几步飘逸、身影渐渐在邯郸城中层叠的屋顶上消失不见。
虞从舟心中骤恸,无力迈出一步。
那人竟是、楚姜窈。
她一身黑衣,本该掩于夜幕之中、无人知晓。为何偏偏,一道闪电划过天际,照亮每处细节。
但即使没有闪电,他就猜不到了么?她的身形,他早已浑熟于心。
他苦笑着捏碎酒壶,走进滂沱雨幕。雨水沿着他唇角,渗入喉间,似乎比烈酒更灼,烫伤他胸口。
原来她怕的不是雷,而是心头的秘密……原来她会的不只是轻功和飞针,而是瞒天过海的骗术。
为何他越想信她,她越不可信。为何他越想留住她,她越不可留
……
洺烟湖边。子期草庐在电闪雷鸣中震抖摇晃。
范雎蜷缩在墙边,头痛欲裂。他尽力用手掌捂住耳朵,但双手颤抖不止、无法自控。雷声从他的指缝间灌入耳中,一声响过一声,震得他犹如千锤万针荡击在头颅深处。
他最害怕打雷。
他父母遇害的那一日,也是彻夜雷电大作。浑沌的漆黑、与悚栗的白光,在他眼前交迭,雷声如钝锯磨割在他心上。那一年,他不过是个五岁的少年。但他永远难以忘记被人逼迫着灌下毒酒的恐惧。若不是洪医傅与甘叔叔相救,他原本早已消失在那一天。
他活了下来。但头痛之症,每逢雷雨轰鸣,便会肆虐倾轧,常常痛到他失却尊严地在地上匍滚。
多年来的折磨,每次疼痛中他睁开眼,都会看见小令箭心痛地哭泣。而今夜,他连睁眼的力气都没有了。
“淮哥哥,淮哥哥!”有人急切地呼唤着他。
他不知道是不是自己幻听,仍旧固执地紧锁双眼。直到那人扑到他身边、衣服上的雨水簌簌淌在他的肩上,他方才豁然睁开眼。
真的是小令箭。她浑身都被大雨浇湿,黑色的长发、黑色的夜行衣都不断地滴淌着水滴。她见他痛得脸色惨白,急急用双手严严实实地捂住他的耳朵,眼神焦虑地打量着他。
每次打雷,小令箭都是这样守着他,她是最害怕他受痛的人,也是最能帮到他的人。她这一捂,他耳边雷声顿轻,额头的裂痛感随之缓和许多。他感觉到她的双手很冰。外面雷雨交加、狂风凌厉,而她依然来了。
他开始心疼。但昨夜天歌酒坊那一幕幕,更令他心乱得难以自持。他不自禁地吼道,
“你来做什么!”
他一把将她推开,她未设防、径直跌倒在数尺之外。
“淮哥哥… ” 她眼中愧疚,一顿一进、又爬到他身边,仍旧用手捂上他耳朵。
“你究竟还有多少事情瞒着我?”
小令箭想要摇头,却不敢摇头。
“说好‘一生无欺’,但如今,只有我一人记得?!” 范雎见她依然不肯相告,心如锥痛。他猛然用力又想将她推开,但她这一次牢牢跪在他身前,不移不动,只是坚持地用手捂着他双耳,怕他听见雷声会头痛加剧。
“你变了,你不再是单纯天真的小令箭,你究竟在想什么?你究竟要做什么?!”
“为什么你不说话?!你从前对我无话不说!”
“……现在无话可说了?!”
范雎从未对她说过一句响话,但今夜是怎么了?是因为见到她在酒坊里卑躬露胸,还是因为虞从舟在众人面前那野蛮的一吻?他控制不到自己,狂乱地喊着,他想逼她说句话,说句让他知道、他与她依然‘一生无欺’的话。
小令箭跪在他面前,睫毛颤抖,紧咬着唇。他看见她眼泪不住蜿蜒而下,却依旧一语不发。
范雎已被头痛折磨许久,此时浑身失了气力,心痛更是盘根错节,恣意肆咬。
他最后冷冷扔出一句,“你要变就变,何必理我如何!别在我发疯的时候却来见我!”
小令箭心头像被利剑剜割,多年来种种心酸、惧怕、强忍、无助,一霎那间都汇聚在胸口,直闷得她喉间泛起血腥之气。她哭着跪行两步,贴近范雎颤抖的身上,侧过脸靠在他肩头。
“我没有去做歌妓… 我真的没有。”她双手仍旧紧紧捂住他的耳朵,那一捂、隔去雷声、也隔去她的语声,“但我其实、比歌妓更不如……”
她知道他此时什么也听不见,所以才敢奢侈地说出、平日里就算打死她她也不敢说的话:
“淮哥哥,我… 我早就已经是个死士。每晚只庆幸着活过今日,闭上眼、又不敢揣测明天。
“我不想骗你的,但又怕你担心难过。我很想把一切都告诉你,但是我说不得。
“我也不想再骗从舟,我更不想害他。我知道自己应该离开他,但是我舍不得。
“淮哥哥,求求你,不要为我这样的人伤心烦恼。我只是一个吊在绞架上的虚魂。就算努力伸脚,也踮不到地了,就算奋力抬手,也触不到梁了。唯一载得动我的,不过一根细绳而已。却又偏偏系错了地方……”
☆、情血双刃
天明启金星;雷匿无惊。
范雎渐渐清醒,发觉自己躺在床榻之上,身上盖着薄被。他披上单衣,踱出草庐,水天之间仅剩一勾残月。
小令箭已经离开。昨夜自己到底对她都说了些什么,他不敢去忆想。她又对自己说了些什么?他始终听不清。
他沉沉垂下眼;余光中却见一人、身着肃紫锦袍,立于两丈开外。
他微微抬眸;却是虞从舟。
四目相接,仿佛寒流激涌、遇冰却缓。范雎淡了眸光;从舟浓了栗色。
此时,一人侧目睥睨,不问来意。
彼处;一人剑眉深颦,有霜半凝。
二人目光冲撞在一起,震起林中散鸟,仿佛双龙御紫檀,二峰出云端。此刻静默,似有百年沉寂,谁若先言,便已输去一半。
范雎并不担心,输的那人一定不是自己。因为虞从舟既然清晨来访,必然心有郁结,早已药石罔医、失了先机。
果然,虞从舟向他走近一步,开问却出乎他的意料,
“你,真的是范氏后嗣?”
他怀疑自己?为何不召兵卒抓他,却来孤身试探?范雎脸上没有表情,他不想作答。
虞从舟并不求解,反而给出另一解,“你可是… 生于周王三年*,六月初七?”
范雎心中蓦然一震,他的生辰,从未与人说过,就连小令箭也并不知晓,今日虞从舟怎会有此一问?他眼神略有闪烁、但只是一瞬。他强自镇定,道,“我是孤儿。流浪之人,不知生辰。”
但他的气场不复坚磐,怎逃得过虞从舟紧紧迫视的眼光?
“流浪之人?你五岁以前,难道不是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
范雎倒吸一息,幼时的种种、不知有多久不敢再忆,此时破闸涌出,他胸口痛楚泛滥,眼中苦涩湿润。
“你是谁?!” 范雎艰难自持,眼光如冰、望着从舟,却不自觉已经乱了心寸。
“我是谁?” 虞从舟仿佛等这个问题很久了,他箭步流星,向范雎走近,
“你看着我的脸!你认不出么?一丝线索都没有么?人人都说,我与娘亲极像,”他紧紧贴视他,凝着一双明眸,说,“难道、你一点都不记得娘亲的容貌了么?!”
这一句‘娘亲’,惊得范雎几步踉跄,向后退去。但虞从舟依然逼迫着他,愈发向他走近。
回忆、在往事尘封的角落里被丝丝抽离。母亲绝美的容颜、温柔的双眼,此时旖旎在他眼前、如云般幻现,又如雾般轻轻扑上虞从舟的玉面,无偏无移、几乎合成一气。
会是真的么?范雎的思绪一时轰乱、不知该在何处起落。他看着虞从舟陌生而又熟悉的脸,那玉琢而出的五官,仿佛天边一道彩虹,美轮美奂,却倏忽变作一弯尖刀,牵扯着太多往事黑暗、刺进他的心里。
“母… 母亲她…… ” 但是、那天的毒,那夜的火… 难道他们并没有杀死母亲?还是、有人救了她?
一颗泪从他眼角划出。有多少年没有为往事流过泪了,他记不得。
他强作镇静,低声问,“你母亲是… ”
“…蔚氏,秀名一个‘兰’字。” 虞从舟看见他的眼泪,目光忽然软下来。
这不是他母亲的名字,但听见这两个字,范雎心弦激荡,泪水如潮涌出。因为这一瞬间,他知道虞从舟并没有欺他。
范雎的母亲、是魏人,向来最爱兰花。而且那一个“兰”字,又是他幼年时学会写的第一个字,母亲珍爱异常… 原来母亲改名了……是啊,她要活在这世上,怎么可能不改?
他抬眼凝望着虞从舟,他的那一双栗色眼眸,的确与母亲极像,倾城绝姿。原来这世上,他还有一个弟弟?!他想起从前曾看过赵国各重臣的卷宗,依稀回忆道,
“你、生于周王九年*?”
虞从舟点了点头,接着他的话道,“周王九年,三月十五。”
范雎不断想起二十几年前的那一夜电闪雷鸣、火烧中庭,原来那时、母亲已经怀有身孕!范雎唇角含着一丝苦楚,却涩涩地笑了。
他重又凝聚眸光、细细打量从舟,仿佛这是今生今世第一次相见。他们身上竟然流着同样的血,原来从舟,是他的弟弟、亲弟弟。过去这么多年间,他们究竟擦肩而过多少回?
“母亲她… 一切可好?”
虞从舟目光微颤,灰了神色缓缓向后退了两步,垂首道,“娘亲她… 在周王十七年、故去了… ”
范雎沉沉一阖眼。他本已在黑暗中跌滚多年。若注定此生无光,为何要让他误信零星的希望?他心中苦道,“原来我还是无福无缘,上天还是不肯让我多见一眼!”
他怔怔咬着唇、却听见从舟撩起衣摆,跪在他面前,轻声说,“娘亲临终、最大的心愿,便是要我找到哥哥,与你兄弟相认。”
母亲已逝,膝前跪着的、是他此生唯一的兄弟。范雎心中狂浪,冲碎石化已久的重重栈防。他伸出手,几乎就要触上从舟双肩,但那一瞬间,他的脑海里有太多思绪纠缠堵截,亟待梳理。当年母亲如何逃脱死劫?从舟为何会在赵国出生长大?他再次忆起从舟的卷宗,“虞从舟… ” 他喃喃自语道,“原来,是虞愿清… ”
范雎的思绪如扁舟掠过万重山阙,最终偏偏胶着在从舟极像母亲的容颜上。自己已经走上一条不归路,若与从舟相认,岂不是会连累他一起坠入无间?他望向窗外,阳光在湖面上反射出刺眼的光芒,他借着那一点刺痛,把激荡之心重又凝结成冰。
他冷冷说,“我不是你要寻的人。我与你,不是兄弟。”
“你!为什么要骗我?!”
范雎方才明明泪流不止。城府如他、亦会有那种失措、那番反应,这令虞从舟心底认定是他。此时未料他会如此作答,虞从舟仰看他道,“你的眼神骗得了谁?难道我不像娘亲么,难道你看见我、不会想起娘的模样吗?!”
范雎靠近他一步,不遮不避地看着他,决绝道,“虞上卿,我即不像你的母亲,也不像你的父亲,难道你看见我,会觉得我是他们的儿子么?”
虞从舟一时哑然。他细看范雎,玉眸挺鼻,五官灼灼,仙气榷凝,但的确、并不似父母。他略微皱眉,但很快反驳道,“你若没有见过他们,怎知自己不像?!”
范雎收了目光、瞥向天际,不理不答。
虞从舟霍然站起,从怀中拿出毕首玉,一按玉珠,锃锃匕首霎时翻弹而出。他递到范雎眼前说,
“那,这样东西呢?你也不认识了?”
范雎刹那失神,他怎么可能不认识?他右手下意识地摸上自己腰间。恍惚间听见从舟又说,
“不用摸了。这不是抢你的,也不是仿你的。‘毕首玉’,世上本有一双,上阕在你腰际,下阕在我手中。”
世上本有一双?范雎呼吸急促、起伏难控,目光定定、却心绪游移。虞从舟不紧不慢地问道,“你的玉上,可是正反各有二字,一面刻着两个‘毕’字,另一面刻着‘白’与‘相’字?”
从舟说得丝毫未错,范雎看着他的双眼,不禁喉咙酸涩。二十多年来,他始终揣测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