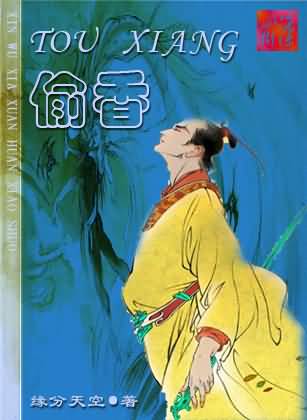迷谍香-第2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可是他永远也不知道,姜窈此时、孤单一人瘫匐在几百里外的莫梨山谷中,浑身浸血,体无完肤。自从多年前、姐姐在她血脉中埋下‘命追’之毒后,每年春分至清明这十五日间,都是她的炼狱之劫。
春花开的越烂漫,她身上的毒性便越烈、漫骨烂肤,叫她全失人形、如鬼如魅。
她害怕被人看见,因而每年春分之前、就躲进空寂幽暗的莫梨谷中。那里野兽少、不会将她叼走,人迹更少、不会被她如鬼般凄厉的哀嘶声吓到。
这一日始终有雨,雨水落在她的裂肤上、嘶嘶沙沙地痛。她早已无力挣扎,任痛意烧灼全身。呼吸之间、全是血腥之气、混杂着泥水的苦凉。毒性亦令她的骨骼多处断裂,她无法行动,勉强爬了几尺,抓过草丛中的几只蘑菇塞进嘴里充饥。
待雨停时,已是深夜、山谷里漆黑无光。她左手指尖摸上一颗小石子,努力将它推到旁边的一堆小石块中。
她又重新数了数,已经七块石头了,她僵痛发麻的脸上淡淡映出一点笑。毒发之痛常常令她的意识忽沉忽悬、难分晨昏,她只能靠清醒的时候、每夜堆叠一颗石头以记录自己熬过的日子。
已经熬过七日了……过去一年她无大功亦无大过,主人总算赏了她今年的解药。她看着石头子、一遍一遍跟自己说,再熬八天、毒性就会消散了… 不知道小盾牌是不是也得到解药了呢?
想来可叹,她与小盾牌相识于人间地狱、早看惯生死,但每年此时,却反而最怕让对方见到自己垂死凄苦的样子。
这许多际遇她永远都看不懂。就像当初在魏国大梁,若不是为了救淮哥哥、她怎会被姐姐投入死士营?但若不是做了死士、负伤垂危,她又怎会被姐姐看见身上胎记、认回亲人?
她涩涩地笑了笑,想起姐姐那张绝美的脸… 意识愈加痛苦沉沦。毒血缓缓从她溃裂的皮肤中渗出,染红了身下整片草坪。她像一只坠进陷阱的幼兽、呃呃哀叫、无人听闻。她双手深深抠入泥中,一遍一遍忍过痛意肆虐。直到天色微亮时,她仿佛被撕裂了全身的骨骼、终于再无意识、重又昏死过去。
☆、来势汹汹
入秦的道路颠簸难行,这一日,蔺相如、虞从舟等人终于要过函谷关,众人都格外谨慎,不论军阶,皆装扮成蔺相如的随行侍卫,下马下车、一律步行。
虞从舟欲与杜宾等人一道步行,被樊大头粗鲁制止,“爷您长成这样、就别出来招蜜蜂蛰了!车里坐着吧!”
他见蔺相如也忍笑点了点头,只得坐进了马车。
似乎所有过关的车旅,都被严格盘查。蔺相如担心秦人会以强抢璧,因而不敢用政客通行文书,而打算用普通的商旅通行文书。听见秦兵守卫向他们的车走来,虞从舟和蔺相如在车内皆微微紧张,不知是否会被守卫盘问出破绽,却忽然听见、在车头回答问话的不是驾车的晁也,而是一个说着流利秦国方言的人。
蔺相如吃了一惊、脸色突变。虞从舟却心头顿暖,不由以拳按唇笑了起来。他见蔺相如怪异地看着自己,尽量忍了笑,向他示意不必担心。
一盏茶后,果然全队车马顺利通过函谷关。待行的稍远,虞从舟终于忍不住,一掀车帘,拉住晁也身边那人的衣袖,笑道,
“你总算知道回来!”
那人回头看了他一眼,欲笑未笑,却身体发软,加上从舟的那点扯袖之力,那人忽然栽进车中,身体的重量压得车帘裂开坠下。
从舟此刻大惊,眼前分明是女扮男装的楚姜窈,但她一脸苍白、唇无血色,全然不像往日那张红润明媚的熟悉脸庞。
“你怎么了?你病了?!” 从舟扶起她,各种担心、理不出头绪。
“快好了,” 她在他臂弯里轻轻地说了一句。
她双眼沉重,很想闭上眼歇一会儿,若从舟他们再晚两日过函谷,她就不会让他发现这狼狈模样了……于是她强打精神,看着他笑了笑说,“见到哥哥,我就全好了。”
但她终于还是沉沉睡去,一直到天黑了才醒来。烛火昏暗中,她看见从舟焦虑的眼神、紧紧凝视她。
“得了什么病?竟如此来势汹汹?”
楚姜窈早想好了借口,笑道,“春天容易得风寒呐。但我就快要好了,别担心。”
“胡说,风寒怎么可能这般沉重?!”
“越靠近秦国,这风寒流疫便越是厉害。秦国的东西都狠得很!和别国的不一样。”
虞从舟正要开口,忽然一只绿头苍蝇飞进屋子,停在她的床架上,姜窈坏笑着对他说,“你不信?我赌秦国的苍蝇不怕人,就算你拍它、它也不会飞走。”
从舟本来就闷恼,看见那苍蝇便更恼,一掌拍在床架上,床架震得厉害,但那苍蝇果然没飞走。
姜窈得意地笑了,说,“凡我赌的,没有输的,哥哥你总不信我!”
虞从舟眉头皱得更紧了,他暗使内力,又拍了一掌,内力震荡,那苍蝇终于飞走了。
他正要再问姜窈的病,那苍蝇居然飞来停在他脖子上,他抬手一掳,想赶飞它,没想到秦国苍蝇真的不怕人、愣没飞走,径直被他掳死了,搞得他满脖子都是虫虫肠肠。虞从舟本就是爱美爱干净之人,这一来,恶心得他一夜都吃不下饭。
第二日起身,虞从舟再探姜窈,见她真的气色好很多,虽然眼神仍然疲惫无光,但整个人看来毕竟不是毫无血色了,他这才有些相信她只是风寒感染。
从舟怕人多反而引人注目,于是让杜宾等人赶去茔城等待接应,他一人陪蔺相如赴咸阳。他本想让楚姜窈也去茔城歇息将养,正犹豫着说不出口,姜窈忽然耍着小性子说,“这么久没见到哥哥了,才一日又要分开呀?” 这话一下子戳到他的软点,他便假装沉着脸、默许了她。
坐进马车,楚姜窈带着些试探地问道,“哥哥离开邯郸的那几日,小盾牌… 他可好?”
虞从舟回忆了一下说,“好像那几日里我都没有见到他,可能是你不在,他嫌闷,出去玩了。”
楚姜窈脸色倏地变暗,眼神略灰,溶杂忧虑之情。从舟起了疑惑,但见她愈发神思飘忽、不言不语,也不知道该从何问起。
数日后终于到了咸阳。马车驶入赵军的驿馆,蔺相如与虞从舟卸下行装,略拂风尘。正待入馆,忽听一阵疾奔的脚步声、打破周围静谧。他回头看去,是楚姜窈奔向驿馆院外一人,啜泣着喊了声,“小盾牌!” 她双眼水汪汪,急急抓起小盾牌的手,上下打量着他说,“你… 没事吧?”
小盾牌笑着摇了摇头,问道,“你呢,还好么?”
楚姜窈用力点了点头,额头触上他的臂膀,在他青袖遮挡后还是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他们二人各有一段劫后重生、难为人道。小盾牌虽亦伤感,但他感受到周围人疑惑的目光,立刻紧了紧她的手,嘻嘻笑道,“那么久见不到你了,我不晓得上哪儿去找,” 他坏笑地指指虞从舟,说,“后来一想,他要去的地方,或许就是你会在的地方,所以就到这儿来等喽。”
楚姜窈亦缓过神来,抬头悄悄看一眼虞从舟,稍显羞赧地笑了笑
……
三日后,蔺相如持和氏璧,入秦王宫、殿会秦王。虞从舟只能在宫外暗侯,心中焦虑难安。两个时辰后仍不见他出宫,正不知他是安是危,忽见他神色严肃地行出宫门。蔺相如略去一节他差点触柱而亡的惊险,只说他已经劝说秦王,必须斋戒五日,再行大典、礼迎和氏璧。
他与虞从舟商量之下,料想五日之后秦王也决计不会按约送出十五座城池,为今之计,必须趁这五日间护送和氏璧离开秦境。
蔺相如自然仍需要留在咸阳遮人耳目,虞从舟等人则持玉璧即刻潜回赵国。既然要离开,当然是瞬息必争。好在他们一路行至茔城,都颇为顺利,得以与杜宾等回合。
虞从舟作了些部署,派人沿渭水各处备下船只,以应不时之须,而他与楚姜窈仍以寻常兄妹身份从小路返赵,杜宾返回咸阳保护蔺相如,其他十几人则扮作马队、沿官道大路与虞从舟平行返赵,以引开注意
……
但楚姜窈却有不安之感。方才过茔城城关时,她似乎瞥见暗处一队蓝衣锦卫,看衣着马饰,很像是公子市的手下。难道公子市得知了虞从舟他们欲潜回赵国之事,也想染指和氏璧?
楚姜窈悄悄叫过小盾牌,与他低头耳语一番,小盾牌将信将疑地说,“非得支开我么?还是、你故意想跟虞帅哥单独一块儿?”
“怎么会呢?你也是帅哥啊!”
见小令箭一脸诚恳地说了这句他早就想听到的话,小盾牌忍不住一扭头、浅笑了起来,点点头说,“好吧,那我听你的。”
小令箭又说,“公子市或许想要利用这和氏璧兴风作浪,宣太后只怕也不知情。若公子市得了玉璧,赵王定然以为是大王强抢玉璧、又不愿换赠城池,只怕会发兵攻秦。大王不但得不到和氏璧,反而自吞黄莲。”
“我明白。公子市觊觎王位已久,璧既已入秦,如若遗失,无论落入谁手,都是秦王负曲。”小盾牌沉着地拍了拍她肩膀,说,“我会见机行事,你也多小心。”
小盾牌转身离开,隐入丛林,小令箭便也赶紧回去收拾了东西,与虞从舟一起继续向东而行。
离开茔城半日,两人肚中正饿,楚姜窈看见小镇街头有热气腾腾的馒头铺,那香气向她扑来,她忍不住就要奔过去,却被虞从舟一把扣住手腕。他故意严肃着脸说,“我们去吃面条。”
“我想吃馒头,好不好?”姜窈摇晃着小脑袋说。
“为何只吃馒头?前面就有家面馆。”
“手边就有个馒头铺嘛!”
“我喜欢吃面条。”虞从舟执拗起来不管不顾,偏想让她尝些别的。
“但我喜欢吃馒头。”姜窈也学起他的表情,皱着眉、抿着嘴。
从舟叹了口气,松了表情说,“好吧,”他有点无奈,“那就去吃面吧。”
姜窈得意地点点头说了声“好”,说完才发现不对,赶紧改成摇头,但已经来不及了,手被从舟紧紧扣着往那面馆拖去。从舟偏偏还得意笑说,“长幼有序,你自然该听我的!”
楚姜窈心想,妈呀,这什么人啊,长得是大美人,演得是大好人,做得是大恶人。她满眼留恋地回头又眺望了一眼那冒着热气的馒头铺。
但进了面馆,她见从舟吃得甚香,不由肠中辘辘,便也跟着吃了几口,发现味道的确不错,虽没有馒头的清香,但也有些说不清的味道。
只是吃完正欲离开,她忽然觉得头沉沉重重,身体酸痛无力,还没来得及说声“有毒”,就已经倒在地上,脑海中最后闪过一念,
“居然这么快就着了道… ”
两人齐齐中毒,虞从舟体质强,比姜窈早醒许多。他睁眼打量四周,他们被关在一间地牢里,两人双手都被拴在木柱上。从舟心忖,他们潜出咸阳之事竟走漏了风声、被秦王知晓?但为何一路行过那许多城关都未被阻拦?秦王究竟演得是哪出?
“这么快醒了?甚好,省得我久等!”他听见有人阴笑着踱进昏暗的牢室,随即有士卒点亮了火把。他看清来人,一身玄衣,脸上三分贵气、三分纨绔、还有四分阴毒。
从舟没有见过这人,此刻心中仍摸不出头绪。
那玄衣人将手指指甲一一掠过挂成一排的各式刑具,金属与骨质相触、发出叮叮之声。他依然阴沉地笑着说,
“若不想受刑受苦,只须交出和氏璧。”
“休想。” 虞从舟冷冷地将那人的目光反盯回去。
☆、难辞其咎
那玄衣人看见他栗色的瞳眸,忽然有点发怔。他走近几步,一瞬不瞬地盯着虞从舟的双眼,仿佛自言自语般说,“这容貌,倒有些像… ”
这样的联想让他觉得有些冷,他立刻一闭眼,甩去一些回忆,心绪重又回到和氏璧上,
“怎么,当真不想说?!”
他身边一名军士低头抱拳道,“在下搜过他全身,的确没有和氏璧。”
“我得来的消息不会错。璧已不在蔺相如身上,定是被这小子藏匿在何处!”玄衣人冷冷转过身,扯下一根长鞭,悠然自得般、将鞭子在盐水中涤过。他回过头、看见虞从舟神色桀骜、眼波微横、反而有些挑战之意,心中不由恼怒,突然将鞭子抛给他身边那军士,厉声道,“敬酒不吃吃罚酒!”
军士接过鞭,猛然手起鞭落,用力劲道,那鞭深深刻入虞从舟胸膛,血水立时溢出,与鞭上盐水交混一起,一阵煞痛、漫入他心肺,煞得他浑身僵尅。
一息尚未提上,那军士下一鞭又已挥到,虞从舟紧闭双眼,屏息苦捱。但一鞭一鞭不断砸来,皮开肉绽之下,各道伤口相叠相扯,刺心之痛令他脑中嗡嗡作响,喉间似被尖锥扎破、腥血翻涌。
数十鞭后,那军士暂收了手,虞从舟终于破出一口气,疾喘不迭,气息带着喉中血痰,在他胸间上下磨梭。
盐水仍在他血脉中蔓延噬咬,虞从舟无力睁眼,只听玄衣人说,“若你还是不说… 哼,这几鞭只是开始!”
虞从舟努力睁开眼,发觉自己视线分外模糊,但他仍旧狠狠睨向玄衣人的方向,不肯输了气势。和氏璧不在他身上,因而他并不担心。
但朦胧间,他隐约看见、另一边柱上被拴住的楚姜窈仍在昏厥之中。他心中霎时漫起忧虑,若一直与这玄衣人耗下去,只怕他们也会对姜窈用刑,他自己虽然尚能强撑,但姜窈嫩皮薄肤的女孩子家,怎么受得了各种刑罚。他心乱如焚,只盼她再多昏迷一会儿。
但偏偏越担心的事来得越快。楚姜窈居然在这时、“嗯啊”了两声,轻轻摇了摇头,手腕挣扎了一番,似乎觉得被绑着很不舒服。虞从舟心中暗急,“这小祖宗竟真的要醒了!”
玄衣人也听到她的动静,吩咐那军士道,“这丫头身上也搜一搜!”
军士诺下,扔开鞭子,向楚姜窈走去。她昏昏沉沉刚睁开眼,就看见那么个凶神恶煞的人立于面前,不禁浑身一抖,顿时全醒了。
而那军士二话不说、便在她身上粗鲁地乱摸乱扯,甚至撕开了她的几片衣布,他粗糙的手指狠狠擦过她的胸前腰间,从头到脚的掳索过去。
楚姜窈又惊又屈辱,但此时人为刀俎,她只得闭上眼忍住,浑身微微僵冷。
“别碰她!”她忽然听见虞从舟充满怒意的声音,循声看去,竟见虞从舟也被绑缚在另一边柱上,身上血肉模糊,显然受了鞭笞之刑。她忽感心神焦灼,呼吸微窒,脑中飞速地想着如何方让他脱困。
她主意稍定,顿时便哭得像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