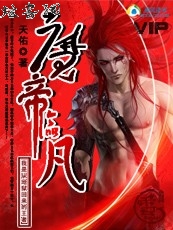困兽 作者:诸葛喧之-第8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涌在喉头的只有血,我呛咳着,看着她跑远逐渐不见,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知道自己没有太多时间了,我侧过头,脸颊贴着冰冷的石碑,闭上眼睛仿佛听见了他的脚步声,隔着五年生死茫茫,在清冷的夜幕里,孤寂地回响。
“小霖……”我轻声喃喃,眼泪润湿了深黑的睫毛,无声无息地滚落下脸颊,我哽咽着笑了起来,用满是鲜血的手,颤抖着抚上碑身,“小霖……”
我们终于可以在一起了,不是吗?
就像曾经许诺过的那样。
喧闹的烟火此起彼伏,忽然想起少年时我带着他去江边放烟花,江的那一头是人声鼎沸的烟花大会,嘭然炸裂的各式烟花壮观竞艳,而江的这头我和他手牵着手,金鱼花火咝咝燃烧着落下点点橙色。
在意识沉没的最后,我隐约是看见他从墓园深处走了出来,和以前一样的清秀消瘦,我挣扎着想要看得再清楚一点,想要再听一听他的声音,然而,所有的感官都无法阻止地渐渐迟钝……
你是来接我的吗,小霖。
你是来接我……到那个有你的世界里去吗?
我望着他越来越模糊的身影,背后是我们的墓碑是最后的归宿。隐约是想到那句墓志铭,我微微笑了起来,一语成谶了啊。
我们终于可以在一起,一分一秒都不少了。
曾经听过一种传说,人死的时候,就好像穿过一条长长的隧道,隧道周围会回放这辈子的林林总总,当看到自己出生的那一幕,生命也就真的结束了。
我想这样也是好的,至少我还能看一次他微笑的样子,至少,当我路过曾经的青春年少时,我还能再听他说一次:“程维,我喜欢你。”
作者有话要说:祝愿排在预算主角内,目前的预算是这样的:
姐夫——沈蓝——祝愿。
困兽应该不会有番外,不过很显然祝愿主角的文里会出现程先生和祝先生未来的生活记录,预算祝愿将有一只黑道忠犬攻和一只警察渣攻,程先生你杯具了,你亲手调教的儿子成了一只受……
下一章最终章,各位妹子悠着点,yoooo!!
118
118、大结局 。。。
我站在墓碑前,怔怔地望着那个面色苍白的男人。他的左腹部中了子弹,虽然手一直捂在伤口处,可是血仍然流淌不止。
五年了,这是我第一次站在他的面前,第一次那么近地看着他。可是他快要死了。
墓园的夜晚漆黑孤寂,守墓人是个年过半百的男人,嗜酒懒惰,并不常来园区巡视。这么多年来,我和程维一样了解这片墓园,只不过他是因为天天都会来看望已经死了的我,而我则躲在远处,悄悄看着形单影只的他。
程维以为我在那场车祸中丧命,其实并不是这样。这是周熙晨的算盘,甚至一开始把我也一并蒙在了鼓里。周熙晨是个很可怕的人,他做事完全不按常理出牌,而且习惯铤而走险。
我这么说并不是毫无依据的,因为我深有领会,那场车祸就是他一手策划好的,我曾问过周熙晨,如果那天真的把我给撞死了,你打算怎么办。周熙晨的回答很无所谓,那就直接送火葬场烧了,反正你这样,活着也得不到解脱。
程维不懂医学,而我那时候也的确是受了较重的伤,有周熙晨这个医生在旁边做手脚,很容易就可以制造出我已经不治身亡的假象。包括后来火化的时候,推我进去的人是程维,但是之后接手火化是在后面的房间里,和丧仪人员沟通之后掉包并不是难事。周熙晨有足够的本事做到这点,他在火葬场里和我彻彻底底地说明了原委,并且告诉我,当初之所以看到程维掐着婴儿的脖子,并不是程维想要害死孩子,而是他之前让护士告诉程维,孩子的情况有些不太对劲,当程维进去查看的时候,便见到了他事先留在婴儿脖子上的浅浅划痕。这些事不能在事先和我明说,因为如果我知道了真相,势必无法把戏码演下去,程维肯定能看出破绽。然后他告诉我,若是我真的下定决心要离开程维,那么就是现在,带着婴儿,立刻离开这座城市,永远也不要回来。
可是他千算万算,算错了两点,第一,我并没有机会把孩子带走,程维一直都让管家昼夜看护着他,并且在参加完丧礼的不久之后,就办了领养手续,决心把他养大。
第二,我不知道究竟是因为程维,还是因为孩子,或许两者兼而有之,我无法独自离开T城,而是留了下来,五年了,从祝愿被程维抱在怀里连话都不会说,到现在他总是顽劣不堪地欺负小朋友,我一直都在偷偷地看着他们,从未走远。
我看着程维一天天在墓园里傻傻地和“我”说话,五年来除了小愿生病,他天天都会来这里看我,从未间断。有时我看着程维孑然孤独的背影,也会忍不住想,若是当初周熙晨没有把事情做的那么绝,那该多好呢。可是周熙晨这样做到底有他的理由,那时候他答应帮我逃离,可是他觉得如果不让程维认为我死了,那么藕断丝连,即使我逃到别的城市或者别的国家,保不准哪一天还是会遇到生命里出现的他。
可是现在我依旧逃不过他,看到吴添乐开枪的时候,我整个人都是懵的,或许是程维一直都显得那么强大,从很早之前就让我有一种他不会垮掉不会生病甚至不会死亡的错觉。
然而子弹就真的打入了他的左腹,他并不如别人口耳相传的那样,是永远无法打到的,立在那个黑暗社会之巅的神。
他也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会难过会疲惫,会因为抽了太多的烟而不住咳嗽,会因为养大的孩子不懂事而皱眉苦恼。
然后,他也是会死的。
我难以言述后来带着他去医院的那段经历,我的脑海几乎是空白的,我抬起他的一条胳膊,将他架了起来,他已经没有了意识,全身的重量都加在了我的肩头。
他的身子还是暖的,血流下来浸透了他的衣服,也浸湿了我的。
他像十年前二十年前一样高大,身上仍然有着那幽淡的,只有爱人才分辨的出的味道。那味道和十年前略微有些不同,没有了淡淡的烟草味。
他已经不抽烟了,从把祝愿带回家的那天起。
远处的烟火声此起彼伏,我朦胧地听着那些喧嚣和欢笑,烟火大会上明快的暖色调和眼前的黑暗让这一切都荒谬地像一场幻境,人们的幸福离我们那么近,可是却又仿佛咫尺天涯。
我们在街头拦车,可是没有出租司机愿意在晚上接载这样可疑的客人,我不知道时间过了多久,似乎每一秒都像一年般漫长。后来终于有一辆警车停了下来,车上下来两个年轻的警官,其中一个看了程维的伤势,就让我们上了车,一路打亮了警灯送我们去了最近的一家医院。
一路上我一直抱着他,我说不出任何话来,他靠在我的膝头安静地像个孩子,我怔怔凝视着他,他的嘴唇薄薄的,全无血色。但却是带着笑意的。
那种笑意很淡很淡,只是嘴角浅浅的上扬,仿佛解脱。
我听说当一个人在弥留之际或许会看到一些虚渺的幻影,我不知道他在意识沉沦之前最后看到的是什么,他靠着墓碑慢慢滑坐下来的时候很平静,我想那时候他或许是看到了幸福的错觉。
医院递来一张手术同意书,我的手在表格上停顿了几秒钟,最终是在“与患者关系”那一栏,填上了家属二字。
之后就是漫长的等待,程维在抢救室内,我在抢救室外。我怔怔望着掌心里他的血液,没有掉下眼泪,却僵冷得厉害。
直到一只手拍了我的肩膀,我才稍微回过神来,抬头看去是送我们到医院来的其中一个警官,他清秀的眉头微微皱着,轻声问:“你还好吗?”
我喉咙发紧,说不出话来,只能僵凝地点了点头。
和这个警官一起的,还有另一个眼角吊梢的警官,狐狸眼警官看了我一眼,语气并不是很和善:“你们是怎么搞的?大晚上会出现在城北公墓那块地方,其中一个还中了枪伤。”
我没有答话,另一个警官就对他道:“算了吧,李旭,你少说几句。”
“我只是问一问而已,又不会真的去管。”狐狸眼耸了耸肩,“我可不想在出差途中还给自己拦一些别的活儿,就算是杀人案都懒得去理睬,反正过两天就得回杭州了,干什么还要给T城警界做贡献。”
那个清秀的警官抿了抿嘴唇,问我:“你还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吗?”
我摇了摇头。他便叹了口气,留了个电话给我:“那如果有事,就再和我联系吧,我姓安。”
他本来是要走了,可是走了两步,又像忽然想起什么似的,折返回来:“你带够了钱吗?不然我借你?”
同行的狐狸眼气得直戳他的脑袋:“我靠,你和他很熟啊,我们送人到医院已经仁至义尽了好不好,你是警察,又不是冤大头。”
我也有些意外,摇头拒绝了他的好意,安警官和狐狸眼走出很远之后,我还听到狐狸眼在那边和他嚷嚷,让他不要做滥好人什么的。
滥好人么?
我一个人静静坐在抢救室外的长椅上,抢救指示灯的红光幽暗地映在地面。回想当初程维又何尝不是个滥好人,竟然会为了把钱给素不相识的小乞丐,自己一个星期都没有好好吃过一顿早饭。
其实人都是会变的,如今已到不惑之年,回头去看一看十年前的自己,二十年前的自己,很多事情就好像在做梦一样,无论如何也想不通自己是如何从一个锋芒毕露的纨绔子,变得像现在一样软弱,隐忍,畏首畏尾。
而程维呢,二十年的时光也让他渐渐迷失了自己的信念,迷失了自己的本心。我知道他曾经是那么正直坚强,就好像刚才那个年轻的警官一样,愿意伸出手拉一把素未平生的我。
可是我们终究都被现实打磨了棱角,戴上了面具,变成了一个和最初的自己相去甚远的角色。
其实又何止是我们,在这个物欲横流的钢铁之城里,很多人都是一样的,为了生存,不得不委曲求全,不得不削去自己的枝节。
曾经张狂不羁的人在碰的头破血流之后,学会了隐忍避让,察言观色。曾经口直心快的人在被人恶意中伤之后,学会了缄默不语,虚与委蛇。曾经诚实善良的人在被背叛诬陷之后,学会了信口雌黄,造谣生非。
那些人都亲手杀了最初的自己,我和程维,我们也是一样的。我是从上流社会走到滩涂地上的落魄子弟,二十年前的我,何曾想到自己有朝一日会变成自己最不齿的样子,唯唯诺诺,犹犹豫豫,在颠沛流离的生活中苟延残喘。而程维也是一样的,我知道他曾经最恨的就是那种草菅人命,快意恩仇的黑道兄弟,可他自己却与初衷背道而驰了。
连自己的本心都无法保护的人,是最可悲的。
然而我们最终都走上了这条道路。
为了在这座弱肉强食的森林里活下去。
手术是在第二天黎明时分才结束的,那时候熙微的初阳从云层后面微微吐露出柔软的辉煌来,就好像每一个不杳人事的少年,对未来抱着那样美好而大胆的幻想。
万枝金箭刺破黑暗,从窗口射进来的时候,我看到手术室的灯熄灭了,被医生推出来的他安静地合着眼睛,躺在病床上,露在外面的手背正戳着点滴。
我上前几步,喉咙里却发不出声音来。整夜未眠的大夫摘了口罩,重重舒了口气,疲惫地按了按眼廓,看到我走过来,只是非常倦怠地摆了摆手,疲乏地对我说了句:“没事的……”
我去重症监护室看望程维的时候,他还没有醒,躺在床上安安静静的模样很像最乖巧的孩子。
我在他床边坐了下来,他的脸色苍白,神情也说不出的憔悴。浓深的睫帘垂落着,五官端正俊秀,鼻梁也很英挺。
可他毕竟是不惑之年的人了。
我能看见他鬓中已有白发。
我抬起手,在半空凝顿了一会儿,最后终是轻轻触碰上他消瘦的脸庞,手指描摹过和记忆里无甚差别的五官,落在他的耳鬓时停住。
“程维……”
我轻声唤着他的名字,比之前任何一次都要认真地凝视着他的面容,他在我心里还是和我们第一次见面时同样年轻的,那些颠沛流离的二十年,仿佛都只停留在了鬓间那几根白发上,是微不足道的。
我没有哭也没有难过,因为现在我能陪在他身边了,我能守着他等着他,当他醒过来的时候,第一个看到的人会是我,没有别人。
这种幸福来的太迟,究竟是不是幸福,我已不能断夺。我这样的人,并不知道幸福是什么,可是当程维血流不止地倒在墓碑上时,我清楚,若是程维写下的那段墓志铭真的一语成谶,那么一定是不幸的。
我们都还活着,虽然很多事情都已不再如往昔,很多故事都不再能回到从前,但是至少我们还活着,我还在他身边。
他用了五年来祭奠我,每一天每一天,春生秋华,万物生发,他用他的人生给我读了一本很长很长的童话故事,在他以为我已经死去的时候也仍然那么固执地坚持,他已经成了是我的习惯,就像我是他的习惯那样。
狐狸对小王子说:“请你驯服我吧。”然后呢,狐狸对小王子又说:“你得非常非常有耐心。开始的时候,你在草地上,坐得离我远一点儿,像这样。我用眼角瞅一瞅你,而你什么都别说。言语是误会的祸根。然而,每天,你都能坐得稍近一些……”
“你最好是在同一时间过来,比如说,你在下午四点钟来,我从三点钟起就会感到幸福。到四点的时候,我会坐立不安,从而我将发现幸福的代价。要是你随便什么时候来,我将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该做心理准备……要形成规律。”
这些话我已经熟稔于胸,是你读给我听的。
你每一天都是六点多来到墓园的,真狡猾啊,程维,你很清楚应该怎样驯服别人,哪怕是一只遍体鳞伤,无家可归的困兽。
我闭上眼睛,轻轻将额头抵在了他的额上,很多话已经不用讲出口,从年少轻狂的少年时代到如今的不惑之年,他已不仅仅是我的爱人,二十年,他逐渐融合进了我的血肉,如同我心腔中不断跳跃的那个器官,爱恨欢伤,等同身受。
我在他床边坐了下来,窗外阳光正好,摩挲的花树投下细碎朦胧的斑驳光影,现在我要做的很简单,就是等他醒过来。如今我们都已从过去的漩涡中脱身了,我不再是他有着许许多多顾忌的落魄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