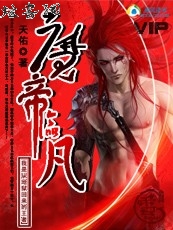风骨 作者:小秦子-第1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一呆,掂量著手心鸡食似半点小钱,想起失去的六匹马,仰後就倒,昏了在地。
旁边的人即时围绕上去,有人揉他的人中穴,喊的喊,推的推,理智些的便赶去报官府了。该是这马贩不能受这无妄之灾,有位富家少爷听见这边喧哗,他牵著马过来一看,竟是有人昏死了,忙道:“各位乡亲让一让,我略懂医术,让我给老丈人瞧瞧。”众人闻言,四散而开,给这少爷挪地儿。你道这富家少爷乃是何人?却是梧桐山庄的叶三爷,叶近秋。只因管事陈平给四弟写信,托他来接回小六,四弟妻子待产,他便替四弟来了,不料来得凑巧,刚进凤凰就撞上了劫匪盗马的事件。
叶近秋掏了一个陶瓷罐儿,放到马贩的鼻下,这药物特是有效,不多时老丈人便幽幽睁目,旁人喜道:“醒了!醒了!果真好医术!”老丈初醒,老怀感伤,叹著气又要哭了,叶近秋问及缘故,方知是一夥强盗同一个小和尚劫走了他六匹马,怒道:“世风日下,如此猖獗,官府若是管他们不得,我叶家山庄也管不得吗?!”将老丈扶起,从袖中取出了锭金子给他,安慰道:“老丈人先将这钱取去,那六匹马便当我向你买了,我自会去寻它们回来。”老丈千恩万谢,捻著袖子擦了眼泪,向叶近秋细述六马的马色,又道:“我家养的马,马蹄铁上均刻有平安二字。”
叶近秋心中记住了,问知了强盗的样貌後与老丈告别,托了热心街坊送他归家,自己也往五弟的酒肆前行。他岂能知道他那五弟的情况可比老丈严重多了,一会儿见了,保准吓散了他的魂魄去。
卫胤x闻于野萌图
乐乐的作品,画的是敬帝和闻於野!!!
我萌得满地打滚!!!
我打滚打滚!!
抱住啃一大口!!
'img'wyxwyymt_1。jpg'img'
24
24
且说叶近秋离了破落店去寻他五弟,记忆中凤归来是清雅之所,这番到此却完全颠覆了从前印象。厅间吵吵嚷嚷的,许多年轻男子三五成堆地吵著不知何些话柄,争的是顶上生烟,店里却是一桌吃酒论诗的都无有。叶近秋甚是困惑了,把缰绳牢牢系在门口的木柱上,他进了门也没遇著有个活人前来招呼,只得自己去找,结果竟在柜台後寻到了小弟,正支著下巴在发愣。“六儿,你在这作甚?”叶近秋挨近去敲了敲柜面,顾了顾乱糟糟的四周,怪道:“这凤归来怎成这样儿了?你五哥呢?扔你自己在这,三哥不饶他。”
叶惊鸿乌溜溜的眼珠子转了几转,似在拉回分散的神智,好不容易他对上了叶三爷的面容,看真了眼前的人,马上就是把嘴巴一扁,说:“三哥,我想你,三哥,三哥!”他只把三哥这二字乱叫,叫越是娇气,小拳头捏紧,脸儿高高抬起,放声大哭,并控诉道:“三哥,你还是带我回去吧,三哥,我不和五哥待了!没了媳妇了不起麽,他多了不起吗!天天儿乱骂人,仆人都被骂走了,饭都快吃不上了!”叶近秋大为吃惊,听得不是很分明,他心想什麽事把这骄纵的小鬼闹成这样,慌忙探臂将他从柜台後捞出来,抱到怀里哄了哄:“别又哭又骂的,谁家能听的明白。你的马尿暂且收一收,把事和三哥说说,老五怎麽了?”叶惊鸿哭的都打嗝了,三哥的出现给他极大的安全感,他掀起衣襟蹭了几把鼻涕,抽抽搭搭地道:“说到底,是五哥自取的。”开口先贬一句,再将叶惊澜要强娶反将人家逼逃的事说了,最後还哼了一哼表达不屑。
叶近秋听毕之後,神情严肃了许多,想道:“老五向来自把自为,现在真是愈见过分了,还有点分寸没有?虽说婚姻乃是他的,可这怎麽也得同家里商量,几时轮到他自家做主?幸的这姑娘落了跑,倘若娶个不三不四的回来,那不烦死个人。”他正自思量,陈平也踏入了店门,这连他都消瘦了些许。陈平刚从守城役处回来,甫进门便将浑水摸鱼的人全轰了出去,大门关的严实,复转身定睛一看,却是三爷到了,不由抢前几步,大喜道:“三爷,怎是您来了?四爷不得空闲?”叶近秋凉生生地瞟了他几眼,嗔道:“我再不来还了得,老五娶妻你怎也不通一声?由著他目无尊长吗?”
陈平摸了摸鼻子,打著哈哈道:“五爷的性子您也知道,他说了要自己做主,我哪敢拦他。”叶近秋不以为然地冷哼,片刻,很是惊诧地又问:“说起来也怪了,老五相中的是谁家姑娘?莫非天姿国色又富甲一方,好得连咱们老五都看不上了?”陈平还没赶上答话,叶惊鸿便把话茬揽过去了,咋呼著说:“谁同你说过是姑娘了?嫂子才不是姑娘,他是男的!五哥可爱惨他了,他也没甚银子,就只在西区种大米呢。”说著,舌头伸出舔了嘴唇,像是回味无穷,“他种的米饭老香了,好吃!”
这小东西口没遮拦的,陈平神色微变,气氛一下子就凝固了,他心虚地低下头,可骤然变得锐利的视线还是投将过来,紧跟著是叶近秋咬牙切齿地问话:“陈管家,这是怎麽回事?一五一十给我说了!”陈平的额头跌落两滴汗珠,他明白是躲避不了的了,只好去倒了两杯茶水,几人在桌边坐好,再将一切始末都拆给他听,全不遗漏,还说:“武夫人是不愿儿子和五爷成婚的,所以才拉著武年逃了,连房子也卖了,落得无家可归。”叶近秋是明辨是非之人,从陈平的诉述也知是自己弟弟不对,他暗道:“还是多亏了武年逃跑,不然叶家都成笑柄了,有机会见著他们母子要好好道歉才行,赔偿是免不了的,万望他不要当真来与老五成婚。至於老五这畜生,他得抓起来扒皮!”这般想定,他端起茶杯要喝,发现早让叶惊鸿喝空了,只得又放下。叶惊鸿蹲在椅上,眼巴巴地看他们,有话想说又不敢说,急得直乱抓耳朵,捧住脸儿挤来挤去。
陈平讲得口渴,正待喝些茶,不意捕获叶三爷暗含怒意的反应,想起了楼上那位颓靡不振的人,又是长叹一气,提醒道:“三爷,五爷是真喜欢武年,现在武年不见了,他本来就很伤心了,您等会儿可千万别骂他。我怕他会去寻死。”叶近秋听了这话,立即瞪眼过去:“瞎说,老五至於糊涂成这样?不过跑了穷巴巴的庄稼汉,有多了不起,真是个好笑!”他的语气中诸多嘲讽,陈平不服气,他张口欲要辩驳,然而字眼到了舌尖又给咽了,略作思忖,只无所谓地甩了甩手,笑眯眯地道:“那您就去找五爷吧,他在楼上呢。”叶近秋斜睨了他两眼,似觉好笑地摇摇头,起身便要往二楼而去,这时叶惊鸿却慌忙拉住他的衣袖,脸蛋憋得红扑扑的,突然哎呀了一声,道:“三哥,反正你来了,五哥不能把我怎样,那我就把事说了吧!我知道嫂子干嘛不要五哥!”便豁出去了,把与武年在马车上的对话抖落干净了,说完了就任性地把脸捂住,在椅子上扭起屁股来,“我原先就想给五哥一点点教训,故意不和他说,我又不知道嫂子会走掉……”
陈平怔住了,片刻後他倏地蹦起来,二目睁圆了,气得猛捶自己的胸口,道:“小祖宗,你这不是害人吗?你也不是奶娃子了,不晓得事有轻重?你早和你五哥说,他就会去哄武年,哄了武年,他娘逼了武年也不会走,於是哪还有现在的事?你知我几天没吃上顿好饭了,爷爷!”这通指责铺天盖地的,叶惊鸿虽未有十岁,脸面也是放不下去,他索性伸横了脖子,回呛道:“呸,甭叫我爷,我没到年纪!你还赖我头上了,你以为我这些天好过呀?明是五哥自己造的孽,与我何干了?”两人当即唇枪舌战,斗得叮咚响,叶近秋懒的去理睬,他想两人是故意在他面前夸大其词,老五怎会为了平凡无奇的男人倾付真情,然而当他信步上了二楼,亲身触到了那股子阴郁的气息,才知道事情真不小了。
这大热天时,一扇窗都没有打开,室内流溢著粘糊糊的湿气。矮桌边,有个相貌落拓的男人端坐著,他手边摆著一壶酒,也没做什麽,仅仅是对著墙壁发呆罢了。叶近秋避开地上倒落的酒壶,来到了叶惊澜的对面,将他全身审视了一番,皱眉道:“老五,你这是干什麽?”叶惊澜缓慢地掀起眼帘,死气沈沈的眸光投向了他,淡淡道:“我什麽干什麽了?”说话时酒味儿重得惊人,面上颜色倒是平常。叶近秋心下有几分不祥了,他捏细了心思,用玩笑的语气说:“这武年走了便走了,你何至於为他闹成这样?哥哥还不乐意你和男的在一块呢,他走了更好,你自家多自在呀……”他这言辞也不知是在开解还是落井下石,还没等他道长了,叶惊澜便有动作了,只见他拖著腿爬到了窗边,把窗叶一推往楼下就要翻去寻死,叶近秋登时吓出一身冷汗,扑去抱住他的腰给拖了回来,骂道:“疯了你,跳什麽楼?再说这二楼也摔不死你,你还想丢人吗!”
叶惊澜低下头,逸出古怪的笑声,道:“三哥,你才疯了,我几时跳楼了?从你进来,我就没动过。”叶近秋发觉到怪异之处了,他扳过弟弟瘦了大圈的身子,焦急道:“你怎麽没动了?你刚刚坐在桌边的!”叶惊澜眼底浮现少许怀疑,认真地盯住了他哥哥,半晌,他抬手掩住了脸庞,口中咯咯乱笑,非常同情地道:“三哥你真疯了,我一直坐在这,我根本没动过。”
连自己的手脚都能忘记,这家夥明显是人事不清了,叶近秋这才开始著慌,从没见过五弟这般失魂落魄,他几乎要落下几滴伤心泪,原先的反对心理瞬间给抛到爪哇国了,连忙轻拍了叶惊澜的脸颊几下,道:“老五,走,三哥带你去梳洗,醒醒脑子。”说著想架他起来,谁知叶惊澜不肯,反倒直接赖到了地上,特别傲慢地道:“我不用你,我要武子来伺候我。”叶近秋惟恐刺激了他,更千万不能勉强了他,於是琢磨了些时,方才小心应道:“老五,莫若你先睡会儿,我去把武年找回来,你可不能乱动。”叶惊澜捡到爱听的话听了,於是朝墙角缩进去,墙灰蹭在他脸上,他也不嫌脏,高高兴兴地把眼睛闭了,嘟哝道:“唉,那我听你的,我睡了。一会儿你让武子来叫我。”不多时,已然沈沈睡去,似乎梦中还委屈不已地哽咽了几声,再又喊了几句武子。
让原先斯文得意的人如此颓废,武年真不是个东西,居然能抛下老五跑了,始乱终弃!这婚事不满意可以谈到满意,母亲反对也可以求到她允许,叶家山庄又不是谈不起,怎麽能弃婚私逃?大男人弃婚,简直太无廉耻了,非得把他逮回来不可。叶近秋愈想愈气,极其痛心地沈道:“五弟,五弟,你真是傻。”见了叶惊澜悲惨的现状,他哪还记得刚才还为武年的逃跑窃喜过,把窗户全都牢固扣紧,三步作俩奔楼下厅堂寻陈平商量追捕对策了。
陈平和叶惊鸿吵不出结果,绕完反把火气给吵没了,直至看见叶近秋去了折回,便转向了他,装模作样地奉承道:“三爷回来了,想必把五爷给说服了吧?也是,为了一个穷庄稼汉劳师动众的,实在是个好笑。”叶近秋抓起杯子来掷他,生气道:“笑话,那不便宜了他?我们叶家的婚事岂由他说逃就逃的?”陈平堪堪闪过攻击,取笑道:“您早间可不是这麽说的。”叶近秋的面色一沈,喝道:“你有这闲工夫,还不如去发了信儿,召集附近的庄人同去找,他便是插翅也难飞!”陈平知晓叶近秋会操持此事,动用了叶家庄的势力便大不同了,他放心很多,衔命去了。
花有开放日,人有行运时,恰逢是武年他们今日出城门,山庄的探子不到半个时辰便得以复命,武年母子同一位少年望东升城的方向。马车,人数,衣色,车程俱都调查明白。陈平和叶近秋的意见相同,均是决定让庄人先跟紧他们,等到叶惊澜休息充足了,他们再前去接应。人终归是叶惊澜的,得由他自行去接,免得又生事端。这中间的耽搁,武年他们那处也有了惊心之事发生。
叶惊澜x武年萌图
乐乐画的,哎,我啥都不说了,简直传神的要命,我心目中的武子和叶五就是这样的。
萌得我泪流满面……
''img'yjlxwnmt_2。jpg'img'
25
25
关慎争驾车赶马,无非一路颠簸,从路程预计会在第三日的午後时分抵达了幽魂林。这幽魂林中载满了槐树与榕树,据说林间深处有一棵百年老榕栖满了女鬼,她们每日每夜在树杆上啼哭,久而久之便有了幽魂林三字作为名号。关慎争来时并未经过幽魂林,他是绕了远路去翻过观景山,如今驾的乃是马车带的又是累赘,前去翻山便不大合适了。至於所谓的鬼怪神说,他听来概是无稽之谈。
在离幽魂林有四里地的位置,有一个小村庄,名叫杏花村。村口有一间篱笆围起的小茅舍,庭院内摆著三四张桌子,屋前插著悬挂酒字布旗的竹竿,收拾得挺是干净,兼有鸟叫蝉鸣为伴,值得玩赏。当下正是饭後的点儿,主人家是位老者,在草棚下支住脑袋打著瞌睡,呼啦啦的鼻鼾声传得老远。关慎争驾至村口,动作熟练地勒住了马匹,扬手扣了扣马车前窗,道:“用过午饭再走,天黑前出幽魂林。”也不等他们言语,已率先跃下马车,径直向店家走去。武夫人先从车里出来,她仍是神采奕奕,倒是尾随她的武年模样不太对,眉间纠缠著化不了的疲惫。
他们三人进了门前,看门的黄狗冲老汉努力吠叫,老汉由此惊醒,揉揉眼睛,但见是有三位客官光临,他急忙在肩上披条毛巾,一边提起了铁茶壶,笑呵呵地迎将上去:“客官,吃茶还是用饭?” 关慎争挑了日晒不到的位子坐下,武年扶住母亲也入了座,他无精打采地搭著眼皮子,对著老者问道:“用饭,你这儿有甚好吃的?”老汉欣喜地给他们翻杯倒茶水,同时推荐了六道荤和素,又问了酒,伺候停当便进屋交代媳妇儿备饭菜。武夫人端详著儿子的神态,略微担忧地握住他的手背,问:“年儿,你还犯恶心麽?”关慎争的视线掠过他的倦容,半声不吭地独自喝茶。武年整个人都不对劲,偏偏又说不上来,他极是无奈地抚著额头,对上了母亲关切的目光,只好勉强地笑了笑,安抚道:“好多了,没事了。”武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