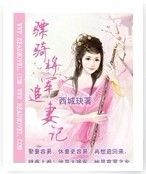朕与将军解战袍-第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只是,一个首辅大臣,为何需要在皇帝身边安插眼线?
回想起苏逸问她可知上一任御前侍卫长是如何而终的,沈秋心有所感,只觉得这宫中暗涌,似乎远没有表面看来那么简单。
而不知从何时起,似乎已被卷入其中。
*****
自打上次在朝上大闹了一回,段云亭似乎安分了些日子。不过,这种安分只是相对而言的。
该赏的歌舞照样赏,该玩的游戏照玩,该打理的政务也是照样堆着不动。
这日沈秋方进御书房,一眼便见段云亭靠在软榻上,手里翻着一卷书。
不用怀疑,决计不会是正经书。
“沈爱卿你可算是来了!来来来,快过来帮帮苏爱卿,替朕把这堆奏折批了!老堆在这儿占地方!”见她来了,段云亭笑眯眯地冲她招招手,又伸手指了指桌案上的一大摞东西。
沈秋抬眼,这才发现苏逸已然站在房中了。二人对视了一眼,沈秋无奈耸肩,苏逸倒是一副司空见惯的样子,已然举步走到桌案边,拿起奏折。
沈秋没办法,也只能跟了上去。粗略翻看了一下,见所奏皆非大事,便也懒得细看,就着段云亭的意思,刷刷刷地朱批着“准”字。
段云亭一见二人已经开工,便十分满意地继续沉浸在书海之中。
“陛下,”室内沉默了一阵,忽然苏逸开了口。沈秋循声望去,但见他面色之中隐隐有些肃然。
段云亭亦是从书中抬了眼,道:“何事?”
苏逸抬眼同他对视,许久后慢慢道:“摄政王上了奏折,下月初三……回京。”
听闻此言的刹那,沈秋注意到段云亭的面色,竟是微微的变了。
作者有话要说:2012。4。8,修。
☆、第五章
【第五章】
那眼中一闪而过的深沉,一瞬间让他几乎判若两人。然而也只有一瞬间而已,很快段云亭面上的笑容恢复了几分,换做一副若无其事的神情,道:“皇叔可曾说过为何而来?”
“据折子里说,乃是入京探望其长女。”
“看来朕这皇叔对朕倒并不是太惦念,倒是朕多虑了。”段云亭默然许久,笑道,“他此番入京,所带人马多少?”
苏逸看了一眼奏折,道:“千余人。”
段云亭闻言沉默。
“陛下……”苏逸欲言又止,然而瞥了一眼沈秋,却终究没有继续说下去。
段云亭放下手中书卷,站起身来,背身望向窗外,半晌后才道:“罢了,你二人且退下吧。”他声音格外低沉,便有如那夜谷中小屋里,沈秋曾听到的一般。
觉出几分异样,沈秋意欲说什么,而苏逸递给他一个眼色,口中已称告辞。
出了御书房,苏逸轻轻将门带上。沈秋看了他片刻,终于道:“事已至此,我是如何也脱不开干系了吧。究竟是何事,为何……仍不教我知道?”
苏逸没有回答,只慢慢道:“陛下等这一日等了三年,你……且让他好好想想吧。”说罢他抬眼,朝远处的天边望了望。那里浓云密布,已非昨日那般晴朗。
他忽然叹了一声,道:“眼看着……这天就要变了。”
*****
当夜轮到沈秋宿值,段云亭破天荒地没让她进入房中。故自黄昏时分起,她便只是侍立在段云亭寝宫外,寝宫里始终一片灯火通明,直到月上中天,里面都不曾有过动静。
没有人进出,也没有半点声响。
眼见着夜已深了,沈秋站得也有些乏了,便悄悄走到回廊边,坐了下来。
抬头看着空中月色,许多事浮出脑海,似有所头绪,却又不甚明朗。
对于这东齐宫中的事,她本无心过多牵扯进来,只是这置身事外的感觉,不免让人有几分失落。
正此时,听闻“吱呀”一声,身后明显地有灯光投了过来。
沈秋一回头,只见段云亭一身明黄的袍子,正抱着手歪斜地靠在门边。
“今夜是你当值?”他的面容隐没在背光的阴影之中,似是微微地挑了挑眉。
沈秋赶忙站起身来,以为此番这小小的偷懒被他逮住,虽不至于治罪,但也免不了一顿调侃奚落。
然而段云亭只是却走到她身旁,撩起袍子坐了下来。
“算你有运气,朕今日心情大好,便权当不曾见过。你且坐下吧。”他虽作此言,然而语气淡淡的,却是教人决计看不出心情哪里好了。
沈秋依只得言坐下,见他半晌不语,实在按捺不住好奇心,问道:“陛下……可是有何心事?”
段云亭闻言抬眼望向天际,他的侧脸在月色之中被镀上了一层银白,眼中神情亦是极为少见的柔和。
“朕便这么藏不住心事,一眼便能教旁人看出?”他保持着仰头的姿势没有动,只是轻轻地笑了一声。
沈秋无声地看着他,一时不知如何作答。
“朕今日倒当真是有些话想找人说说,“然而段云亭很快笑道,“只是这话你若听了,便只能对朕死心塌地;但凡有半分忤逆,则将是死路一条。”顿了一顿,他才转眼望向沈秋,声音变得缓慢而低沉,“若是如此,你可还愿一听?”
沈秋静静地同他对视,只觉对方话中之言分明给人以选择,但那神情,却又强势得不容拒绝。
她笑了笑,道:“陛下该知,自打我被首辅大人单独唤入房中的那一刻,便已然无法退步抽身了。且不论我今日听与不听,只要对你有半分忤逆,便照样难逃一死。”
“你果真聪明。”段云亭闻言笑了,道,“应是苏逸提点过你的吧。”
沈秋明白,苏逸口中所提及的上一任御前侍卫长,只怕便是未能经受住秦仁嵩的压迫和利诱而做了眼线,从而被段云亭处置了。
此时此刻她也已然明白,段云亭什么都知道,他从不荒唐,也不糊涂。
他只是在做戏而已。而这场戏,一做便是三年。
如今,似乎到了该作结的时候了。
正沉吟之际,段云亭已然幽幽地开了口:“你且听朕讲个故事,如何?”
“好。”沈秋静静地看着他,颔首。
段云亭讲了一个简单而又复杂的故事:
很久以前,宫中有个妃子产下了一名皇子。但因为皇帝怀疑这妃子同宫中侍卫有染,便暗自认定这孩子不是自己所出。故那孩子虽顶着皇子之名,母子二人在宫中却是备受冷落,人尽可欺。
待到皇子十八岁那年,皇帝驾崩。然而尸骨未寒之际,宫中发生了一场政变。皇帝的三弟——即舞阳王——连同身为朝中宰相的老丈人,以“妖后祸国”之名,将皇后送入皇陵中殉葬。这场政变将朝中外戚一党一网打尽,并处死了本应继位的嫡长子,甚至连同嫡出的二子三子也不曾放过。
这本是朝中权力更替的一次全盘洗刷,却意外地将那个最不可能继任皇位的皇子推上了前台。
因为彼时,那个皇子的母妃已死。他孤身一人,无权无势,最适合做傀儡皇帝,任人摆布。
政变那日,他独自一人蜷缩在黑暗宫殿的角落,看着窗门上投射着的刀光剑影,听着门外不曾断绝的哭喊声,砍杀声,心内是从未有过的恐惧和绝望。
然而下一刻,宫门洞开,火光投射进来,将门外人的一道道身影拉得老长。
他们忽然跪下,道:“恭迎陛下登基!”
自此,舞阳王成了摄政王,手握军权;丞相成了首辅,总揽内政。而他名为天子,实则却不过是个被架空了权力的傀儡皇帝。
他心里明白,既是傀儡,便终有一日会被弃置。他不甘如此,没有一日,甘愿过……
段云亭话音落了,二人之间便只剩下一片沉默。唯有夜风吹动着院中枝叶,摇曳间沙沙作响的声音。
沈秋忽然明白,为何禁军无数,那日竟拦不住一个秦仁嵩。只因段云亭虽贵为天子之尊,手中却从来未曾有过一兵一卒。
半晌之后,她听见段云亭道:“你心下定是十分好奇,朕为何要将你带回宫中吧?”
沈秋转头看着他,等待着他的答案。
“实不相瞒,只因这内宫之中,朕并无一人可以拖信,倒不如寻一宫外之人,来得妥帖。”但段云亭没有同她对视,只是低着头,轻轻笑了笑,笑里隐约有些自嘲,“有个武艺高强,又值得拖信之人护卫在周身,心里总是要安稳些。朕兴许是怕兔死狗烹,鸟尽弓藏,自己哪一日……便不明不白地死了吧……”
沈秋看着他,讶异之下,只觉心里堵堵的,莫名难受。
若不是今日亲眼所见,谁又能想见,平素嘻嘻哈哈,老不正经的段云亭,也会有这样的一面?
沉默了许久,段云亭神情里似是恢复了几分轻松。他笑了笑,道:“不过,实则朕方才所言……倒有一句不实。”
沈秋转头看他,还未发问,却被他忽然伸手揽住了肩头,登时浑身僵硬,表情也不自然起来。幸而有夜色遮掩,方才没有露陷。
“实则自打你跟着进了宫的那一日,朕便已然将你视作自己的人。方才那番话,无论你听或不听,一样的别无退路。”段云亭用力将她揽近了几分,笑了笑,低声道,“此事……你该明白。”
他语声可称柔和,然而话中之意却又是少见的强势。沈秋闻声不由转过头去看他此刻的表情,然而对方不知何时已然恢复了一脸满不在意的笑。
下一刻,段云亭又忽然放开手,站起身来,若无其事地伸了个懒腰。仿佛刚才并未说过那么一番话一般,笑道:“夜已深了,朕且去休息了。”
沈秋站起身来,看着他转身进了房间。只觉得方才被他搂过的地方,到现在都还有些不自在。
*****
次月初三,常年镇守边关的摄政王段霆均回京。他此行为探亲而来,故所带不过千余人马,尽数驻扎在城外。
是日,群臣于宫门外迎接,声势浩大,却唯独不见段云亭。
段霆均身形高大魁梧,目光如炬地在人群中扫了一眼,道:“为何不见陛下?”
他一开口便是气势雄浑,声如雷霆。魄力之下,群臣一时无人应答。唯有他老丈人秦仁嵩上前道:“尚且不知何故未曾前来……已然派人去催了。”
“不必了,他不见踪影,本王亲自去见便是。”段霆均哼了一声,撩起披风,大步而去。
段霆均来到寝宫的时候,段云亭正烂醉如泥地瘫倒在软榻上,杯壶散乱了一地,满室刺鼻的酒气。
沈秋立在他身后,见段霆均气势汹汹地走了进来,便作势伸手推了推他。
段云亭不为所动,口中还喃喃地说着梦话。
沈秋原以为段霆均会同秦仁嵩一般尴尬地立在原地,谁知他竟大步冲上前去,拎起段云亭的衣襟便将人提起了几分。
沈秋本能地上前阻拦,却被他怒喝道:“你算什么东西?滚开!”
沈秋看了一眼段云亭,在他的眼光示意下,退到了一旁。
段云亭身子随着段霆均的力道晃了晃,似是酒醒了几分。他终于坐正了身子,带着醉意,看着对方懒懒笑道:“原来是皇叔啊……”
“你倒是还认得本王?”段霆均用力地松开手,满目怒容,“今日本王回京,你竟连面也不露,岂非是有心给本王难堪?!”
段云亭重重地摔回软榻上,仿佛才意识到什么,伸手揉了揉朦胧的眼,软绵绵地道:“小侄岂敢给皇叔难堪,实在是一时醉宿……哎,忘了迎皇叔回京。”段霆均面前,他竟连自称也改了,二人私底下是何等的情形,有此可见一斑。
段霆均怒道:“你继位好歹已有三年,本王立你为帝,锦衣玉食供着你,难道便是为了看你三天两头不上朝,没事便往宫外跑?纵是傀儡也该有个傀儡的样子,如此不成气候,本王要你何用?”
“皇叔,小侄若太过成器,岂非要教你头疼了?”段云亭伸手理了理散开的衣襟,半睁着眼,看着他懒懒笑道,“小侄自以为除却平日贪玩了些,其余事上还是颇为听话的,如此……岂非正合皇叔之意?若是换了旁人,难保不会为皇叔添些麻烦吧?”
“你还算明白自己的身份地位,”段霆均平复了几分怒气,冷笑一声,幽幽道,“只是你若当真明白,便该知道,这世上能替代你的人太多,你若再这般不识好歹,末了便莫要怪本王不留你!”
这话说得分外深重,变脸沈秋也忍不住微微变色,而段云亭却只是面不改色地徐徐笑道:“皇叔大可放心,朕每日有得吃喝有得玩乐,便分外满足了。自然不会不识抬举,将这天上这掉下来的馅饼拱手送人。”
“但愿你记得今日这番话!”段霆均冷哼一声,拂袖而去。
室内安静下来,段云亭仰面歪斜地靠在软榻上,没有动。只是保持着原本的姿势,伸出手臂遮住了眼。
沈秋走上前去,想说什么,他却仿佛已经预知一般,轻轻道:“朕没事。”
沈秋默然地看着他。今日所见,让她对段云亭那夜所言,才当真有了几分感同身受。若非亲眼所见,又有谁能想到,这荒唐无理,不务正业的东齐皇帝,私底下过着的竟是这样的一种日子?
“苏逸已然离宫,”半晌之后,段云亭终于又开了口,声音里全无一丝醉意,“明日朝上,一切自见分晓。”
*****
当夜,沈秋照例帮着段云亭批阅奏折。
此刻她也明白,面对着这些奏折,为何段云亭能如此随意地让旁人代劳,只批一个“准”字了事。
因为到他手中的奏折,实则已是拍板定下的决议。无论他准或不准,结果都并无差池。
段云亭那晚格外安静,只是背身立在窗边,看着窗外无边的夜色,一言不发
沈秋批阅奏折之余,抬眼看向他,只见他一身明黄的锦袍,长身玉立,整个人在室内的灯火通明之中,竟同时给人以雍容和冷寂这两种矛盾着的感觉。
而他心内所想,自己几乎可以感同身受。
沈秋静静地看着他,不觉出了神。直到门外忽然响起一个声音:“小姐,不可如此冒然进去,且待在下禀报一声,再……”
然而门已经被从外推开。一个粉衣女子出现在门边,往室内扫视一圈,目光落在段云亭处,面上明显露出笑颜。
“楚楚,你怎么来了?”段云亭闻声回过身来,有些惊诧。
那唤作楚楚的女子几步走到段云亭面前,笑道:“我此番随父亲一同回来,也……抽空来看看陛下。”顿了顿,垂下眼去,面上分明是微微地泛起了红,“一别数载,不知陛下一向可好?”
“是啊,想来已有数载未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