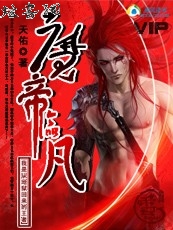苏醒 作者:何许人[出书版]-第2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那天晚上,铃蓝告诉我她可能要去北京一个月,为了新的画展,还预约了一位老中医。我们在房间里拥抱亲吻,这将是一次历时最久的别离。我们都小心翼翼,如同之前的每一次,铃蓝是个需要极度呵护的女人,玻璃一样的女人。送她上车的时候,我发现娇妹竟然红着脸看着我,眼里有莫名的火光在闪烁。
第二天,送走了最后的宵夜客人我正在厨房做着最后的清洁。工人们都睡去了,他们需要早起。娇妹递了一瓶酒给我,这是我爸爸酿的,全凤凰最香的,你尝尝。
苗家人送的酒是不能推辞的,这是规矩。我收下了,谢了她。可她没有要离开的样子,望着我,好像等着我喝,然后亲口告诉她这酒的确很好喝。正好我饿了,弄了个卤水拼盘,干脆当着她的面喝一点,让她满意。
那酒真的很香,诡异的香。不单纯是酒的芬芳,似乎所有春天的花都被装了进去。一口喝下去,好像有一只小手在心尖挠着,挠得心痒痒的,忍不住再喝下一口。我似乎都没来得及吃菜,就把那一瓶酒都喝完了。喝得我全身的毛孔都舒展开了,散发着那异香,无数的山花仿佛在我皮肤上开放着,望着娇妹的笑,我有种飘飘欲仙的感觉。
不知道什么时候,娇妹开始脱衣服了,那层层叠叠的绣片下有着丝缎般光滑的皮肤。我眼前泛起了充满酒香的水汽,她冰凉的身子贴过来,有种不可言喻的舒畅。我一定是醉了,我忘了我是谁,也忘了她是谁。我把她压在了那个柜子上面,柜子就开始吱吱哑哑唱起了歌。她就像是沱江的水做的,柔软的身体可以包容最激烈的冲撞。欲望像九月天的野火遇上了干柴,放肆地烧,那一刻我登峰造极。
烟花绽放之后徒留些星星在天空,酒劲过去了,我有些胆怯。娇妹像只野猫一样,舔着手指上的鲜血,她伸出舌头的样子魅惑至极。我甚至觉得她比我更满足,这个夜分明是她的设计。
我从来没有背叛过铃蓝,我也不爱娇妹。虽然我知道娇妹喜欢我,她偷偷看我画画,偷偷翻看我听的歌,甚至把我脱下来没有来得及洗的衣服捧在手心嗅着,我知道,她们民族的女人为了爱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娇妹,我只爱你铃蓝姐。”我必须跟她摊牌。
“不要紧的,我只要这样就满足了。”她脸上的潮红还没有褪去。这样的女人,我还能说什么呢。男女之间,往往会一而再再而三。
我不想带她去我的房间上那张属于我和铃蓝的床,于是后来的每次,我们依然在厨房,在工人们睡了之后,在那张柜子之上。娇妹喜欢把自己摆成案板上的肉,任我宰割。
(3)铃蓝终于还是回来了,不过晚了三个月,她的病已经治好不少,医生说,她现在的心脏状态甚至可以怀孕。
娇妹看到她有几分歉意,低眉顺眼的,没了往日的野劲。“怎么了?是不是谈恋爱了,我们的娇妹会害羞了呢。”铃蓝姐妹般搂着娇妹,娇妹的手却在背后拉着我的衣服。
我赶紧走开,“娇妹有了男朋友,过几天还会带来给我们看呢。”我的演技蹩脚,台词亦像三流的肥皂剧,幸好铃蓝没有看出端倪。我告诉娇妹,我们以后再也不可以继续下去了。可娇妹只没心没肺地笑,仿佛我说的话一个字也没听进去。
事实证明,她那样的笑是有道理的。她怀孕了,已经快四个月了。我感觉自己掉进了一早就挖好的坑里,有些被动。
我对她说,不能要,打掉。
她嘤嘤地哭,这个孩子我想要,哪怕你不承认也是可以的,你不知道我有多爱你,绝对不会比铃蓝姐少。
我说你别傻了,我们根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当初,当初如果不是那酒,我根本不会和你……说到酒,她笑了。“你最后一定会爱上我的,因为那酒里有我下的蛊。”什么?!我震惊了,难怪那晚的酒香那么诡异。虽然关于蛊毒,都是苗乡的传说,不过没有体验过的人,不会知道那些东西是否真的莫须有。
我真的生气了,推搡间,她从二十六级楼梯下滚落。血从她身下倾泄而出,她紧紧捂着肚子,疼得瑟瑟发抖。送到医院,孩子已经掉了。
(4)半个月后的一个雨夜,面色苍白的娇妹来店里找我。彼时,她正在站厨房里望着奔腾的沱江水,手里扔出一片钥匙,我认出,那是她躺下和我欢爱那柜子的钥匙,柜子里面又没放什么东西,这个女人不知道想搞什么鬼。
我说我们都结束了,最好不要再纠缠不清。她瘦削的脸上表情有些异样的执着:知道吗?我们苗家的男人为什么一生只真爱一个女人。她把视线移到了我身上,那是因为我们的女人会下蛊,只要下蛊的人活一天,那个男人就会爱那个女人一天。
这些匪夷所思的民间传说是吓不到我的,如果她说的事情是真的,为什么我现在对她完全没有爱意?不想这些了,这个女人让我烦,孩子已经没有了,我给了她一大笔钱,这些应该足够了。她到底想要什么?
“如果你不娶我的话,我会把我们的事情告诉我爸爸,你应该知道吴家有多少人吧。”她竟然威胁我,这个乡下女人。
夜色正浓,雨更浓,一阵雷鸣的同时,我用肘子让她晕了过去。见鬼去吧。这个不知所谓的女人,不但要我的身体还想要我的全部。那晚被她下药的酒,还有意外怀孕的孩子,这个处心积虑的女人真是太可恶了。我喝了半瓶新酿的包谷烧,有了些底气。
刀是雪亮的,雪柜里还有些空。我磨刀霍霍,我挥汗如雨,我要这个女人彻底消失。我要让她知道,男人是不会害怕女人的。我面目狰狞,每一刀都命中要害,温热的血被我用桶收集起来,加少许盐,混在粗糯米粉里可以做一道凤凰名菜,血粑。绞肉机不停地工作着,还拌了些姜丝进去。那颗曾经漂亮的头颅,被洁厕剂淋过后不会有人再看清她的样子,连同斩碎的骨头,用麻袋装着,再加进去一块足够分量的大石头,扔进沱江里。一圈不大的气泡浮上来,她消失了。
一切都刚刚好,只是还差一点点,最后的器官是娇妹的心,已经切成了小块,还没有来得及放进绞肉机就传来了铃蓝的声音。我把它慌乱地塞进了柜子。
很好,所有吃过店里的肉汤和血粑的游客都赞不绝口,没有比这更鲜美的了。我微笑着看着他们满足的表情,挽着铃蓝的腰,目送着客人们擦干净嘴巴,打着饱咯离去。生活重新回到了过去,没有娇妹的时候我脸上一直是这样轻松的微笑。
没有人知道娇妹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也不知道,那个午夜的雨太大,不会有人看见她在我这里出现过。
(5)可是蟑螂出现了,虽然数目不是很多,但是让人头疼。那天我正在电脑上登记资料,突然没来由地显示屏黑掉了。我检查了电源,没有问题,可怎么都不能正常开机。第二天,请了电脑专家来检查。机箱一打开,几只特别大的蟑螂飞了出来。
“是蟑螂咬断了电线引起死机的。”专家告诉我。
什么?蟑螂连电线都吃?铃蓝瞪大眼睛望着支离破碎的各色电线,有些不相信。专家告诉我们,蟑螂不但吃电线,基本上所有人能吃的东西,人不能吃的东西它通通能吃,生命力特别顽强。送走了专家,我上网查了查关于蟑螂的信息。
原来它们是世界上生命力最强的生物,即便地球被核辐射污染五十遍它们也不会死。好在网上同样介绍了不少灭蟑螂的办法,还有不少专业杀虫公司的联系方法。我记下了距离凤凰最近的一家公司电话,邮购了不少灭蟑特效药。
药很快送来了,我按照说明把药撒在了蟑螂经常出没的地方。药很灵,没过几天就发现了不少蟑螂发尸体。我把它们扫到一起,用纸包着,捏起来,恶狠狠地揪断它们的腿,“一条,两条,三条……”我望着墙上娇妹的油画,嘴角的微笑可能有些恶毒。最后,我把这一小堆木乃伊蟑螂塞进了那个打不开的柜子缝里。
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再看见蟑螂。
(6)突然有一天,许许多多乌黑油亮的大蟑螂又出现了,这次它们成群结队,大摇大摆的样子根本没有把我放在眼里。我的头又开始隐隐做痛,自从看见蟑螂在店里出没以来我就经常这样。这些不吉的昆虫,行动迅速,在阴暗的角落潜伏着,像小小的幽灵不时窜出来吓人。
特效药好像失去了作用,不知道是不是它们身上已经产生了抗体,好几次我明明看见它们已经活动缓慢,似乎要从墙壁上掉下来了,可我一靠近,它们又振翅飞翔,似乎刚才的样子不过是戏弄我。
终于,蟑螂来找我的麻烦了。
那天一个客人在汤里喝出了一只蟑螂,把我们告了。我用了很多钱才把事情摆平,不过防疫站负责人对我说,如果蟑螂的问题在整改时间内不解决,他下次就不再帮我了。
我开始绞尽脑汁找蟑螂们修养生息的栖身之处。地毯式的搜捕还是没有发现什么端倪,可我却分明感觉到蟑螂们躲在某个角落看着我笑。终于,我把视线落到了那个打不开的柜子上。只剩下这个地方没有看了。
我找来一把大钳子,其实要撬开这个锁很容易,只不过我不想这样做,一旦柜子打开我将看到已经萎缩的破碎的娇妹的心。想到这个,我就有些心虚,手上使不出力气。
柜子终于还是打开了。蟑螂们水一样流淌了出来,它们冰凉的翅膀贴过我的皮肤就像那晚娇妹的皮肤一样凉,他们振翅高飞的声响让我的汗毛竖了起来。它们密密麻麻的疯狂地扑向所有能吃的东西。我被这情景吓住了,明明放进去的蟑螂的尸体,怎么会变成那么多只鲜活的蟑螂?它们不是已经死了吗?莫非它们是蟑螂的鬼?
恐怖的事情还没有结束,蟑螂们走得差不多的时候,我看见了柜子最里面,有一具老鼠大小的婴儿的骸骨。怎么我没有看见娇妹的心,那颗已经萎缩的,破碎的,可能已经被蟑螂咬得千疮百孔的心。那小小的骸骨上残存的腐败组织上还有一些透明的小虫在挪动着。突然,我想到了一件事情。
“你一定会后悔的。”娇妹在去医院的路上对我说。
我承认,是我故意推她下去的,因为她坚决不肯把孩子打掉。我明白了娇妹的意思,柜子里的小骸骨,是她肚子里面的孩子。我的头开始剧痛,似乎里面有只小手在拉扯着我的神经。
一只大蟑螂落在了脸上,整整六条腿稳稳站在我的脸上,这腿曾经沾染过娇妹的心和我的孩子。我重重地给了自己一个耳光,把它打死在自己脸上。
后来,蟑螂死去的地方皮肤开始溃烂,医生说,这不过是普通的筒线虫感染,可不知道为什么用了很多药都治不好。我每天都在家里躲着,像蟑螂一样怕光。现在我整张脸都开始溃烂了,我甚至觉得脑子里面也在溃烂。
铃蓝说她在网上查到,即便蟑螂死了,肚子里的卵也不一定死,只要合适的时候它们就会孵化出来,我们柜子里面的就是这样。
我说,不是,它们是孩子派来的。铃蓝看我的样子摇摇头,隔壁的大娘说你像中了蛊毒。我却指着墙上的蟑螂说,你看,那是娇妹,她来找我了。
十二、温床
他的头被一个透明的胶袋套住,胶袋在脖子处收口,用宽边的透明胶缠了一圈又一圈,很紧,绝对不能用手撕开,就算是正常人也不可能,更何况现在的他已经烂醉如泥。看到他安详的面容,真让人放心。她的脸上露出了一丝久违的微笑,从这一刻起,他再也不会离开她了。
胶袋不大,里面残存的空气并不多,他可能三分钟之内就会窒息。她计算好时间,接着开始脱去他身上的衣服。刺骨的冷空气让他的皮肤竖起了鸡皮疙瘩,没关系,这并不妨碍她用眉笔在他身上画上一根又一根的线条,然后还标记了1234的顺序。待会儿就按这个顺序下刀吧,他曾经许下誓言,要永远陪着自己,既然他做不到,就让自己来帮他吧。让他的血肉跟自己融为一体,这样,他就真的可以永远陪着自己了。
胶袋里的空气一定是用完了,他的脸色变得很红,口鼻的附近也有不少水汽凝结的小水珠,他努力地转动头,想摆脱什么。她能感觉到他的心跳忽然加速,他的手却变得冰凉,他在挣扎,在醉梦里挣扎。可惜,无论他怎么用力也摆脱不了,这就是他的宿命,违背誓言的宿命。——摘自岑雪小说
A、
岑雪是个写字为生的人,她曾在一篇小说里提到过,夜里十一点半是一天之中人的心最柔软的时刻,看肥皂剧也最容易流泪的时刻,最容易被往事打动的时刻。
现在就是夜里十一点半,秦朗挑这个时间打电话给岑雪,说他开始写小说了,知道她现在担任一家杂志的主编,想让她看看稿子。他还说,想见她,却被她干净利索地拒绝了。她已经不愿再回想这个男人,三年前,秦朗的确担当过她生命中最浓墨重彩的角色,但时间已经冲淡了一切。一切的一切都会过去的,不是吗。如果两年前他来找岑雪,或许她还会欣喜若狂,如果是一年前他来找她,也许她还会答应他的请求出去见个面,现在,她一转身就会忘记这通电话。
妈妈曾说,爱的背面并不是恨,而是忘却。
偌大的两层楼里只有岑雪一个人,客厅和走廊的灯又全都坏了,除了保姆房外,所有地方都码着厚厚的一层灰。三分钟后,岑雪还是决定出去一趟,见见他也罢,让他看看她现在过得有多好。
B、
从外面回来,岑雪不想再被打扰,关了手机,疲倦不堪地看着已经耗费了六个小时打扫却收效甚微的家,没有亲人的空房子,真的还能被称之为家吗?脑中繁杂如麻的思绪终于令大脑崩塌。
跟秦朗在一起的那年也不过是高二,因为爸爸的原因,家成了岑雪最不愿意待的地方。小时候,岑雪是很爱爸爸的,是爸爸让她感觉自己像个真正的公主,每当有人说他太宠她时,他总是骄傲地说女孩子就是要富着养,将来才不会被坏男生用一点微不足道的东西拐跑。岑雪知道,爸爸爱她,可他对她的爱居然抵不过那个坏女人。那个有着很复杂很恶劣背景的坏女人,全世界的人都能看出她跟爸爸在一起不过是为了钱,她真的很想当着所有人的面对她大口骂出最难听的话,可惜,最终这念头被一秒又一秒的等待给消磨了。她说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