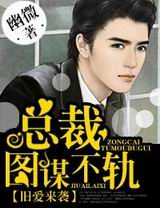图谋不轨-第5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哪怕你是那样的努力过。
他穿着一身青色登山服,帽子盖住了前额,仅有几盏灯的墓园里,庄浅看不真切他的五官,却知道他是谁,她此刻只看到他握着枪的那只手,修长的骨节,宽厚的手背,娴熟的动作。
秦围的这双手,注定该是握枪的,用来翻阅无聊的文件,太大材小用了。
庄浅想起小时候,这双手,抱过她多少次,给她擦过多少次眼泪。
他走了过来,就停留在她的面前,军靴上泥水缓缓落地。
庄浅一声不吭,他也就这么居高临下睨着她,像看着一件可笑的废弃品。
近距离的时候,庄浅才发现,十几年没见,秦围其实变了很多,他的五官较之从前,尽管一样的好看,却更为张扬凌厉,他的身形较之从前的瘦弱,如今更能给人纯力量上的压迫,就连他的眼神,看着她的眼神,也是除了表面温度之外,半点情谊也没有的。
哪怕她一直假装看不到。
雨水淋得她浑身冰冷,庄浅四肢僵硬,在两人死一般的沉默中,突然率先开口了:
“你现在是不是很失望,是不是正等我哭着问你‘为什么’,然后再将你准备已久的讥讽与咒骂倾倒而出?”
“我偏不问。”她别过了脸。
秦围蹲下·身来,枪口轻轻抬起她的下颚,仔细端详半晌,开口道,“这里肮脏泥泞,弄脏了妹妹的衣裳,你可不要向爸爸妈妈哭诉才好。”
爸爸妈妈?就是他身后的那两块冰冷墓碑。
他这时候叫她一声妹妹,恶心得庄浅想吐。
庄浅:“衣裳脏了可以清洗干净,心要是脏了,就再也洗不干净了。”
秦围没接话,他倾身给她解绳索,眉目宁静而温柔,一如从前,自顾自说道,“你以前怕寒又怕脏,娇气又懦弱,谁胆敢弄脏了你的新衣裙,必定是要受一顿教训的,可爸爸疼你,哪怕你无理取闹,谁也不敢多说你一句不对。”
解了绳子,他偏着脑袋看她,似乎想要看明白,眼前的这个人,究竟有哪点出彩,值得万千宠爱。
听他提及父亲,庄浅终于盛怒,得空的双手一挥,狠狠一巴掌甩在他脸上,“秦围!我纵有千般不好,万般不对,可我是怎么对你的?我是怎么对你的你难道一点都感受不到!”
她语气急切,“是,我承认,我最初不习惯你的存在,可那是小孩子的独占欲作祟,原本稳定的家庭中突然多出一个人,我难受也是情理之中,”
庄浅深呼吸一口气,目光涩然地注视着他身后的墓碑,“可是后来我是怎么对你的?我把你当亲哥哥,好吃的好玩的首先送你一份,除了你我谁都不理,我把你当成父母之外最重要的人,你又是怎么对我的?”
她眼眶染上湿意,秦围定定地看着她,很久之后,他才捂着恻恻泛疼的左脸,笑了起来:
“阴历八月十三,距离中秋团圆仅两天,这个日子,你不陌生吧?”不等她回答,他又继续道,“这是咱们共同的生日,也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日子。二十二年前的这一天,父亲找到了我,他救我于水火,许诺补偿我富贵荣华。”
说到这里,他眼中笑意一寸寸扩大,惬意而满足,直到后来,这种笑意渐渐凝固,凝固成苦涩:
“我一直为这个日子庆幸着,每天认真学习,努力训练,就像天下所有懂事的小孩一样,眼巴巴等着父亲一句难得的夸奖,尽管最后总是什么都没有。”
“原本这样没什么不对,我从前没有父亲,不知道父亲与孩子是怎样相处,我以为我们这样的父子关系很正常,所以我更加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加优秀,超乎他预估的优秀。直到有一天,我发现事情不是我想象中那样的——”
“原来,父亲还有一个孩子。原来,他也不总是板着脸的。你只要多吃一口饭,他就会笑得心满意足,你什么都不用做,他也会千方百计哄着你,你乱发脾气无理取闹,他还是照单全收。”
庄浅冷冷听着他回忆往事,看着他眼中不再掩饰的厌恶,心底终于凉透。
秦围有一下没一下顺着她湿漉漉的发丝,屈膝跪坐在地上,额头抵着她冰凉的额头,小声呢喃,“小浅,还没有来秦家,还没有见到你的时候,我就知道,你一定很爱茉莉,会唱甜腻腻的中国小调,笑起来颊边有好看的酒窝,你一定喝粥爱喝咸的,吃药最怕苦的……”
庄浅震惊地盯着他,近距离对上他眸中冷骛。
“这样看着我干什么?很诧异我对你这么了解?因为这每一个细节,都是多年前父亲刻在我骨子里的东西!”秦围目光陡然变得嗜血,他突然一把狠狠拽过她的头,声音压抑而愤怒:
“你大概不知道吧,在没见到你的时候,我就恨不得你死无葬身之地,在知道你的存在之后,我以前自以为是的所谓父爱,全都成了可悲的笑话!”
“父亲对我的好,不过是将对你的好简单粗暴的重复了一遍:他大概永远不会知道,我最爱的花不是茉莉而是雏菊,我睡前最讨厌听狗屁不通的中国调,我从小嗜甜,那种腥咸的海鲜粥让我想吐,我喝药不怕苦,他却加大量糖直到药失了效而我几周不好——”
“来了秦家,他也只是将我当成一个理想的玩偶,让我对你有求必应,弥补他不能时刻陪在你身边的亏欠!”
歇斯底里地吼完最后一句话,秦围粗重地喘息,目光中闪烁着灼灼的烈焰,像是午夜里燃起的鬼火,森寂且清寒,仿佛下一刻,都能将她挫骨扬灰。
这一刻,他真的是要她死的,尽管他因为某种不知名的原因忍耐着。
庄浅清楚地感受得到。
面对一个恨你入骨的人,眼泪是示弱的白旗,提醒对方更加无情地践踏你。
庄浅才要夺眶而出的眼泪又咽了回去,再开口的时候,声音沙哑,“秦围,这么多年,我在你的记忆中,一直都是这样不堪的模样?”
庄浅苦涩地想,兄妹也好,玩偶也罢,终究是要付出感情的,虽然明知真相被揭开的那一日,这种可怜的感情,会变成对方伤害自己的利器。
秦围站起身,手中枪口朝地,眸光中半丝她熟悉的温柔都没有,尽是阴沉。
“你为什么不死?”他突然声音飘忽地问。
他握着枪,发际的水一滴滴落尽脖颈,脚下锃亮的军靴踏在地面,发出沉闷的声音,一步步逼近她,“从小到底,这么多次,你为什么不死?你为什么要活着挡我的路!”
“我死?”庄浅狠狠一抹脸上的雨水,踉跄了几下才从水坑中站起来,面无表情,“你有什么资格决定我的生死?”
秦围放声大笑。
冷厉的笑声回荡在空荡的墓园,几分可怕,“你活着有什么用?你不过是个废物!你就是一团扶不上墙的烂泥!枉费爸爸的心血!”
他眼睛充血,开始语无伦次,“我们身上都流着爸爸的血,他说了的,我能力超群,只要听话努力,以后我可以入族谱,继承家族事业,我是他唯一的儿子……可他跟你一样是骗子!他转眼就要将我赶出家门自身自灭!”
“留学?深造?这全都是他用来哄你的笑话!事实就是他将我抛在美国街头多少年不闻不问!”激烈的大笑声之后,秦围终于笑出了眼泪:
“父亲对你有求必应,对我却苛刻到近乎残虐,这些我都不怪他,可我恨你,从小到大,在秦家十年,我都跟你可怜的母亲一样,要靠着讨好你才能换来父亲看我一眼——你可能从来不知道,从小到大,只是听你叫我一声‘哥哥’,都会恶心得我整晚睡不着觉!多看你一眼,我都怕自己忍不住失手掐死你!”
“你不是已经下手无数次了吗!”庄浅歇斯底里一声大吼,双手死死捂住耳朵,屏蔽了他各种恶毒的咒骂。
她看着他,声音带着难受的哭腔:
“我九岁那年,被人从身后推进泳池,让我至今看到深水都心惊胆寒;我十二岁那年,房间内误出现白粉,我只好奇尝了一丁点,结果在急救室险些没能抢救回来……这些不都是你的杰作吗?”
她哭着撑靠在一方墓碑上,哽咽,“这些,还不够弥补你那点可笑的不平衡吗?”
秦围浑身一僵。
庄浅看着他的目光失望透顶,“秦围,我不是蠢,我只是学不来你的狠。”
“小孩子心思最敏感,从你踏进秦家的那一刻,你以为我感受不到你对我的敌意吗?当着爸爸的面,你总是对我有求必应,可爸爸不在的时候,你连看我一眼都嫌恶心,你以为我真的感受不到吗?”庄浅突然笑了起来,笑到鼻子泛酸:
“我小时候不爱讲话,脾气不好,所以你有恃无恐,你把我当花瓶、当傻子,你吃定我不敢跟别人说,也不会跟爸爸告状,所以你可以随意设计陷害我,却还要在爸爸面前造出我容不下你的假象,做这一切,你不过是笃定我蠢到不会反击——”
“事实上你赌对了,我确实不敢。”庄浅深吸了一口气,“我不敢,更重要的是不想,因为你到底对我好过。”
因为你对我好过,所以我就想对你更好一点。
秦围握着枪的手收紧,呼吸急促:“原来你什么都知道。”
“我当然知道!”庄浅站起身,冷笑着逼近他几步,“你又有什么我不知道的?”
“你心有不甘,意气难平,你一次次逼我上绝路,不就是觉得爸爸偏爱我吗?可我是他的亲女儿,他就我一个亲女儿,父亲疼爱自己的孩子有错吗?你凭什么不甘心!凭什么意难平!凭什么指责我不配!”
说到后面,庄浅痛哭出声,跪倒在地上水滩中,紧紧靠着身后冰凉的墓碑,秦贺云的墓碑。
“可父亲不止你一个孩子!”秦围突然变得怒不可遏,手中枪一扔,上前一把掐住了她的脖子,将她抵在墓碑上,大吼,“你知道什么,父亲不止你一个孩子!”
“你想、想说自己吗?”庄浅剧烈吸气,被他猛力推搡之下,后背摩擦在墓碑上,痛得锥心,却依旧含不甘示弱,冷声问,“秦围,你想说父亲还有一个孩子,就是你,对吗?”
秦围没出声,只狠狠盯着她,掐着她脖子的手用了大力。
他快意地看着她脸色一点点涨红,一点点变得青紫,生命一点点从他指尖流逝。
可那种亲手了结掉她的痛快,近在咫尺,却并没有带给他半点多余的解脱。
庄浅看着他,看着他眼神挣扎,茫然,慌乱。
像是看着一个可悲的笑话。
“你是在做梦!”在他失神的瞬间,她猛地提脚,重重将他踹离出两米,在他回神反击的时候,她已经捡起了那把被他扔掉的ak,黑洞洞的枪口指着他。
雨水滂沱,庄浅却不觉得冷了,一种激烈的愤怒在心底叫嚣,提醒她用尽各种手段,也要将让所有伤害自己的人付出代价。
她唇角噙着冷笑,大声道,“秦围,这么多年,你都是在做白日梦!父亲从始至终都只有我一个女儿,你算什么?你不过是个没名没姓的外人,一个被你母亲抛弃、硬塞给我爸爸的可怜虫!”
她说,“你处心积虑,机关算尽,事到如今,你难道不觉得自己才是最大的笑话吗?”
“你撒谎!你是在撒谎!”秦围面目疯狂,冲上来狠狠一拳挥向她。
庄浅毫不示弱,两人扭打成一团。
砰砰几声,手枪走火,几枪放了空。
庄浅最终被他掐住脖子,压在水潭里,命悬一线。
她呼吸艰难,声音嘶哑,却依然力争,“我撒谎?是你母亲恬不知耻,跟别的男人生了你,却又没能力养活你,就将爸爸当傻子耍,说你是爸爸的孩子!你还要污蔑我撒谎?”
秦围眼中惊涛骇浪。
庄浅痛快地笑,他越是惊慌,她就笑得越痛快,“你来秦家的第二年,我躲在爸爸的书房里睡觉,意外被争吵声惊醒,那是你母亲又一次不识好歹来问他要赡养费,在爸爸将亲子鉴定结果摔出来的时候,她才堪堪收起难看的嘴脸……”
说着,她伸出手,一点一点拉下他的脖子,嘴巴凑近他的耳朵,温柔地叫了一声哥哥,“你想不想知道,在得知你不是他的亲生子之后,爸爸打算怎么对你?”
秦围眼神骤然变得慌乱,庄浅却愈发痛快。
脖子上的劲道一点点松了下去,她脸色渐渐平复,稍稍平复了呼吸。
庄浅自己都知道,自己此刻一定笑得很恶毒,她对他说:
“盛怒之下,爸爸要将你送给跑黑船的下流混混,让你跟黑船上那些肮脏的低贱人一起混生活,让你只能接触妓…女、嫖·客、赌徒凶手……让你一辈子都只能做个出卖劳力却连半分报酬都得不到的下…贱粗人。”
她说,“你原本的生活就会是那样的:像是阴沟里可怜的臭虫一样,被粗俗有钱人使唤,跟肮脏的妓…女偷·欢,被恶毒的嫖…客痛打。”
她说,“是我,秦围,是我救了你,给了你可以选择的未来。”
她还说,“是我哭着求爸爸,说我要哥哥,我不要你走,你才有命留下来,才有机会受到良好的教育,得到全能的训练,才有命在今天一次次陷害我!”
到后来,庄浅目光通红,已然歇斯底里。
“不可能、这不可能的……”秦围失魂落魄,他猛地推开她,踉跄着起身,大吼,“你撒谎!你是骗子,你从小都是撒谎精,这些都不是真的!你是骗子!”
没再给他又一次出手的机会,庄浅抬起枪,子弹迅速上膛,食指轻轻扣动扳机。
黑夜里,一声沉闷的枪响。
秦围没力地跪了下去,正跪在秦贺云的墓碑前。
他的左膝盖鲜血汩汩,喷洒在泥泞的地面。
庄浅木然地看着他,继续说,“你就是一条心理扭曲的可怜虫,得不到爱,也不配爱人,你母亲把你当成骗钱的工具,至于你父亲?根本无从谈起,你没有父亲。”
“这世上唯一对你好的人,唯一真心对你好的人,不是生你的母亲,也不是给你希望的秦贺云,是我,是我这个被你恨之入骨的‘妹妹’。”
她声音顿了一下:
“不过现在,你真的是什么都没有了,你也不必再嫉恨我,因为我跟你一样一无所有。”
秦围跪坐在水潭里,抓着墓碑的手都磨出了血,整个人如同死透了一般毫无动静,麻木地听着她一声声恶毒的诅咒,只有膝盖还在不断地溢血,将地上的泥浆浸染得愈发浑浊。
庄浅在原地跪了下来,分别在庄曼和秦贺云的墓碑前扣了三个响头,周周正正地扣完头,她脸上都溅满了泥浆,良久,她突然吃吃地笑了起来,问秦围:
“你说这是不是就叫做‘人生如戏’?当一个人处在绝望,却最终发现自己连恨的资格都没有的时候,他一定就想死了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