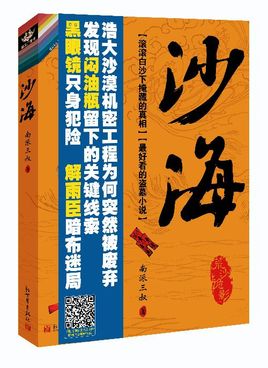陈毅系列传记-第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张伯驹微微一笑道:“齐先生不拘成格,自成一家。依我之见,这个‘云’字便好过了邓石如的那个‘天’字。上联若是‘地为龙世界’,下联的‘天’字便不可一动。上联为一个‘海’字,与‘云’字相对,又有什么不妥。”
听张伯驹这么一解释,齐白石才宽了宽心,笑了起来。
话题自此扯开,张伯驹说起了民间传的纪晓岚改唐诗的故事。
“乾隆皇帝有一次得了一个十分珍贵的扇面,让纪晓岚题一首王之涣的《凉州词》在上面。晓岚得意,一挥而就,写完一看,才发现丢了一个字。那原诗本是一首七绝:‘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纪晓岚一时得意,竟写丢了一个‘间’字。”
齐白石问道:“那怎么办了?”
张伯驹继续说道:“扇子递给乾隆皇帝,乾隆一下便看出来了。这位‘古稀天子’自幼饱读诗书,岂能骗得了他?一问。纪晓岚答得却妙:古人向有‘一字师’之说。惜墨如金,方有千古文字。王之涣这一首,‘间’字原本多余,臣便把它略去了,乾隆不解,让纪晓岚详述。纪晓岚便道:这本是一首词,词,长短句也,方名实相属。这首词念来,却是这样:‘黄河远上,白云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乾隆听罢,连声道好。”
齐白石听了,细细一想,也觉有趣,笑了起来。
小叙片刻,齐白石忽然对张伯驹说道:“前次去中南海,我见到了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他告诉我,《伯远帖》已从香港买回来了,不知是花了几百万还是几千万,用的是外国钱。周先生说了,有时间,可以去故宫看一看。”
张伯驹心头一震!
他仿佛听到了久别的亲人的消息。
“听森然说,这《伯远帖》在丛碧兄手上过过?”齐白石问。
张伯驹猛地站了起来,似乎并没有听到齐白石问什么,怔了好一会,才对齐白石说:“齐先生,过了年,我们一起去看一看,怎么样?”
“好,好!”齐白石连连答应着。
方才他们进屋的时候,何香凝便出去了,这时,她同齐白石的夫人胡宝珠一同拉着手进了屋。因为常来常往,自然免去了客套。何香凝向张伯驹问起了他的夫人:“伯驹,这两天慧素怎么没到我那儿去?”
何老太太已经七十多岁,身体健朗,广东口音很重,为人热情豁达。她的画属于岭南画派,高洁冷艳、苍劲峭丽,尤工画松竹花卉,别具一格。最近,慧素正和何香凝以及刘继瑛、肖淑芳为慰问抗美援朝的志愿军做几幅大画。自古以来,女画家便寥若晨星,女国画家、女书法家更是凤毛麟角,屈指可数。何香凝望重德高,又十分好客,在北京的女画家都愿意同她在一起。
张伯驹道:“这几天,孩子有病,脱不开。”何香凝关切地问候了一番,又道:“一半天,我要去府上拜拜呢。听人说,慧素临过一张吴历的山水,绝了,不少人题词呢,真该看一看。”张伯驹热切地表示了欢迎。大家又闲聊了片刻,便告辞了。
齐白石送他们出了门,临别,不放心地嘱咐道:“对联的事,就不用往外传了,免得不好。”张伯驹见老人慎重的样子,觉得挺有意思,又劝了几句,便离去了。
二
大年初三,家里来了一位稀客:谭得侃。
一晃几年不见,谭得侃明显地老了,皮肤松弛、粗糙,抬头纹又密又深。走起路来,步子也不那么稳了。一双黑黑的眼睛,全无昔日的光彩。一身毛料的中山装,只能带给人一点儿强打精神的感觉。看得出,这几天他的日子不那么好过。
他从广东来。
北平解放后,为还欠款和维持家用开支,张伯驹把护国寺的一处老宅卖了,全家迁到了后海南沿的一个小院里。这是他最后一点儿不动产。院子不大,也不够规矩,一排四间北房,西边是一个偏厦。街门冲着后海的南沿,进门是个不大的天井。右手拐过去,便是那一排北房。院子里,种了几棵桃树,到南墙,不过几米宽。早年间,这个小院是安顿老家来人临时住一住的,全然是寻常百姓之家的模样。张伯驹会住到这种地方来,谭得侃也是万万没有想到。若不是傅湘领路,他根本就找不到这里了。
一见张伯驹,谭得侃便直截了当地说:“我打算在这儿住几天,方便不方便?”
张伯驹自然应承了,让荣管家把谭先生带到客房里安顿了下来,谭得侃一路劳累,洗了洗,便关上门睡了,直到傍晚,才出了房。
虽说睡了一大觉,可他的气色依旧不大好,分明有什么心事。
谭得侃是有心人,礼数上是周到的。傍黑,有人把他的行李送了来,是沉甸甸的两口大号木箱。谭得侃让人把其中一箱抬到上房,打了开来,居然全是各地的名产,有南京的板鸭,金华的火腿,姑苏的酥糖,山东的牡蛎,江苏的银耳,广西的猴头,浙江的鲤鱼,广东的龙眼和月饼。一个大箱子,装得满满登登。张伯驹颇觉意外,客气了两句,谭得侃却随意说道:“一点土仪,不成样子,胡乱送人算了。不值几个钱的。”“谭先生好似有什么心事?”张伯驹关切地问。
谭得侃目光发涩,微微一叹,好一会儿才说:“张先生,我是来求你帮忙的。”他回身看了看,又道:“请借一步说话。”
张伯驹好生疑惑,便把谭得侃请到了书房里,关上了门。
谭得侃闷闷地吸上了烟,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说:“听傅湘兄说,你把城里的房子家里的地,都卖了?”
张伯驹点点头道:“哦,是四九年初,正是北平解放前后。”
谭得侃目光发滞,点点头说:“你是聪明人,聪明!得侃当初不服,还想同仁兄一争高下,如今才知道,确是万不及一。”
“谭先生这话是从何讲起?”张伯驹更加不解了。
谭得侃一叹,摇摇头说道:“这事,说来话长。本来,我这个人是抱定宗旨,一件古董不卖的。可那一阵,地贱得让人流口水,钱又毛。我想着是机会来了呢,一下子买了八千多亩上好的水田。辛辛苦苦攒了几十年的古董,一下子卖掉了一多半。想不到,共产党真得了天下,上来就搞土改。开头,我以为是减租减息呢,没怎么当回事。唉,结果是分田地。八千多亩良田,一下子全分了!”
张伯驹默然地看着他,不知说什么好。是命中注定,还是因为贪心不足呢?
谭得侃又道:“好在,那些地不是用我的名义买的,要不,非得划个地主,戴上高帽儿游街不可。”谭得侃咽了口唾沫,唏嘘了几声,又说:“这还不说。最惨的,是上海的那些房。我想着上海自古便是块风水宝地,寸土寸金。打上海的那阵,房子稀烂贱,买幢三层的楼,才几百块大洋。正好,上海有几个南洋来的商人想买古玩,我就把余下的都拿出来,换了几十万现洋,买了大大小小八千多间房子,有楼,有店铺,还有厂。”
“也没收了?”张伯驹问。在他的印象中,似乎这不属于没收之列。
“麻烦就出在这儿!”谭得侃连呼吸也粗重了起来,说道:“这个事,外界一般还不知道呢。民国十七年,孙殿英不是掘了慈禧太后和乾隆的陵么?民国三十四年冬天,曹志福又带着遵化县县长贺年汉、民兵队长穆树轩一伙,偷着把同治的惠陵、康熙的景陵也给盗了。东西装了几辆大车。中间,因为穆树轩私藏,让曹司令给崩了。接着,又一口气把咸丰的定陵也给掘了。那东西,真是没少弄。”
张伯驹点着头说:“皇室的载涛、载润上书政府清查,但没有下文,对吧?”
谭得侃恨恨地说:“事情,又毁在项林这个混蛋头上。不知怎么搞的,他同贺年汉这伙人拉扯上了,劝我买下一点儿来。那价钱,也真是过得去。我动了心,弄了一批回来。在上海卖给那些南洋来的商人的古玩,就是这批东西。事情,就麻烦在这批东西上。”
他说得有些气促,喘吁吁的。张伯驹给他倒了一杯水,他双手把杯子捧着,喝了几口,一声长吁道:“那些东西,让上海军管会的人发现了,全扣了下来。张伯公,听说,你跟共产党的上海市市长陈毅,交情挺深。能不能帮着……通融一下。我实在是……倾家荡产了。一念之差,竟落了这么个下场,真是太没想到了……
说到这里,谭得侃突然停住了。
张伯驹的面色一下子变得十分难看起来。他停顿了一会儿,说道:“谭先生,你让我为难了。”
谭得侃身子一震,呆呆地望着张伯驹,嘴唇动了动,喉咙里呼噜了两声,没说出话来。
张伯驹道:“谭先生知道,我是国民党的旧人。同陈仲弘先生,我只是以文会友。陈先生精于诗词,每有佳咏,令伯驹钦敬。至于别的方面,他当他的市长,我当我的百姓,是没什么联系的。这类事,我看,倒是谭先生的不是。审时度势,顺乎潮流,是我们文化人的立身之本。发国难财,趁乱投机,正是伯驹一向所不齿的。”
“张伯公,你和陈市长讲一下,成不成另外再说。堂堂一市之长,这么点小事,打个哈欠就办了。在我,却是一生的心血。我家上有老,下有小,这辈子,真是不敢吃、不敢喝,有了病,连剂药都是舍不得吃的……”
他说得声泪俱下,张伯驹却不为之所动。
“谭先生,这件事,伯驹实在难以开口,你还是听凭军管会处理吧。”
谭得侃脸上的肌肉滚动,眉目中,是一种使人看不下去的绝望。
第二天,谭得侃便离去了。
两口箱中的土产,一箱给张伯驹,一箱是打算由张伯驹拿去送给陈毅家的。张伯驹执意让谭得侃把东西带回去,谭得侃死活也不肯拿。张伯驹无奈,便把家中的最后一百块银元包了一包,拿给了谭得侃。
送走谭得侃,慧素道:“他这是贪心不足、机关算尽,聪明过头了。”
张伯驹道:“古人云:欲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有。他这是一个太好的例子了。”
这时候,门外一阵热闹,竟是何香凝老太太同几位女画家一齐来串门了。一块来的还有一个人是张伯驹夫妇所没想到的——西谛。
西谛比张伯驹略小,三十年代初便已是文化界的知名人士,著述甚多,尤以藏书丰富著称。抗战期间,他在上海留居,致力于进步文化。他所著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俗文学史》二书,享誉甚高,亦为张伯驹十分推重。以往,张伯驹同他来往不多,只是一般的相识,打打招呼而已。一九四一年张伯驹被韦江魂绑架,慧素找到了他,他当即鼎力相助,当成自己的事来办,不但慷慨解囊,而且通过舆论界向歹徒施加压力。张伯驹脱出樊笼之后,曾同慧素一道登门道谢。解放后不久,他出任中央政府的文化部副部长,事务多多,二人之间的往来便少了。张伯驹为人倨傲,尤其对当官的人,你不理我,我决不去求你,免得让人看低了。一上岁数,他的这股劲就越来越突出了。
“伯驹,老郑来请你出山呢,”何香凝热切地说:“为新中国,你应当干点什么。一个人闷在家里,会老得快!”
西谛的本名为郑振铎。
张伯驹忙道:“我一个衰朽之人,能干什么?”
“起码可以自食其力。”何香凝不客气地抢白道:“新中国不喜欢吃闲饭的。我这个人,别看七十多岁了,这些年,还不全是靠着事撑着。真闲下来,什么也不干,早就死了。李济深、蔡廷锴、程潜,还有冯玉祥夫人李德全,都是你熟悉的,哪个不在干事?昨天我碰见了李书城,比你岁数大多了,光绪七年(1881)生人,才比我小三岁,还不是干得热火朝天?最近,准备出任农业部的部长呢。”
张伯驹连连摇头道:“晓圆先生(李书城字晓圆)乃一代人才,伯驹怎么和他比?辛亥武昌举事时,他便是汉阳总司令部的参谋长了,后来又出任过北京摄政内阁的陆军部总长,乃国之耆宿。伯驹何德何能,只要不给人家添麻烦,也便心满意足了,不敢再奢望什么。”
何香凝冲着西谛一笑,指指张伯驹说道:“瞧丛碧这股劲,竟是比我还老了呢。”
满屋一阵哄笑,闹得张伯驹也有些不大自在起来。
三
何香凝她们是来看画的,于是,慧素取出了《雪峰图》。《雪峰图》画心不大,高二尺许,宽一尺许,原本乃是清六家之一吴历所作。吴历字渔山,号墨并道人、桃溪居士,江苏常熟人,生于1632年,殁于1718年。他五十岁上入天主教,后至澳门进耶稣会。在上海、嘉定一带,传教三十年。其善画山水,初学黄公望、王蒙,丘壑层叠,笔墨苍润。自澳门归来后,画风有变,构图设色更为邃密苍郁,多用干笔焦墨,格调独特。
慧素临这件东西,其中还有一段故事呢。
《雪峰图》原为傅湘之父所藏,传到傅湘手中,自是极为珍贵。傅湘个人收藏不多,唯有这一件《雪峰图》,是可以自豪的。
民国二十七年夏天,突然一场豪雨,使傅湘家那栋年久失修的房子四处漏雨。傅湘的夫人和孩子们帮着搬东搬西,竟然把挂在墙上的这幅画给疏忽了。傅太太也知丈夫对这件东西的珍爱,当时,傅湘碰巧外出,没在家。傅太太把画摘下来,卷好,因为孩子在里面叫,她随手把画放到了柜子顶上,一转身,便忘了。雨停了,傅湘回来,一进屋便找这幅画,傅太太竟不知放到什么地方去了,急得傅湘又摔碟子又摔碗。后来,总算在柜子顶上找到,已经让漏进来的雨水泡得面目全非了。傅湘一急,登时说不出话来。傅太太知道这下祸事大了,吓得周身发抖。
“就你的破衣烂衫是金的,我这东西全不是东西!”傅湘恨得直骂,然后,把自己关在房里,寻死觅活。书房里的盆盆碗碗,全让他摔了。
他一辈子也没发过这么大脾气。
傅太太跪在房门口,央求他看在孩子分上,看在她多年操持这个家的分上,饶了她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