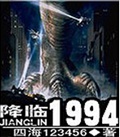1973年的弹子球-第1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也许过于乐观,但不怎么傻。”
“知道。”
“非我自吹,这比相反情况好得多。”
她点头:“那么,今晚是要去打弹子球喽?”
“是。”
“举起双手。”
我朝天花板举起双手。她仔细检查腋窝。
“OK,去好了。”
我和西班牙讲师在上次那家咖啡馆碰头后,马上钻进出租车。顺明治大街一直走,他说。出租车起跑后,他掏香烟点燃,也给我一支。他身穿灰西服,扎一条有三道斜纹的蓝色领带。衬衣也是蓝色,比领带赂浅。我则灰毛衣蓝牛仔裤加一双烟熏火燎的轻便运动鞋。活活一个被叫到教导处的差劲儿学生。
出租车穿过早稻田大街的时候,司机问还往前吗?讲师告以目白大街。出租车前行不久,驶入目白大街。
“相当远吧?”我问。
“相当之远。”他说着,找第二支烟。
我用视线跟踪一会窗外闪过的商业街景。
“找得够辛苦的了。”他说,“第一步是逐个查询收藏者名录。问了二十人左右——不仅东京,全国都问了。但收获是零。任何人知道的情况都没超过我们。第二步是问做旧机器生意的人。人数不多。只是,查阅品种目录花了不少精力,数字太大了。”
我点头,看他给烟点火。
“但知道时间这一点很有帮助—是1971年2月间的事。请人家查了:是有吉尔巴特—桑斯、‘宇宙飞船’、连续编号165029。1971年2月3日废弃处理。”
“废弃处理?”
“废品。就像《金手指》里的那玩艺儿。压成方形回炉,或沉到港湾里去。”
“可是你……”
“阿,请听下去。我灰心丧气,向对方道谢回家。可心里总有什么放不下。类似直感的感觉告诉我:不对,不是那样的。第二天我再次跑到旧机器商那里,去了废铁仓库。看了20来分钟拆废作业,然后进办公室摸出名片——大学讲师这名片对不知底细的人多少有些作用。”
他说话速度比上次见时略快。不知何故,这点使我有点不快。
“我这样说道:正在写一本小书,为此想了解一下废品处置情况。
“对方提供了方便。但对于1971年2月的那台弹子球机一无所知。理所当然。两年半的事了,又没有一一核查。收来光当一放,就算完事。我又问了一点:假如我想要那里堆放的洗衣机或摩托车的车体之类的东西并付相应款额,那么可不可以转让,他说没问题。我又问这种情况此外有过没有。”
秋日的黄昏很快过去,夜色开始笼罩路面,车眼看要进入郊外。
“他说如想了解详情,请问二楼负责管理的人。于是我上二楼问1971年前后有没有人买过弹子球机,负责管理的人说有。我问是怎样一个人,对方告诉了我电话号码。情况像是那个人求他一有弹子球机进来就打电话告知
有点走火人魔了。我就问那个人买了几台弹子球机,他想了想说:看来看去最后买下的时候有不买的时候也有,记不确切。我说大致数字即可,他告诉说不下50台。
“50台!”我叫道。
“这样,”他说,“我们就要拜访那个人。”
21
四下彻底黑尽。并且不是单一的黑,而是像涂黄油一样把各种颜色厚厚涂上去的那种黑。
我脸贴车窗玻璃,静静注视这样的黑暗。黑暗呈平面,平展得不可思议,仿佛用快刀将不具实体的物质一片片薄薄切开的切面。奇妙的远近感统治着黑暗。巨大的夜鸟展开双翅,轮廓分明地挡在我们面前。
家舍越走越稀,后来只剩下如地底轰鸣般涌起几万只秋虫鸣声的草原和树林。云层如岩石沉沉低垂,地面上的一切无不耸肩缩首似的在黑暗中屏息敛气。唯独秋虫遮蔽地表。
我和西班牙语讲师再不做声,只是一支接一支吸烟。出租车司机也紧盯着路上的车前灯吸烟。我下意识地用指尖“砰砰”叩击膝盖。并且不时涌起一股冲动,很想推开车门一逃了之。
配电盘、沙坑、水库,高尔夫球场、毛衣破绽,加上弹子球机……到底去哪里才好呢?我怀抱一堆乱了顺序的卡片,一筹莫展。我恨不得立即返回宿舍,一头钻进浴室,而后喝啤酒,拿着香烟和康德缩进温暖的被窝。
我何苦在黑暗中疲于奔命呢?50台弹子球机,简直荒唐透顶。梦,虚无漂渺的梦。
尽管如此,3蹼“宇宙飞船”仍不停地呼唤我。
西斑牙语讲师让车停下的地方是离道路500米开外的一片空地的正中。空地很平,及踩软草如浅滩一样无边无际。我下了车,伸腰做了个深呼吸。一股养(又鸟)场味儿。纵目四望,了无灯火。唯独路灯依稀照出其四周一小块景物。简直像被人从脚下拖进地底什么地方。
好一阵子我们默不作声,让眼睛习惯黑暗。
“这里还是东京吗?”我这样问道。
“当然。看起来不像7”
“像世界尽头。”
西班牙语讲师以一本正经的表情点下头,没有应声。我们嗅着草香和(又鸟)粪味儿吸烟。烟悠悠低回,作狼烟状。
“那里有铁丝网。”他练习射击似的笔直伸出胳膊,指着黑暗的纵深处。
我凝眸细看,认出铁丝网样的东西。
“请沿铁丝网直行300米左右,尽头有座仓库。”
“仓库?”
他并不看我,冗自点头道:“哦,大仓库,一眼即可看出。以前是养(又鸟)场的冷库,早已不用了。养(又鸟)场倒闭了。”
“可是有(又鸟)味儿。”我说。
“味儿?…。啊,沁到地里去了嘛。雨天更厉害。扑楞楞振翅声都好像听得到。”
铁丝网里边简直伸手不见五指,黑得可怖。虫鸣都像要窒息。
“仓库门一直开着。仓库主人给打开的。你要找的那台机就在里边。”
“你进去了?”
“一次——”获准进去的。“他叼着烟说,椅红色的火在黑暗中闪烁。”进门右侧就有电灯开关。注意阶梯。“
“你不去?”
“你一个人去。这样讲定的。”
“讲定?”
他把烟头扔在脚下草丛里,小心踩灭:“是的。说想呆多久就呆多久,离去时把灯关上。”
空气一点点凉下来。泥土特有的凉气拥裹了我们。
“见仓库主人了?”
“见了。”少顷,他回答。
“怎样一个人物?”
讲师耸耸肩,从衣袋掏出手帕摄了下鼻:“也没什么特征,至少没有肉眼看得见的。”
“干嘛收藏弹子球机达50台之多呢?”
“这个嘛,大干世界无奇不有,如此而已,对吧?”
我觉得并非如此而已。但我向讲师道谢离开,独自沿铁丝网前行。并非如此而已。弹子球帆收藏50台同标签收藏50张情况有所不同。
看上去仓库俨然蹲着的动物。周围高草密密麻麻。拨地而起的墙壁一扇宙也没有。死气沉沉的建筑。对开铁门上大约是养(又鸟)场名称的字迹上厚厚压了一层白漆。
我从相距十步远的地方抬头看一会这座建筑。无论怎么想都没有好的想法浮上心头。我不再想,走到人口,推开冰凉冰凉的铁门。f1无声地开了,另一种类的黑暗在我眼前张开。
22
我摸黑按下贴墙开关,隔了数秒,天花板荧光灯“咔咔”交相闪烁,白光顿时弥漫仓库。荧光灯总共约有100支。仓库比外面看时的感觉宽敞得多,但更可观的还是灯的数量。晃得我闭上限睛。稍后睁开时,黑暗早已消失,只有沉寂和清冷剩留下来。
仓库看上去确像冷库的内部,考虑到建筑物的本来用途,也可说是理所当然的。一扇窗也没有的墙壁和天花板涂着有浮光的白色涂料,但已布满污痕,有黄色的有黑色的,及其他莫名其妙的颜色。一看就知墙壁厚得非同一般。我觉得自己简直像被塞进了铅箱,一种可能永远出不去的恐怖钳住了我,使我一再回头看身后的门。料想再不会有第二座如此令人生厌的建筑物。
极其好意地看来,未尝不可看成象的墓场。只是没有四肢蜷曲的象的白骨。目力所及,唯见弹子球机齐刷刷排列在水泥地板上。我立于阶梯,凝然俯视这异乎寻常的场景,手下意识地摸向嘴角,又放回衣袋。
数量惊人的弹子球机。准确数字是78台。我花上时间清点了好几遍。78,没错。机以同一朝向编成8列纵队,一直排到仓库尽头墙壁。简直像用粉笔在地板画过线似的,队列整齐得分厘不差。四下里所有物体全都一声不响,一动不动,恰如琥珀里的苍蝇。78个死和78个沉默。我条件反射地动了下(禁止)体。若不动,觉得自己都有可能被编进这兽头排水口的阵列中。
冷。果真有死(又鸟)味儿。
我缓缓走下狭窄的5阶水泥楼梯,楼梯下更冷,却有汗冒出。讨厌的汗。我从衣袋掏手帕揩汗。唯独腋下的汗奈何不得。我坐在楼梯最下一阶,用颤抖的手吸烟。……3蹼‘宇宙飞船’—我不愿意这副样子见她。作为她也是如此……想必。
关上门后,虫鸣一声不闻。无懈可击的沉寂如滞重的浓雾积淀于地表。78台弹子球机将312只脚牢牢支在地上,静静承受别无归宿的重量。凄凉的场景。
我坐着吹起口哨,吹了“跳吧,随着交响乐”的开头四小节。那般悦耳动听的口哨声回荡开来,回荡在无遮无拦空空荡荡的冷库中。我心情有所好转,接着吹下面四小节,又吹四小节。似乎所有东西都在侧耳倾听。当然谁也不摇头晃脑,谁也不按拍踏脚。但我的口哨声还是被整个仓库——包括边边角角——吸进消失。
“好冷!”吹了一通口哨,我出声地嘟囔道。回声听上去根本不像自己的语声。那声音撞上天花扳,又雾一样旋转落回地面。我叼着烟叹了口气。总不能永远坐在这里唱独角戏。一动不动,便觉寒气同(又鸟)肉味儿一起沁人五脏六腑。我站起身,用手拍掉裤子沾的冷土,拍脚踩灭烟头,投进白铁皮罐。
弹子球…。·弹子球。来此不就是为这个么?寒冷简直像要冻僵我的思维。想想看:弹子球机,78台弹子球机。……OK,找开关!建筑物的某个位置应该有让78台弹子球机起死回生的电源开关。——“找开关,快找!
我双手插进牛仔裤袋,沿墙慢慢走动。呆板板的混凝土墙上到处垂着象征冷库时代的断头配线和铅管。各种器械、仪表、连接盒、开关,就像被大力士强行扔掉一样留下一个个空洞洞的洞。墙壁比离远看时滑溜得多,仿佛给巨大的蛤蝓爬过。这么实际走起来,建筑物真是大得很,作为养(又鸟)场冷库未免大得反常。
我下罢楼梯,正对面又一座同样的楼梯。爬上楼梯有同样的铁门,什么都一模一样,我差点以为自己转一周转回了原处。我试着用手推门,门纹丝不动。没有门闩没有门锁,但就像用什么封住了似的岿然不动。我把手从门扇收回,下意识地用手心抹脸上的汗。一股(又鸟)味儿。
开关在此门旁边。拉杆式大开关。一推,地底涌起般的低吼顿时传遍四周。令人脊梁骨发冷的声响。随即,数万只鸟一齐展翅般的“啪嗒啪嗒”声响起。回头看去,但见78台弹子球机吸足电流,发着弹击声向记分屏弹出数干个“o”,弹击声止息后,剩下的唯有类似蜂群嗡嗡声的沉闷的电流声。仓库充满78台弹子球机短暂的生机。每台机的球区都闪烁着形形色色的原色光芒,板面描绘出各自淋漓畅快的梦境。
我走下楼梯,阅兵一般从78台弹子球机中间缓缓移步。有几台仅在照片上见过,有几台在娱乐厅见过,令人发怀旧幽情。也有的早已消隐在时间长河中,不为任何人所记忆。威廉思的“友谊7”,板面上的宇航员名字是谁的?格列?……六十年代韧。巴里的“大沙皇”、蓝天、埃菲尔铁塔、快乐的美国游客……戈德利普的“国王与皇后”,有八条螺旋上升球道的名机。仁丹胡刮得潇洒有致而神情淡漠的西部赌徒,袜带里藏的黑桃王牌……
盖世英雄、怪兽、校园女郎、足球、火箭、女人……全部是光线幽暗的娱乐厅中千篇一律的褪色朽梦。各种各样的英雄和女郎从板面上朗我微笑致意。金发女郎、金银发各半女郎、浅黑发女郎、红发女郎、黑发墨西哥女郎、马昆辫女郎、长发及腰的夏威夷女郎、安·玛格莉特、奥留丽·苏本、玛利莲·梦露·………没有一个不洋洋得意地挺起勾人魂魄的(禁止)——有的从衣扣解到腰间的薄质短衫里,有的从上下相连的游泳衣下,有的从尖尖突起的乳罩底端……她们永远保持(禁止)的形状,而色调却已退去。指示灯像追随心脏跳动似的一闪一灭。78台弹子球机,一座往日旧梦——旧得无从记起——的墓场。我在她们身旁缓缓穿行。
3蹼“宇宙飞船”在队列的大后方等我。她夹在浓妆艳抹的同伴中间,显得甚是文静,好像坐在森林深处的石板上等我临近。我站在她面前,细看那梦绕魂萦的扳面。留蓝色的宇宙,如深蓝墨水泼洒的一般。上面是点点银星、土星、火星、金星……,最前面漂浮着纯白色“宇宙飞船”。船舱闪出灯光,灯光下大约正是一家团圆的美好时刻。另有几道流星划破黑暗。
球区也一如往日。相同的黛蓝色。球靶雪白,如微笑闪露的牙齿。呈星形叠积的10个柠檬黄色奖分灯一上一下缓缓移动。两个重开球是土星和火星,远档是金星……一切安然静谧。
你好,我说。……不,也许我没说。总之我把手放在她球区的玻璃罩上。玻璃冷冰冰的,我的手温留下白蒙蒙的十支指印。她终于睡醒似的朝我微笑。令人想起往日时光的微笑。我也微笑。
好像许久没见了,她说。
我做沉思状屈指计算,3年了!转瞬之间。
我们双双点头,沉默有顷。若在咖啡馆里,该是吸一口咖啡,或用手指摆弄花边窗帘的时候。
常想你来着,我说。心情于是一落千丈。
睡不着觉的夜晚?
是的,睡不着觉的夜晚,我重复道。她始终面带微笑。
不冷?她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