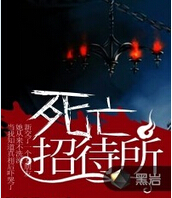死亡拼图-第6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贝弗控制住自己的声音,平静的道:“当代表团团员有意见向大使呈递时,意见是由另外一个人写了转呈的话,这就表示什么?”
“这很简单。如果大使的首席助理,认为有高明的提议或者战略,可以在安理会中驳斥反方的动议,而本人又不在会场的时候,他就可以托另外一名出席的团员代他提出。”
“皮尔斯助卿在星期四与星期五的议程中,由别人替他提出他的建议相当多次,这是表示什么?”
“这就表示当时他并不在场。他平常在联合国中相当繁忙,而且与各国代表的关系也相当良好,有时他必须在开会中途离开会场,去跟其他各国代表接触;老实讲,各国代表都对他相当喜欢。甚至苏联代表团的人,也很喜欢他。”
对,没错,他们当然全喜欢他。这样的话,彼此在安理会针针锋相对、僵持不下之前,可以先在场外进行秘密交易,贝弗心里想到这点。
“我突然又想到一个问题,能再向你请教一下吗?”
“不敢当,先生。”
“卡本特到底出了什么事?”
“我也很想知道。我希望我能找到他。我猜他大概是崩溃了。”
“什么意思?”
“我想您大概还不晓得吧。他太太和儿女在圣诞下前两天,出了车祸,全死光了。你想想看,圣诞树下,没放礼物,却放了三具棺木,他会怎么样?” ,
“真惨,太不幸了。然后呢?”
“出事之后,他只离开了两天,就回来了。当然,我们大家认为这样对他比较好,到人多的地方,大家都关心他的地方,总比一个人要好些。”
“我想皮尔斯助卿对这件事相当帮忙。”
“对,先生。就是他硬说服卡本特节哀顺变,继续上班的。”
“喔。”
“然后某天早上,他突然不见了。隔天就收到了一封他拍来的辞职电报,说他不干了。”
“这不是很不寻常吗?!他为什么本人不来递辞呈呢?”
“我想他是受刺激过度吧。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可能还会顾到什么大体的。”
“当然,皮尔斯助卿在接获电报之后,也就批准了。”
“是的,先生。这是皮尔斯的想法,认为他已经失踪了。唉,我希望他没有什么事情发生,一切都还好……”
他已经死了,小参事先生。
傀儡已经死了。
贝弗挂断电话之后,就继续撑开眼皮查下去,一直弄到旭日东升。
他第二项检查的资料,就是“暧昧”那个代号被偷之后的当晚,“无可救药,径予格杀”的指令,被人由国务院以保防电话打给罗马,对哈洛克展开追杀的时间表。
他一核对之下,就找到他要找的东西了:皮尔斯当天并不在纽约,而是溜回华府国务院五楼他本人的办公室了。他随着下班的人潮,在五点钟溜出办公室签了退,又趁人潮汹涌而出的忙乱之际,重新溜回办公室躲起来,等第二天一早,再趁着大批上班的人潮涌进国务院办公大楼时。溜出去签了到,谁可能会去注意他。就跟他贝弗一样,他现在也可以利用这种方式去签个到,再继续进来工作一样。
可是,这怎么可能呢?从他任何的资料和记录上看,他乃是个典型的美国儿童、少年、青年、学生、军人和公务员,完全是个标准的美国人。他怎么可能会跟苏联有勾搭呢?
到八点钟左右,他因为实在支持不下去,就倒在椅子上睡了。
到了八点三十五分,他被办公室门外,那些一早赶来上班的人声给吵醒了。
他站起来,脸孔浮肿,睡眼惺忪的,穿了一身邋遢不堪的皱衣服,衣冠不整的,带了满头乱发,和颔下窜出的胡髭,开了门,走出去和被他突然出现而吓了一大跳的中年女秘书道了早安。
他从对方吃惊打量他的眼光中,也晓得自己现在是副什么德行——领带没打,卷了袖子,两眼发暗,头发紊乱,一脸胡髭,他晓得。
他叫了咖啡,然后去上了个厕所,再洗了把脸,尽量把自己弄得象样一些。
等他穿过大办公厅,经过那些来上班的秘书和各部门主管时,每个人都盯着他的怪样。
他们还不晓得天都快塌了,他自顾自的想道。
十点钟左右,他记起哈洛克对他的规戒,就上街找了个公用电话亭,挂了通电话到纽约一家电视公司的新闻采访部,请他们立刻将他所需要的录影带和照片,以飞机送到国务院给他。他有点忍不住想报告总统。但他忍住了。他谁也没讲。
现在,他又看了看表。十二点二十二分,离刚才他看表的时间,才过了三分钟。
飞机应该快到了;纽约与华盛顿之间,每小时都有班机对飞一次;问题在于他不晓得是哪一班。
他的思绪把门上传来的一串轻叩所打断,他马上带了十二万分的渴望与兴奋大喊:“请进!”
是他的女秘书,她站在门口,一脸关怀地望着他,与早上她看他的眼光完全一样。“我去吃中饭了,好吗?”
“请便,丽沙。”
“要我带点吃的给您吗?”
“不了,谢谢。”
女秘书很尴尬地楞在门口好一会儿,才鼓起勇气说:“贝弗先生,您没事吧?”她问。
“没什么,我很好。”
“要我帮什么忙吗?”
“别替我瞎担忧,去吃饭吧。”他勉强挤出一个笑容。
“那……等会儿见了。”
她还不晓得天都快塌了,他想。
他的电话响了起来。是楼下大厅安全部门打上来给他的;纽约送了一个邮包来给他。
“请替我签收了之后,加派一名武装警卫送上来给我。”他交代楼下安全室说。
七分钟之后,一卷录影带被放进了录放机中,闭路电视的荧屏上,立即显示出了一个联合国安理会,正在举行会议的画面。
画面下方,有打出—个日期的注脚:十二月三十日·星期二·下午两点五十六分。正在发表演说的人,是沙乌地驻联合国大使。
数分钟之后,镜头开始扫描与会的各国化表团,先是以色列代表团,再就是埃及的,再来就是美国代表团。
贝弗将画面用遥控固定住。四个人都在:大使、旁边坐了亚瑟·皮尔斯,另外两名代表坐在后排。在就好,没必要再听下去,他按下遥控器,让画面因快放而变得模糊了一阵子。等到他手指再一放,沙乌地大使仍在讲话。
他正打算再按下快放键时,突然发现摄影镜头又扫到了美方代表。
亚瑟·皮尔斯不见了。
贝弗连续按了几次倒转键,找到了他想要看的画面。照理讲,在友邦代表致辞之际,中途退席的行为是相当不礼貌的。国务院的这位朋友在离席之前,应该有相当的理由才行。
有了,在那儿。
皮尔斯正在看表,然后站起来,弯身向身旁的大使耳语,接着又转身朝身后那名参事——不是卡本特——讲了几句话;对方点了点头……一名女播音员的声音插进来说:“美国代表团现接外电,可能是由该国之国务卿所打来的。请美方代表派人离场接听。我们猜测,或许美国务卿将对沙国代表伊班·卡沙尼大使的演说,有所补充。”
贝弗马上又按下快放键,按了放,按了放,再按,再按。演说完毕了;许多代表团起立鼓掌。亚瑟·皮尔斯并未回座。
再下去。
一月一日。星期四。早晨十点四十三分。安理会主席主持新年团拜。皮尔斯不在美方代表席上。坐在他位置上的人——应该是卡本特——手中握了一大叠文件。
一月二日。星期五。下午四点十分。一名“中共”代表正在发表演说,所有的与会其他各国代表,都戴了耳机在听。皮尔斯不在美国的席位上。
一月五日。星期一。上午十一点四十三分。皮尔斯缺席。
一月五日。星期一。下午两点十六分。皮尔斯仍然缺席。
一月五日。星期一。下午四点四十五分。皮尔斯坐在椅子上。对也门代表的演说,大摇其头。
贝弗关掉录影机,望了望桌上的那个大牛皮纸信封。老实讲,他已经不必去打开了,也晓得“安理会新年团拜”的那些照片中,绝对找不到助理国务卿之一的亚瑟·皮尔斯的影子了。
那时他正在“布拉瓦海岸”。
只剩下最后一件事,他必须再去查一下。贝弗拿起电话筒;他向“运输部”查问他所需要的资料,揉着眼睛,困得要死的等对方报告过来,身子禁不住有点发抖。
四十七秒钟后,回答来了:“去年十二月三十号,星期二,有五班飞机由纽约直飞马德里。十点、十二点、一点一刻、两点半,还有五点十分……一月四号,星期一,西班牙时间,由巴塞罗纳经马德里飞纽约的班机,有四班,从早上七点半开始的那班,抵达纽约甘乃迪机场的时间,是十二点二十一分;九点半的那班,抵达甘乃迪的时间,是下午三点……”
“谢谢你,”贝弗打断对方。“我要找的资料,已经有了。”
他的确已经找到了。皮尔斯是搭三十号那班五点十分的飞机飞往马马德里,然后于星期一乘那班九点半的飞机返回纽约的,所以他在四点四十五分的时候,才重新出现于联合国安理会的代表席上。反正查旅客舱单,也绝对查不出有位旅客的名字,会跟助理国务卿皮尔斯的大名一样。
贝弗将椅子一转,望着窗外有着行道树的街道,他想从楼上先找到一个电话亭。哈洛克必须晓得这件事。他站起来,走到另一张椅子前去穿外套和大衣,两件衣服全披在椅背上。
房门没有敲一声就打开了,贝弗突然一僵,全身的肌肉部瘫掉了。
把门随手一关,身子靠在门框上,站在那里的人,是另外一名助理国务卿,他前额上方的黑发中,有着一绺雪白色的头发。他挺立着,平视的两眼之中,有着一丝冷酷和倦怠的神色。
当皮尔斯说话时,他的声音冰冷而平板。“你看起来好像累坏了,贝弗,”他说:“而且你的经验也不够老到。疲乏和经验乃是一种很差的组合;容易造成疏忽。你要问问题,也该问得不着痕迹一点才对。那个现在递补卡本特的年轻参事,今天早上有点兴奋过度了一点”
“你杀掉了卡本特,”贝弗说时,几乎发不出声音。“他不是辞职的,而是被你杀掉的。”
“那也没办法,他当时情绪太过于激动了。”
“天哪……你竟然连他太大和小孩都不放过!”
“那天也是环境所逼,不得不尔。当年你在越南时,不是也杀了不少人吗?嗯?有多少?别忘了我也在那里待过,我亲眼看到你干过的事。”
“可是你也在那里杀了……”
“但是我却不像你们那么甘之如饴,把草菅人命当成乐趣,残杀儿童。”
“为什么会是你?!什么道理?!为什么会是你?!”
“因为我有意如此。我们站的立场不一样,贝弗。而我的信念,远比你的还要坚定。这是很容易明白的一件事,就像你现在所看到的这些事一样,我能干得出,而你却无能为力。我能,而且我愿意。世界还有比你们这些人所选择的生活方式更好的一种模式可以生活。我们会让它实现的。”
“凭什么?!凭着把世界炸得粉碎吗?!凭着把我们逼进一场你们设计的核子大战中吗?!”
皮尔斯一听,顿时全身一凛,瞪着贝弗。“这么说,那是真的了,”他冷静的说。“他们已经发现了。”
“你竟然还不知道?……天哪!你竟然还不知道?!”
“也不必自责太深,我们其实也差不多知道了。我们听说——我听说——他已经发疯了。他弄出来的战略,会使得美国陷入僵局,不再被他国所信任。等这些战略全部完成,落入我们手中时,那么美国的生杀大权和死活,就会操纵在我们手里,任我们宰割了。不管你们再怎么欺凌弱小,我们也可以将你们彻底毁灭了。”
“你完全错了……完全走入歧途了,”贝弗喃喃道。“大大的错了,完全判断错误们……到时候我们都必须面对世界末日。谁都逃不掉的!即使是‘那个人’也逃不掉!”
“你却也一样——跟我一样——找不到他,对吧?他把核子大战的蓝图弄出来之后,人就转入地下了。你们也不晓得他到底会给谁看,给了谁看,或者卖给了谁。你们慌得要命。”皮尔斯向前走了几步。
“你也无法找到他。你把他弄丢了。”
“但我们却晓得他是谁。我们研究过他的习惯,他的需要,他的才干。他与其他聪明人一样,复杂,但却可以意料。我们会找到他的。我们晓得怎么去找,你们却不晓得如何着手。”
“谁是‘我们’?莫斯科并不承认有你们这帮人。从‘布拉瓦海岸事件’中,我们已经打听到许多内幕。国安会根本与布拉瓦海岸无关。”
“国安会那群人算什么。他们只是一群过气的老家伙而已;到时候,他们自然会俯首称臣的。”皮尔斯环望了一下贝弗桌上的录影带,以及那个牛皮纸袋。“怎么?花那么大的工夫,费那么大的劲,就是为了想找到—名失踪的外交官吗?”潜伏份子抬起头来。“赫维里柯回来了,对不对?”
“谁?”
“我们还是比较喜欢他原来的本名。米海·赫维里柯。可惜美国人并不太喜欢移民,否则的话,换了个环境,他这么有才干的人,今天可能就是站在我现在的位置了;可惜他走错了路。他已经在这里了,对吧?”
“我不知道你在讲什么。”
“哎呀,得了吧,贝弗。他假如没回来,怎么会把那个叫韩德曼的人杀掉了?你们后来替他把真相掩饰掉,也是想靠他帮你们一把;当然,那个女的,你们一定也已经找到了。你们怕他把你们的内幕全部揭发,所以就笼络他。你把所有的事情,都跟他说明了,对吧?弄来弄去,你们还是得回到‘布拉瓦海岸’去。”
“你才回到布拉瓦海岸!”
“的确。我们一旦在打算跟西方世界中,最最有势力的人打交道。而且我们一定在楔而不舍,谨慎的进行中。你们没这种胃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