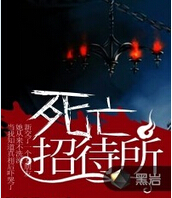死亡拼图-第4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走着瞧好了。”
“她还好吗?”他实在憋不住那种发自内心深处的焦虑与渴望。
“跟别人一样——那些知识分子——一来以后,就发了阵疯……哈!”柯侯德先咧嘴无声的笑了一下,然后才喷出一串狂笑,跟着又喝了一口茶。“我们跟她解说了一下这里的规矩,她说无法接受。你想象得到吗?哈!无族接受!哈哈——”老蛮牛狂笑了好几声,才把声音慢慢放低。“在她被转送出去以前,我们会好好盯住她的,她应该懂才对。别人都懂。”
“这用不着你担忧。我会带她走的。”
“别自说自话。”
“我付过钱了。”
柯侯德身子内前—倾,止住摇椅。“付了多少?”
其实这个问题,他早就想问了。哈洛克晓得这个问题可不容易回答,很危险;纽约那里不会有答案的。他得再跟这个坐在他对面的老粗谈判才行。
“你不会去向韩德曼哪?假如他在家的话,你不就问到了吗?”
“也许我想先听听你的说法呢?老板。”
“你怎么晓得能信得过我?”
“那我又怎么晓得,我能信任得过韩德曼?你凭什么又信得过他?”
“为什么我不能?我不是找着你了吗?虽然被请进来的方式,我不太喜欢,可是我还是照着他告诉我的话,找到你这个地方了啊!”
“可是你总得对我有个交代啊?”
“有什么好交代的?我连身份证都没带。”
“可是真正有办法的,有影响力的人,虽然身份证不带,却会带钞票。”老狮子又开始摇椅子。
“我当然带够了钞票。”
“那么你到底付了韩德曼那个德国人多少钱?”他又不摇了。
“两万美钞。”
“两……?!”柯侯德一听,脸色马上一白,连脖子都扯紧了,眼睛睁得老大。“真不少啊,老板。”
“他说这价钱并没有乱要,很公道。”哈洛克把二郎腿一跷,神得很,他感到裤子被烤得很热。“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你有没有想过,他并没有跟我联络过?”
“凭你们彼此之间的这种复杂的联络方法,你没接到他的通知,也说得通。他当时正要赶往波士顿,当时你这里没人接电话的话——”
“怎么会没人接电话?!电话旁边随时都有人。你晓不晓得就这么闯进来,会把老命丢掉?”
哈洛克把一条腿又放下地。眼睛瞪着柯侯德,“你是指那些电脑?”
“你刚才讲过狗的事;我们的确有很多狗,都是受过训练的,对入侵者,只会围住他,不咬。没命令,绝不会乱动。可是你并不晓得。你如果真遇到了狗,会怎么样?”
“当然只有用枪打啦!”
“你打了狗,你就会被我的人射死。”
“幸好我没这么做,否则我给过德国人两万美金的事,你就不知道了。”
“就是啊。”
“可是他收了钱,不是要和你分享的吗?”
“谁晓得?也许他想独吞,想把钱凑多点,将我这个地方接收下来。”
“我不懂为什么你会这么想?”
“那为什么他不打电话先通知我?害得我差点就毙了一个人?他再忙,急着去波士顿,也该打个电话,或托个人打个电话给我啊!”
“你打死一个入侵的人,一个带了枪闯进来的人,又有什么不对,谁能怪罪你?”
“是没有人能怪罪我,”柯侯德说着又开始摇摇椅。“可是事情也可能因此闹大,话会传出去,说我柯侯德是个老粗,只会惹麻烦,我们组织可容不了我,把我踢出去。”
“从什么地方踢出去?”
对方喝茶不答,沉吟了一下。“你花了两万美金之后,还预不预备再花些钱?”
“这我可要考虑一下。我们要这个女的;她跟我们的‘敌人’有勾结。”
“谁是‘我们’?”
“这我可不能告诉你。即使告诉你,也没什么意义……他们会把你从什么地方踢出去?”
柯侯德耸耸肩。“反正第一步,就是不让我再管这些人……象那个叫克丽丝的女人。”
“那不是她的真名。”
“我晓得不可能是,这关我屁事。反正她先得在这儿做一两个月工,才能送走。送到南部,西南部——中西部,或者北部的那些州去,我们爱送她到哪里,就送到哪里。”老蛮牛又笑了笑,“总之,得等上个把月才行,去贿赂个国会议员,当权的民意代表。这些人得老老实实的等着我们安排好,才能把他们送出去。他们就跟一群羊一样。”
“可是羊也会反抗的。”
“反什么抗?!反抗他们自己呀?把他们往原来他们逃出来的地方送啊?送给枪毙队?还是古拉格群岛啊?你还没弄懂,这票人都是早已吓得半死的人了。任我们摆布,敲竹杠,这种生意好做得很!”
“那么合法证件真的都会行吗?”
“喔,当然,通常都会。尤其是那些具有特殊才艺的,具有创造力的,有得更快。得付个好几年的钱,才能还清这笔债。”
“可是我却认为这种行业还是不保险。那些人可能到后来,会拒绝付钱,用揭发你们来做威胁。”
“那还不简单,我们就再给他一张证明——死亡证明。”
“现在轮到我问你了。谁是‘我们’?”
“轮到我回答你了。我不会告诉你的。”
“可是你不是说,德国佬想把你挤出去吗?”
“很可能。”电话响了。柯侯德马上从摇椅上跳起来,奔过去。“也许我们马上就能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他把茶杯放到电话几上,拿起话筒。“喂?”
哈洛克紧张到几乎快要窒息的地步。韩德曼的大学同事,或是他的房东,他的邻居,可能因为好奇的缘故,去找过韩德曼,发现他死了。还有他研究所的那些研究生。各种可能都有……
“继续试。”喀尔巴阡山人说道。
哈洛克这时才恢复了呼吸。
柯侯德空手走回摇椅。“韩德曼的电话,没人接。”
“他到波士顿去了。”
“你到底还愿意付多少钱?”
“我身上现在带的钱不多。”哈洛克回答时,想到他车子皮箱中的数目。差不多还有六千美金——是他从巴黎带过来的。
“可是你己经给了姓韩的两万大洋了。”
“那是早就谈好的。这样好了,我可以分期付款给你。先付五千。”
“什么分期付款?”
“我坦白讲好了,”哈洛克身子向前弯,用两双手肘撑在膝上。“这个女的,对我们值三万五,上面只发这么多。我已经花掉两万了。”
“再加上五千,那该还剩下一万啊?”
“都放在纽约。你明天可以拿得到,可是今晚我必须先看看货色。今晚我必须带走这个女的。
“也带走我的那一万?”
“我干嘛要这么做?这种钱老子还看不上眼哩!而且虽然你是这么说,可是并不一定你就拿不到韩德曼分给你的钱。狗咬狗,贼偷贼。现在他中泡私囊的罪证已经被你逮到,你就可以把他踢出去了!”
柯侯德哈哈狂笑。“你可真是不赖,老弟,真不赖。有什么保证我可能拿到这些钱?”
“派你最好的人跟我们去纽约拿呀!我又没枪,叫他们用黑管子瞄到我的脑袋瓜,不就结了?!”
“搭飞机主吗?别他妈诈唬我了—一谁能带枪上飞机?!”
“我们开车子去。”
“为什么一定要今晚走?”
“他们明天一早就要她。我必须把她带到纽约的第六十二街转角上,去交给另外一个人,他身上带了那笔剩下来的数目。他会把她从甘乃迪机场,送上一架苏联民航机。你的人到时候可以控制全场;见了钱才放人。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柯侯德又开始眯起双眼摇椅子。“德国佬是个贼,你这捷克佬呢?会不会也是个贼骨头呢?”
“怎嘛?难道还不放心哪?!你连手下最好的人,都放心不下吗?”
“可是假如我就是最好的人呢。假如是我去呢?”
“有何不可?”
“好,敲定了!就这么办!我们一起去,我跟那个女的坐后座。我用枪比住她的脑袋瓜。还有另外的一把枪对准你。两把枪,老板!头款的五千大洋呢?”
“在我车子里。派个人开车跟我去拿,可是得由我亲自拿,他站在我车外等。你不答应,那就免谈。”
“你们共产党一向疑心病很重。”
“那当然不在话下。”
“同乡!唉,我真替你丢脸哪!”
“女的呢?”
“在后面一幢房子里。她拒绝吃饭,把盘子乱砸乱丢,把我那名古巴手下砸惨了。为了利益的关系,我们不得不强迫她吃。也许古巴人已经开始整她了,那小子最喜欢整这种受过高等教育的女人,最对他胃口了。”
哈洛克笑了笑;这个笑容是他有生以来量困难的一个笑容,“门窗都牢靠吗?”
“干嘛?他们还能往哪逃?”
“我想先看看她,然后马上走。”
“有何不可?这样我也好先拿到五千大洋。”柯侯德止住摇椅,朝左边大吼,“你!陪我们的客人到他开来的车子去。叫他开回来,你用枪比着他脑袋就行了!”
十六分钟之后,哈洛克将数好的五千美金塞进了柯侯德的手中。
“去看你的女人吧,老板。”柯侯德说。
他绕过几栋房子,朝那座直立式仓的左边走,拿了他那管“勒马”的汉子,跟在他后面。
“就在那儿,你的右边。”
树林边,有应小仓,看起来象小仓,但却并不是小仓。好几个窗户都亮着灯光,很高——表示它有两层,有二楼。窗上有一根根的黑影,是铁杆。里面的人不可能逃得出来。这完全就是个集中营。
哈洛克可以感觉出他后背脊椎凹处的那把刀鞘,那种硬帮帮的压力,使他非常乐。他晓得要制服身后的那个人,拿到他那把被夺去的枪,是非常容易的——在雪地上滑一跤,那小子就注定要向鬼门关报到了——可是目前还不能这么做。等以后再说,等珍娜相信了他,等——假如——他能使她相信之后。而假如她不相信的话,他们两个人都可能只有死路一条。
听我细诉!听我说,为了我们两个人,为了我们两个还没有疯狂的人——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子对付我们。
“敲门吧。”身后的人说。
哈洛克伸手敲门。一个带有拉丁口音的人,在门内回答。
“谁?干什么的?”
“开门哪,柯先生的命令。我是里安哪。快点。 ”
门打开两三寸,露出一名身穿汗衫大块头的身影。他先瞪哈洛克,等看到后面的人以后,才把门完全打开。
“没电话过来呀。”他说。
“我们以为你这会儿正忙着服侍小娇娘呢。”后面的人吃吃笑了两声。
“拿什么去服侍?!两条猪猡?一个疯女人?!”
“我们就是要找她。他想看看她。”
“那他脑袋最好硬一点,我可不是骗你!小娘儿们我十分钟前才看过,睡着了。我看她大概已有好几天没闭过眼了。”
“那他不正好来个饿虎扑羊!”里安说着,就把哈洛克推进门里面。
他们爬上梯子,走进一条两边都有很多门的长廊,都是铁门,上方中央还有个可以打开往里瞧的小窗孔。
我们都无异被关在一座可以移动的监狱里。是在哪儿说过的这句话?布拉格?……还是巴塞隆纳?
“她在这间里面,”古巴人说时,已站在第三个门前面。“你要不要看一下?”
“把门打开,”哈洛克说,“你们到楼下去等我。”
“他妈的——”
“是柯先生交代的,”穿皮夹克的里安解释。“照他讲的做。”
古巴人从腰上拿下一根钥匙,从把小室的门锁打开,往旁边一站。
“下去,下去。”哈洛克吩咐他们。
两个人只好回楼梯口。
哈洛克开开门。
小室里一片漆黑,反倒是外面比里面亮,窗口有光从屋外透进小室之中。他可以看到她躺在小木板床上的影子。是趴着睡的,脸朝下,衣服穿得好好的,金色的头发披散着,一双手臂垂下来,手指触到地板。她没盖被子,压在身下,衣服很绉,从睡姿和她轻微的鼾声,可以看出来,她已经困顿欲死。看着她,他内心中充满了疼爱与凄苦,心口发胀发闷,想到她这段日子以来的遭遇,他几乎有点克制不住自己的内疚;全是他害的,她才会这么惨。信心丧失之后,只能凭本能残存下去;爱情幻灭之后,他还能象个人那样的活下去吗?他是个畜生!只有禽兽才会这么对她……他简直无地自容。而……又充满了爱。
他可以看出她床旁的那盏落地灯,捻亮它的话,就可以照到她。一股寒意涌上来,令他的喉咙发紧。他曾面对过无数次危险,可是却没有任何一次,比得上这次令他如此紧张、害怕、受惊和迟疑。这一刻比任何一刻都更重要。假如他失去了它——失去了她,他们两个人之间的桥梁折断,永远折断了的话——他只有死。
他发现他没有勇气去打开那盏落地灯,不能……他宁可站在黑暗中去呼唤她的名字,一个字、一个字的呼唤她,将她唤回他的怀抱。
可是,要他拿什么话去讲?要他说什么呢?拿什么去解释呢?这只是一场恶梦……?
他还是决定不把灯打开。他走上去,轻手轻脚的走近床边。
一双手臂突然从黑暗中撞向他,白白的手臂在黑暗中一闪,那双手就击中了他的小腹。他感到被一个尖锐的东西戳中——不是刀,是另一种东西。他向后跳开时,手一低,已经抓住了那支肩膀,半扭不扭的——他绝不能再让她有一丝一毫的痛苦了。他不能再伤害她。
假如她能够,她一定会杀了你的。普莎夫人说过。
珍娜从床上滚下来,她的左腿早已顺着滚势后收,用膝盖上抬的冲力,撞到他下部,尖锐的手指甲,抓向他的脖子,抠进他身上的肉。
他无法反击,他办不到。
她扯住他的头发,硬把他的头朝下按,右膝一抬,又踢中他的鼻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