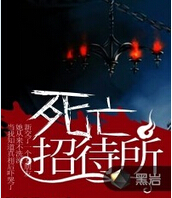死亡拼图-第3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力握了两下,捏紧那只僵硬的手。
二色相间的小跑车,奔驰在马里兰州乡间公路的弯道上,当车子一个急转弯时,车灯照亮浸淫在一片凄风苦雨之中的乡野。
穿大衣戴帽子的那个人,一看到他要找的目标之后,马上就把车速减慢,关掉大灯,让车子滑着停下来。靠路肩栏杆边,停放了—辆白色的救护车,车身两侧喷了“贝斯达海军医院/紧急救护小组/第十四号救护车”的字迹。
小跑车滑到救护车旁煞车停住后,他又象上次那样,掏出打火机亮了一下,旁边那辆救护车的驾驶座车门,立刻就打了开来,跨下一名二十多岁的男子,身上穿了医院发的雨衣,雨衣并未扣拢,可以看到年轻人里面穿了件医院的白制服。
轿车中的人一按他身侧的电动钮,他右侧的车窗就滑下去。“进来!”他放声大喊。“免得你淋湿了!”
年轻人低头钻进轿车,把车门砰然关上,用右手抹了一把脸。他是个拉丁美洲人,黑发、黑眼、褐皮肤。
“你欠我一大笔钱,妈妈,”拉丁人说。“你该给我一大笔,妈妈。”
“我会给你的,虽然我觉得你替我办这件事,只是还我一个人情。”
“怎么说?妈妈少校!”
“上士,你本来在越南要被军方枪毙的,要不然,现在也可能还在军人监狱服刑,每天搬石头呢,怎么?难道你忘啦?”
“可是这不能一概而论,老子替你宰了那个医生!你该给我酬劳!何况当年那件事情要不是我替你跑腿,也不会出事啦!”
“那么我再问你,那次你溜到军医卡车上去偷吗啡,被两个宪兵当场逮到的时候,要不是我刚好在,你会有什么下场?”
“说得好听,妈妈,难道老子运气真的每次都会那么背?!是你叫我去偷卡车上的吗啡的,就是你搞的鬼——才害得我差点没被枪毙掉——就是你害的,少校!”
“你以为我不晓得你现在还在干这种偷鸡摸狗的贩毒勾当?我这几年还是一直在盯着你没放过。你再怎么偷偷摸摸,也逃不出我这对法眼。你替我办事,是还债!”
“嘿嘿,少校,别以我不晓得你的近况。老子上次在电视上,刚好瞧到你从‘联合国’坐了辆大轿车离开。那可是你吧,没错吧?”
“怎么会是我。”
“少来!老子这对眼睛——是白长在我脸上的啊?!会不认识你妈妈少校!你他妈的这些年混得一定很有来头!不但要给我钱,哼,而且还得付一大票才打发得了我!”
“老天,你好像很认真嘛!”
“少啰嗦!钱——拿来就行!”
“可以。先把枪还给我,”穿大衣的人说。“那把枪是我交给你办事用的,该先还给我。这也是为你好,免得从那把枪,被警方查出来是你干的。”
医院男护士伸手掏进雨衣口袋,拿出一把袖珍型的小手枪;与刚才穿大衣的人,在波多马克河畔用过的手枪一模一样。
“里面没子弹,”拉丁人说着就把小手枪摊在掌心。“拿去!”
“递过来给我。”
“自己来拿!老天爷,这里面黑得跟地狱一样,老子什么也看不见!哎呀!痛死我了!搞什么鬼……?”
穿大衣的人在伸手去抓枪时,不小心刮了对方一下。“抱歉,是我的戒指刮到你了。”
“算了,妈妈。钱。把他妈的钞票给我啊?!”
“好——给你就给你。”那人把枪放回大衣口袋后,顺手掏出打火机一亮,只见两人中间的椅垫上,放了一叠用橡皮筋扎好的美钞。“在这儿——五千大洋,五十张一百的——不算算吗?”
“算什么?老子晓得你在哪做事,”医院男护士把车门打开。“以后我会常来拜望你的,妈妈。”
他伸脚跨出去,然后用力将车门关上,走向救护车。
开跑车的人马上挪身坐到右边的位子上,将脸贴在窗上朝外望,同时右手拉住门把,准备一看到对方的反应之后,就冲出去。
男护士才走了没两步,突然身体一软,开始摇摇晃晃向前摔跌,两手大张着想去扶住救护车的车身。他头向上仰。凄厉的惨叫,雨水打在他脸上。三秒钟不到,他就倒在路边斜坡的草堆上了。
穿大衣的男子跳出跑车,走到对方倒地的脚跟前,从左口袋掏出一个皮下注射针管。他把昏死在地上的男护士左手臂抬起来,将他的衣袖卷上去之后,就把握在右手的针管调整了一下位置,对准裸露的手臂插了进去,拇指慢慢压下玻璃针筒,将筒中的液体全部打进对方的身体中。等针打完之后,他顺手拉过对方的另一只手,将连着针头的注射器放进那只瘫软的手掌,再把对方的手指调整了一下,弄出自行注射的握姿,然后用力将那只手掌握紧。
他站起来,向四周望了望,看到那卷压在男护士身体下的湿钞票。然后就朝救护车走过去,打开后门,看到车内的急救仪器放置得很好,随手把口袋中的小手枪重新掏出来,丢到椅垫上,然后又伸手到大衣口袋掏出四个小玻璃瓶。其中两个已经抽空,另外还剩下两瓶是满的。他藉着救护车中的灯光,低头看了看药瓶上贴的标笺;每一张都是一样的字:
贝斯达海军医院
管制药品
成分:C17H19NO2H2O
“吗啡。”
他手一伸,把掌心一松,四个药瓶就咔咔咔咔的四声,掉在救护车的地板上。
突然间,一股狂风扫过来,将这个人头上戴的帽子刮掉了,向他的跑车方向滚过去,他伸手想抓,却没抓到,只好诅咒一声追上去捡。四周虽然黑暗,可是却仍然可以看到他额前方的黑发中,有一撮雪白的头发。
尼古莱·马耶可夫的确是很生气,他不但淋得—身湿,而且连头发也淋湿了,还要去追帽子,弄得他既窝囊,又恼火,而且时间也愈来愈急迫了。
身为助理国务卿之一的亚瑟·皮尔斯,一名当朝大员,照理讲是不应该被雨水淋湿成落汤鸡的;他得赶紧换掉这身湿衣服才能见人。他答应今晚去跟英国驻美大使喝杯酒聊天的。趁喝酒之便,他准备跟对方讨论一点有关“石油输出国家组织”的问题,跟美国有切身利害关系。
这些消息,其实莫斯科并不需要,可是套出一点“英美”之间的石油战备,总是好的。就是因为他们对所有情报都不轻易放过,所以他们这群后起之秀,才能获得自苏联秘密情报头子雅戈达以来,最大的权势。这条路虽然早在半世纪以前,就已经一步步的铺好,可是只要“巴希法”无法找到的话,他们就无法查出安东尼·麦锡所知道的那桩秘密,唯有这个秘密,才能使他们这批俄共中的新秀“渥拿雅”爬上最后的终极目标——为了全世界的利益,他们必须抓到莫斯科的生杀大权。
成长于美国爱荷华州一个农家的亚瑟·皮尔斯,实际上,却是出生于苏联的雷门斯柯村,本名尼古莱·马耶可夫的这个人,在捡回被风刮掉的帽子之后,就转身走回他的小跑车。他很累,可是这场游戏却不能不继续玩下去,绝不能中途停止。行百里者半九十——他说什么也得继续下去。
布鲁斯大使瞪着贝弗助理国务卿。“你是说——这名潜伏的奸细晓得谁是‘巴希法’,比我们还要早就晓得了?!”他大声问。“你凭什么敢这么讲?”
“布拉瓦海岸事件,”助卿说。“还有过去七十二小时中所发生的每一件事。”
“一样样说清楚。”总统命令。
“布拉瓦海岸行动前的最后数小时,哈洛克拿到了一具经过马德里中情局所改造的发报机。哈洛克和马德里的中情局外站,都不晓得这件事。布拉瓦海岸行动,只有一个人晓得真正的内幕,就是行动负责人‘马肯齐’;他是所有秘密行动中最具经验的中情局干部;他是绝对可靠的一名特勤人员。”
“而且毫无后顾之忧,”总统插嘴,“马肯齐从布拉瓦海岸回来后不到二十天,就心脏病发作,死在游艇上了。医生仔细检查过他的尸体,不是他杀,是自然死亡。”
“只有他晓得所有的内情,”贝弗继续说下去,“他雇了条船,两个男的,和一名会讲捷克话的金发女子,然后要她在海滩上又喊又跑,演戏给哈洛克看。那三个人都是贩毒和吸毒的下流胚——两个男的是贩毒的,女的是个婊子——都是花了大钱请来的演员,只要有钱,什么都肯干的那种人。哈洛克发出他自以为是苏联国安会的密码,可是却并不晓得那个发报机是动过手脚的,发出去的电波只能被躲在不远的马肯齐截到。他一收到哈洛克的电讯,就马上发出讯号,叫那三名演员上岸表演。几分钟之后,哈洛克就看到了我们叫看他到的戏,而且信以为真是那么回事。然后,‘布拉瓦海岸事件’就过去了。而整个的内幕,只有总统、两位、和我,四个人晓得,马肯齐事实上只能说是一知半解而已。其他参与的人,则只是听命行事,更搞不清是怎么一回事了。至于其他有关行动各方面的细节,尸体的处理,以及证物等等东西,我们全部都加以彻底毁灭掉,避而不提了。马肯齐再一死——真正唯—的局外人——就只有我们四个人晓得真相了。”
“你说的马肯齐,或许只能称之为‘唯一局外的男人’吧!”海雅中将修正对方。“却无法掩盖那‘唯一局外的女人’。因为珍娜·卡拉丝晓得。她虽然逃掉了,可是却一定晓得真相。”
“但她只晓得我告诉她的那种说法,我就是那名到巴塞隆纳去找她谈话的人。我告诉她的故事,具有双重目的。第一,唬住她,吓住她,要她完全按照我们的要求去做,以便保住她的性命;第二,让她因为惊吓过度,而心神失常,以便令哈洛克产生警觉,认为她举止神秘可疑,而易于倾向说服自己,认为她毫无疑问的是苏联派来卧底的双重间谍。”
布鲁斯大使轻轻吹了声口哨,才说,“好啦,保密保到后来,竟然在七十二小时之前,会有个电话——追查不出到底谁打的——打到罗马去啦,偏偏代号用的又是史登局长建立的那个代号。”
“而且,从现场报导回来的消息说,十二分钟后,又发生了一次大爆炸。炸弹明明是些炸掉她乘的那辆轿车的。”海雅中将接口说道。
“何况,已经有明显的迹象显示,除了我们直接由罗马派到‘莫里涅山口’去的两名干部,和那名突然冒出来的科西嘉杀手里奇之外,还有另外的两名炸药专家,明显的也是由罗马派去的。”贝弗接下去说。
“他们是被我们的人派去的,”总统说,“可是却绝非是属于我们的。他们三个是由华盛顿这里的某个人——那个引用‘暧昧’代号的神秘人士——私下派去的。”
“而这个人也正是与莫斯科有牵连的人,他显然也晓得‘布拉瓦海岸事件’的详情,所以才怕哈洛克和珍娜·卡拉丝这两个人,会把涉及安东尼·麦锡与‘巴希法’之间的秘密揭穿或泄露出去,因此他也急着想把这一对男女加以灭口,顺便也把史登、道森、米勒、还有华伦四个陆续先干掉。”
“为什么?”中将问。
“因为他怕我们从‘莫里涅山口’往回追查到罗马,再往回追查到华盛顿,会泄了他的底。”
“这倒是真的。”中将说。
“我除了如此推测之外,别无他途可想,”贝弗说,“然后,他假传圣旨给罗马,要华伦转达格杀哈洛克的命令;又另外派人去执行炸死珍娜·卡拉丝的行动,双管齐下,一箭双雕。”
“而你认为这个下达那个命令的人,之所以会晓得这些内幕,是因为——你认为——他那天晚上也在布拉瓦海岸吗?”
“绝对有这种可能,是的,将军。”
“老天,为什么?”
“因为他也晓得珍娜·卡拉丝本人并没有死在布拉瓦海岸。”布鲁斯接口替贝弗回答。
“可是照理说,那应该是不可能的,马肯齐雇的两个人是毒贩子,打死的又是个妓女,而他后来拿回来的各种证据,不都是已经证明卡拉丝死了吗?除非马肯齐在死前,曾经把这件事的内幕泄漏出去过。”中将还是不太相信。
“我不认为,”助理国务卿说,“我认为,这个利用‘暖昧’代号搞鬼的人,早在三个月以前,就已经扯上‘巴希法’了。而且他也晓得该去注意哪些事情,所以当哈洛克以四一○最高机密指令到马德里去时,他就已经警觉到了——”
“这表示他是国务院里高阶层中的一员,”大使半途插进来说,“他是某个能接触‘极机密’资料的人。”
“对。所以他才能盯住哈洛克,晓得有某件事正在进行。因此他后来也就一路跟踪哈洛克飞往西班牙,在马德里盯上他,然后又跟他回到巴塞隆纳。那时候,我刚好在那里,马肯齐也在。他当然一眼就认出了我是谁,而我与马肯齐当时曾经碰过两次面,显然他也看到了。”
“既然他发现你在那里,他当然也可以收集到马肯齐的资料,将它一并转送莫斯科了。”老大使上身前倾着说。“让苏联也晓得你们一定有什么秘密行动在进行之中。”
“是有这种可能。没错,一定是如此。”贝弗承认。“也就因为如此,所以我才想到,必须再把所有的记录详查一遍。今天一早,我到国务院秘密行动用的‘机密档案库’,把哈洛克当初对布拉瓦海岸的目击报告,与其他有关的资料,全部都抽调了出来,拿回家重新再仔细看过了。一直研究到下午三点——同时再把当初马肯齐由巴塞隆纳返国述职,用口头对我所做的报告,彼此详加参照比对,结果,果然被我发现到一些出入。”
“那方面的?”大使问。
“就是马肯齐原计划的行动方案,与哈洛克在现场实地所目击的,有出入。”
“你刚才不是说过,哈洛克看到了我们希望他看到的戏了吗?”总统问他。
“他可能比我们想象他所能看到的,看到了更多的细节,远比马肯齐原先设计的剧本还要多的情节。”
“可是马肯齐不是也在那里吗?”中将反驳,“你到底在讲什么啊?!”
“马肯齐当时所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