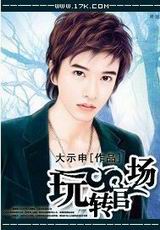官场文化与潜规则(道破天机)-第16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实际价值的道歉是法理政治制度中的道歉而不是伦理政治中的道歉,不夸大不缩小;具有现代特质的道歉是边界清晰而不是边界模糊的道歉,那种含糊而沉痛的道歉,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只有这样,道歉才会成为官员有效问责的动力,才不至于成为官僚阶层自我掩饰的工具。
在西方成熟的制度下,官员引咎辞职多数并不是基于制度规定,而是根据政治惯例。它的更深厚背景是沉积多年的政治文化。
在中国,还没有形成有利于“可问责政府”的官场文化和政治氛围。官员的道歉,实际上仍然是“一切听从组织安排”。
真正的“问责”,既来自于制度的硬规定,也来自民众与舆论的软压力,还来自于官员自身的道德自觉,以及更为深厚的政治氛围。如果仍然是“组织安排”,就不是人们期待的真正的“问责”。
问责的困境,是当前行政体制中责权不清之弊。在每一部门和每一官员不能明确自己的权力和责任、也无法通过恪尽职守避免失误发生的情况下,仅为平民愤而去问责,难以令官令民心服口服。
事实上,在权责过多集中于政府,政府权责过多集中于某一人的现状下,单就某一个人而言,制度安排很难实现其责权利的平衡。
问责的机制是通过上下互动,即上级与民意的互动来对官员施加压力。这种压力如果力道不当,则可能适得其反。
科学的问责制度的前提,是合理地配置和划分行政权力,以及合理的官员进退制度,而这有待于更深刻更全面的制度改革。
官员问责制度是西方政党政治的产物,其中谁来发动这个程序至关重要。在中国,这种政治责任的追究并不是由民众来发动的,仍然是属于传统的“自上而下”的组织处理。
权力架构是一个金字塔型,对权力的监督应该是一个倒金字塔型。尤其是对主要领导的监督,倒金字塔是多层次的,全方位的,如果大家都认为官太好当了,那么可以肯定地一个重要前提,就是问责的太少,甚至可能没有问责,才会出现“越是大官越好当,越是小官越不好当”的现象。
问责制度是民主政治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宪政民主政体下有限政府和责任政府的一个重要实现途径。宪政体制下的责任政府的首要责任就是:对其所做的一切,就与国家相关发生的一切,向公众有所交代。
“谁来问责官员?”
官员问责,现在成了大家共同关注的焦点。到目前为止,从2003年至今的几次大的官员问责的实际案例中,几乎都形成了一个固定模式,即发生了重大事件,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然后由中央派出工作组进行调查,再宣布处理决定,除了事故直接责任人外,再由主管的高官引咎辞职,承担政治责任。
目前,在官员问责的实际案例中,之所以出现上级、尤其是中央成了问责主体的现象,一个原因是中国的政府管理体制仍然受到几千年来所形成的官员权力纵向授予关系的传统影响。虽然从总体上说,当代中国政府其权力来源于人民,也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予以保障;但是,在各级政府之间,则更多的是下级对上级的绝对服从。虽然在各级地方,也有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但是他们对于各级行政部门,也就是狭义政府的监督是非常弱的,各级政府依然受到上级乃至中央政府的制约;在这种体制下,官员问责制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官员”问责制——官员之间的互相问责。这种问责的特点有:
中央到地方,随着行政层级的降低,一般而言,问责的动力是趋向于弱化的。也就是说,只有中央的问责冲动是最强烈的。
官员之间问责的可预期性不强。目前的问责主要局限于重大安全事故和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同时官员之间的问责,往往充满隐讳和波折,民众未必充分了解内情,因此对官员虽然有“问责”,却尚未形成制度,远不是常态的政治生活规则。
官员问责,官员成了问责的主体,上级问责下级,中央问责地方,这种由上而下的问责固然有它高效率的一面,但是依然无法排除它受制于上级和中央的视野局限的不足,以及所带来的事后追究的弊端。
官员问责制最早出自于西方。一般所说的官员问责,指的是:并非由于官员直接造成的问题而去职。官员问责与所谓的责任政府原则是密切相关的,它不仅要求政府考虑人民的利益,而且要求政府对人民解释、说明其决策的目的、依据及结果。
官员问责制有四个层面:一是道义上的责任,向受害者和公众负责;二是承担政治责任,向执政党和政府负责;三是承担民主责任,向选民负责;四是承担法律责任,向相关法律法规负责。
谁来问责官员,即官员问责制的主体到底是谁,如何保障主体的权利。
我们的政府是“人民政府”。世界上所有的现代政府,都是民选政府,也就是其权力来自于人民,用经济学的术语说,就是民众与政府的关系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人民把治理国家、维护人民生命安全和社会秩序的权力委托给政府官员,即公务员;由他们代理民众去处理各种公共事务,由此可见,政府的权力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那么,民众也就理所当然的成为问责的主体。如果权力的授予者没有对权力的监督权,那么这种授予也就成了剥夺,因此,官员问责是否能够真正常态化,而不是由风暴最后变成过眼云烟,关键就要看民众是否真正成为官员问责制的主体。,是否由民众起来问责官员。
我们目前的官员问责能否真正保障民众的问责官员的权利呢?
问责的前提是知情,没有知情权的问责权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从宪政民主制度的角度讲,知情权是指公民接受、寻求和获得官方所掌握的情报信息的自由和权利。知情权能契合于现代社会并且其重要性日益突显的原因在于该权利之客体的“情报”、“信息”的巨大价值。公民是否占有以及占有信息的多少直接影响其参与管理国家和实现自身利益的程度。知情权的客体应当包括国家机关所掌握的一切关系到公民权利的利益、公民个人想了解或者应当让公民个人了解的各种信息。
那么如何才能保障民众的知情权呢?关键是要保障公共舆论的相对独立性,因为公众自己是不可能去主动获取各种资料的,主要还是要依靠各种媒体,既包括传统的大众媒体,也包括新兴的网络媒体。如果正式的媒体不能承担起向广大公众传达真实消息的功能,那么就会有非正式的媒体来承担这一功能,这就是我们俗称的流言。流言的内容未必是错的,但是流言是无法纠错的,当公众通过流言获取信息时,其对政府的压力也是非理性的。
“公共舆论”的核心,是舆论来源的非官方化。无论东西方,在传统的封建王权社会中,都没有今天所谓的“公共舆论”,有的不过是官府对民情的调查和对百姓的教化。金字塔的权力结构,与金字塔型的信息流动结构唇齿相依。朝廷从来将信息控制视为维护统治权的重要环节。信息的官方垄断和控制,造成了官民信息的高度不对称的社会结构。这种本来由特权之手建构出来的社会结构,被提升成“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的普遍永恒的客观法则。官员为保持自己的“上智”地位,本能地追求垄断和信息控制。而在“公共舆论”时代到来的今天,这种官场本能的表现所能产生的唯一效果,不过是向社会不断展示着一些失职官员的自私与恶意。
今天中国,,网络的迅猛发展给非官方声音的传播创造了巨大空间,官方媒体吃市场饭的趋向也迫使它不得不面对公众传播,舆论的主人悄然由官场向公众转变。“公共舆论”时代的到来,打破了信息的官方垄断与控制,社会的信息流动从金字塔结构向网络结构转化,信息平等的力量开始冲击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任何制度下都有问责制。官员问责制,古以有之。而公众问责制,则是“公共舆论”时代的产物。皇位上的君主,由上到下授予官员权力,形成层层人生依附关系,君主是主子,官员是奴才。
有不少学者批评,今天中国开始推行的所谓问责制,还是由上到下的问责制,是上级官员对下级官员的问责制,不是公众对政府的问责制,因此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问责制。
其实,权力由谁授予,就应该由谁来问责。在权力授予的主体和程序没有转变的情况下,强调所谓的问责制,当然只能是上级官员对下级官员的问责制,最多不过是强调上级的权威而已。
“公共舆论”时代的到来,标志着上天将权力交给了公众,标志着民权革命时代的到来。民权革命的根本指向,就是将由上到下的权力授予制转变为由下到上的权力授予制,就是将问责的终极主体由君主转到公众,就是将君主问责制转变成民主问责制。“公共舆论”时代摧毁了信息的垄断与控制。近年来,那些失职官员被问责的背后,都有强大的公共舆论问责的压力。
真正的引咎辞职应该基于政治责任、职业道德、良心、愧疚感和羞耻心,应该是自觉、自愿、诚恳、主动的行为,而不是在保职无望的情形下,把辞职当作无可回避的惩罚来被动的应对。引咎辞职是“自罚”而不是“他罚”,是官员主动承担责任的一种常规方式。主动的辞职说明了曾经失察、失职的官员尽管在职务上有所缺失,却没有失去职业操守,没有丧失良知和勇气。
在任何组织系统中,高低不等的权力和职务,是与大小不同的责任和义务相对应的。党政组织的成员要尽忠职守,就必须对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负责,不愿意负责任的就别去做官,负不起责任的就尽快走人,这就是权力和责任对等的简单逻辑。
中国的党政官员辞职一直是、也仍然是极其罕见的事情。失去民望的的官员主动辞职仍然只是个案,并未形成制度性的常规。通常的情况是,行政级别牢不可破,官民区隔壁垒森严。在此地捅了篓子,就到彼地去做官;在此部门做不下去了,就到彼部门去做官;丢了实权的,还要保留级别待遇,候补待用;如此一来,官员辞职,除非等到中央震怒,身败名裂,谁也保不住的时候,才真正丢官罢职。
亲自面向公众道歉是引咎辞职者必须的一个程序。引咎辞职是一种道义上的愧疚。在西方国家,这种愧疚指向普通民众,因为他的权力来自于民众。但在中国,引咎辞职者是背向民众,而向他的上级领导递交辞呈,他们的愧疚指向上级领导。这和官员的权力来源有关,他的权力来自哪里,他就会对谁负责。
既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为什么官员又拥有权力呢?其合法性就来自人民的授予,无授予既无权力。
要承担责任,首先就必须权责划分明确。但中国的政治并非如此,比如,政府实行首长负责制,但实际上是党委领导下的首长负责制。在实际的政治运作中,由于党政不分,各级党委拥有重大问题的决策权,可人大和选民既不能罢免党委成员,也不能在法律上要求党委或者书记承担行政责任。一旦出现决策失误或者领导无方,从宪法和法律上讲,由书记承担政治责任缺乏宪法和法律依据,只能是由行政官员承担责任。
可是这样一来,就会凸显行政机关与党委之间的矛盾。因为一旦问责追究的是政府首长的责任,那么,处于幕后的党委的责任,就自然而然地成为疑问。作为亦步亦趋的执行者遭到处理,而真正的决策者却可以逍遥法外,是难以让行政官员心服口服的。问责制向深处发展,党与政之间的矛盾因此也就会显得更加突出。这就意味着将逐渐导致党政关系从量变发生质变,由中共自身来积极推进宪政体制下的问责制,恐怕需要更大的胆识和毅力。
无论是选举产生的官员,还是人大任命的官员,都不应该有行政处分一说。他们承担的只能是政治责任,要么继续任职,要么下野。他们的责不能由行政机关来问。可以说,无论是记过等行政处分,还是责令辞职,都不是宪政民主意义上的制度创新。而为中国舆论所赞赏的“引咎辞职”也无法成为法律上的规定,因为把“引咎辞职”写进法律,那就意味着可以强制政府官员等于自证其过。
因非典灾难而开启的问责制,给我国公共权力监督提供了新的手段,并迅速走向制度规范阶段。这与我国加快政治文明建设步伐,落实执政为民目标是一致的。
推行问责制的首要意义,在于用制度强化和确保权力的公共属性。我们党始终强调的是,权力来源于人民,服务于人民。但在具体实践中,确实存在着少数公务人员“敷衍塞责”的现象,存在着公共利益被忽视的现象,存在着公共权力没有服务于公共事务的现象。问责制从目标到整个规范、程序的设计,都始终围绕着确保权力的公共属性这一目标。
推行问责制,还将推动公共权力的现代化转型。现代化社会对公共权力的要求有其自身的特点,首先,权力要有明确的边界。其次,权力要有明确的分工。只有做到了这两点,才可以将权力明确到人,才能落实好问责制。从转变政府职能的要求看,目前依然一定程度地存在“缺位、越位、错位”的问题,依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党政不分、政企不分的情况。在推行和完善问责制的过程中,梳理、明确、定位权力的边界,将有助于推动我国政府的现代化转型,也有助于推动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步伐。
推行问责制,还有助于公务人员以更高的要求约束自己。按照权责统一的要求,权力的授予就意味着责任的授予,行政机关及其公务人员,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不能只讲权力,不担负责任,要在勇于承担责任的同时正确行使权力。而与法律和纪律的约束不同,问责制还具有“道义约束”的特点,被问责的官员,不一定触犯法律,违反了纪律。只要没有尽力履行职责,或履职能力不足,出现问题后,都在问责的范围内。因此,各级官员及其他掌握公共权力的人员,必须积极作为,以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