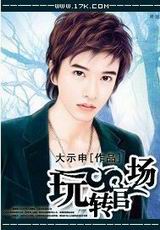官场文化与潜规则(道破天机)-第13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使是国有资本,由于在代理链条的“下端”代理人几乎获得了与私人资本同样的权力,并且在若干方面模拟私人资本的经营方式,客观上存在劳动要素被侵害的可能性。而在转型经济体制中,虽然按劳分配依然被强调为主体地位,但相应的体制设计还很不完善,甚至有些方面存在严重“缺位”现象。特别是劳动集体谈判的权利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使得劳动要素在参与分配过程中始终处于弱势地位。国有企业工会组织基本作为企业“职能部门”存在,在维护职工利益方面往往受到企业管理层的掣肘;大量的非国有企业还没有工会组织或徒具形式,劳资矛盾协调机制严重缺位。
政府职能的缺位、错位和越位
中国在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政府职能已经发生了重要转变,但相对于经济市场化进程而言,这种转变还仅仅是初步的,甚至在主要方面是滞后的。集中表现为政府职能的缺位、错位和越位。中国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中,新体制因素主要是通过传统体制外的“增量”方式发展起来的,计划体制内的变动相对要滞后,特别是大量的国有企业如何转型尚在探索之中。一方面,“体制外增量”的长足发展奠定了市场化资源配置的基础,并日益向“体制内”渗透和拓展;另一方面,“体制内”国有企业、国有银行和政府之间的关系盘根错节,政府还难以“超然”于市场之外。这种情况意味着,体制转型中的市场主体“身份”在一些领域常常是模糊的,市场主体地位不平等以及交易过程中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往往对竞争结果具有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因素。
就收入分配关系而言,在政府依然介入市场较深的情况下,必然制约政府在维护市场主体平等权利、保证公平竞争方面职能的发挥;同时也影响到政府再分配职能和公共政策对社会收入分配的有效调节。目前社会反映强烈的教育、医疗、住房以及社会保障等问题,是一个突出的表现。
资源的行政性配置在任何社会都是存在的,但由于权力运行的特殊性,为了维护市场公平竞争和效率,同时也为了防止权力“寻租”性腐败,成熟的市场经济都严格限制其介入的领域,并且对权力运行规定了公正透明的程序以利实施有效的监督。
中国在体制转轨中虽然大幅度减少了行政性资源配置,但行政性资源配置不仅在国有经济部门依然普遍存在,而且近年来已经出现向非国有部门渗透的迹象。在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条件下,行政性资源配置的权力具有了“价格”意义,因而“客观上”存在着权力市场化的可能。从80年代中期利用产品“双轨”价差牟利,到90年代要素市场化中的“寻租”,人们不难观察到大量权力市场化的现象。近年来,在城市改造拆迁和土地转让、资金信贷以及资本市场“圈钱”等领域,权力市场化的现象依然没有止步的迹象。
行政性资源配置中的权力市场化是社会财富占有和分配不公的最主要因素,其负面影响要远远大于市场调节机制本身的缺陷和社会调节机制的不完善,而且还使后者产生严重扭曲。权力市场化导致了许多领域仍然是血缘和裙带关系盛行,抑制了基于企业素质和个人能力的公平竞争,市场运行中的优胜劣汰机制往往演变为逆向淘汰。
权力市场化现象的根源,是对权力运行缺乏有效的体制性制约机制,特别是在经济转型期体制不完善的情况下,少部分掌握公共资源配置权力的人甚至可以左右逢源,很容易地利用权力来交换、攫取自身利益。
主流经济学家几乎成为今天社会分配不公平现象的道德承担者。公众对他们的批评是,为利益集团说话,牺牲弱势群体的利益。
经济学家是否必须是没有个人利益欲求的道德圣人,是否必须是完全立场中立的人?在一个健全成熟的社会,经济学家当然可以有自己的立场,可以为利益集团说话。事实上,在西方国家,在公共决策层面表达不同观点的经济学家,利益或者价值阵营是非常公开的。
中国经济学家程度不同地卷入为利益集团说话的现象,说明社会需要经济学家为不同的利益集团说话。一个正常社会,总是存在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纠纷和博弈,这种利益的博弈,通常靠的是政治层面上的代言人来实现,但往往也离不开有人从影响经济决策的角度为之代言;尤其到了微观的经济问题层面,经济学家的代言和服务就非常重要。虽然从学术角度上说,经济学家研究的内容通常总是效率问题,似乎天然容易站在强势集团一边,但经济学发展到今天,同样有从弱势群体角度考虑问题出发的福利经济学家。更重要的是,一个社会的公平与效率的兼顾,更依赖与利益集团在政治上的博弈,而不仅仅是各种不同经济学家声音之间的平衡。
经济学家的社会定位更具有“工具知识分子”的特征,尤其是对公共决策的影响力。涉及公共利益的宏观决策,在西方国家是政治上的“多数同意”,民意决定政府在不同经济学家的声音中“购买”谁的,而不是象中国那样直接向政府建议的方式影响政府决策。这种社会定位的差异,使得在西方社会的经济学家和法学家一样,既有纯学术的一面,又有成为服务和受雇的一面。
强调经济学家的公有制身份与其主张的矛盾,并非凸显其言行上的自相矛盾。中国今天已需要象律师一样自由寻找雇主的经济学家,但他们在满足这种需求时,实际的身份却是“法官”。换言之,如今的经济学家在中国的权威地位,并非来自其纯粹的学术地位,而是来自体制所赋予的国家和政府机构的权威和公信力。
正是经济学家这种身份与行为的矛盾,使他们在享受不正常的风光时,也承担了更多的社会道德要求。媒体对专家、学者的言论主张与社会不公正之间的道德联系,多少是知识分子对自己社会作用高估的一种错觉。因为言论和主张并不能真正改变社会力量对比。社会决策能否公平、公正,主要来自社会群体之间力量的均衡;而在中国,则是弱势群体在公共决策中是否存在议价能力,与经济学家的良心并无太大关系。
今天集中体现在经济学家身上的各种矛盾,其实是政府公共决策的形成过程、监督过程,以及社会各阶层利益的代表与实现等一系列牵涉政治层面的制度不完善的集中折射。
中国应当加快相对经济改革已经严重滞后的政治体制改革,以避免改革进程的中断和倒退。必须通过政治民主建设和完善使社会各阶层的利益都能充分得到体现和代表,增进弱势阶层在利益分配和博弈中的政治议价能力,改变今天出现的改革成本承担者和受益者不对称的局面。
尽管民众、官方和学者对“中产阶级”的界定很不相同,但这个群体的出现看来是公认的。不仅如此,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现状,让“中产”不再单纯是一个收入的概念,而被赋予了政治的、文化的、道德等多重涵义。一个流行的理论是,中产阶级是社会的稳定器。中产阶级越庞大,社会就越稳定。因为中产阶级渴望保持稳定,不希望激进的变革。
然而,这个被认为拥有强大力量和光明未来的阶层,却正在经受着难以言说的困惑和疼痛。计划经济下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滞后,前几代人的贫困并没有给这一代人留下多少可继承的资源。
目前我国的房地产市场发育很不成熟。眼下在这个领域里大行其道的往往不是诚信、不是法律,而是开发商和少数特权者的合谋。在城市,政府垄断住宅用地供应,政府又只向房地产开发商供应土地,市民不能获得土地自己直接建造房屋。于是,在城市,先有开发商,再有房子,然后才有业主。业主是由开发商创造出来的。在开发商交付房屋之前,根本没有业主。这些成为业主维权的先天劣势。
导致维权出现的常见问题,归根到底是经济利益的冲突,但十有八九,它们最终会演变成为社会问题,甚至会导致流血冲突;
而从根本上看,“单位”对个人的影响虽然减弱,但国家通过掌握的主要经济资源和项目审批权、对各类新经济精英、知识分子等的政治地位的决定权等各种手段,某种程度上重建了对社会和个人的控制。不能忽略的是,这个社会最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资源,始终还掌握在国家和政府手中。对这些资源的掌控和运用,对个人的维权行动往往有釜底抽薪的作用。
种种迹象表明,目前在中国被炒得很热的“中间阶层”、“中产阶级”等概念和说法,只是在某方面与西方中产阶层的特征有些类似,仅仅是种“雏形”,距离成为主流社会价值观的主体力量,还有相当艰难的发展路程。
中国经济改革陷入困境源于权利与权力的错位
中国的改革,成功于农村的土地经营权承包,失败于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这就引出了一个令人诧异的问题:同样是“产权改革”,为何前者成功,后者失败?
始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最初是着眼于政府“下放权力”,后来逐渐聚焦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共十四大决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提出了“清晰产权”。
按理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这个进程,完全符合经济体制转型的逻辑,也是所谓“渐进式”改革的真实写照。因为,我们不难理解,二十多年前,在计划经济体制还没有松动、经济改革还没有赢得人心、思想启蒙还处于“完整准确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邓小平语)那个层次的时候,谁说要“搞市场经济”无异于离经叛道,且很难获得广泛的社会舆论支持。
然而,令人诧异的是,在所谓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竭力推动下,中共十四大以后,当那个作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核心内容的“清晰产权”被赋予实施之后,中国经济改革的面貌突然发生逆转。这些年来,急剧攀升直至远超国际警戒线的基尼系数、在严酷镇压中仍然风起云涌的民间维权个案,为中共十四大以来的改革提供了一幅简洁而生动的写照。
由权贵主导的产权改革给普通民众带来了一场浩劫,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仅以最近两年为例,除了我们知道的太石村血案、汕尾血案之外,不到半年前,在上海闵行区,还发生因征地引起农民自焚的惨剧;就在一个多月前,在上海市的顶级中心城区黄浦区,也就是最近被撤职并立案审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的发迹地,一名居民因不满住房动迁后的补偿,持刀冲进动迁组的办公室,造成了一死两伤的悲剧!
这场浩劫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
用产权经济学的方法来分析,动迁居民至少拥有两个权利:第一,参与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的权利;第二,作为原住民,从城市中心地段搬往偏远地区居住后,获得级差地租收益补偿的权利。第一个权利来源于“先占原则”,这是由自然法理论演化出来的,在财产关系上广泛应用的一个法律原则。因为,孙长征兄弟在居住之初,此地并无商业开发价值。随着这个地块升值,作为原住民,有权分享增值的部分。第二个原则则是我们熟悉的“公平原则”。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城市居民的动迁可以不遵循上述原则,一句“无私奉献”就可以在理论上“摆平”。而现在动迁居民所面对的,不是国家而是大大小小的开发公司,对于这些以赢利为目的的开发商,有什么理由要靠劳动吃饭的老百姓对他们无私奉献呢?进一步说,既然政府口口声声是说是按照货币化办法而不是行政性办法来动迁,那为什么又闭口不谈“补偿原则”呢?
或许有人会说,承办动迁的并不是开发商,而是政府。上述原则未必适用。果真如此,问题就更大了:明明是开发商的商业性动迁,那让开发商同原住民去谈好了,政府在一旁仲裁,有何不好?为什么非要横插一扛子呢?这不是有意为寻租创造条件吗!
至此,我们不难看出,其所以孙长征们缺乏谈判能力,其根源就在于他们应该具有的“参与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的权利”和“获得级差地租收益补偿的权利”没有凸显出来,政府有关部门对于当事人的这些权利,没有一个说法。虽然孙长征们感到懊恼,但他们除了抱怨动迁费太少,在南京市买不到房子之外,却也不知道依据什么,以及如何去伸张自己的权利!因此,政府也就用不着对当事人和社会公众交代,只是通过暗箱操作,冒出一个莫名其妙的“每平方米补偿3750元”来,叫孙长征兄弟两家五口人如何消受?
与孙长征们权利不清相对应的,是政府方面的权力扩张。
我们已经看到,上述纠纷发端于南京市的市政建设工程中。在中国,市政建设毫无疑问属于政府的行政行为,所以,执行动拆迁任务的机构才被命名为“拆迁办”,同那些林林总总的什么“计生办”、“文明办”一样。
那么,作为政府,在实施自己的行政行为时,同利益受到损害的公民一方发生冲突的时候,应该如何处理呢?换句话说,政府行政权力的边界在那里呢?
在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国家,当遇到这类没有法律依据而无法诉诸法院的纠纷时,可以向一个独立的第三方机构申诉来调解。比如,一名病人住院之后要支付费用,决不是仅仅由医院开账就要病人付钱,一定要经过一个中立于病人同医院之间的第三方,审核用药的合理性之后,才由病人付钱。道理很简单,如果医院开具的费用不经过独立第三方审核,医院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怎能保证它不滥用昂贵药品以谋增加收益?
而那个管辖拆迁办的南京市政当局,主要承担着改善南京城市形象的职能,其官员的政绩乃至升迁,均取决于城市形象工程的进展,它当然对尽快拆迁有着超强的冲动。这种“寻租”冲动可以被堂而皇之地掩盖在“改善城市形象”的职责的幌子之下,而实现这种“寻租”冲动的行政权力又不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