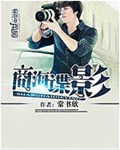商海情仇-第3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一到冬天,姑妈的病就加重。”边说边倒药,又掺了水继续熬,“吃了好多药都不见效,唉……”老曹重重叹口气。
郑戈仔细端详他,个子不高,很瘦,中分头,三角脸,额头很宽,浓黑的八字眉下一双大眼很亮,鼻子很尖,鼻翼两边饿纹(相书中讲的法令线)很深直切嘴角,尖下巴,天生一副哭象,照相书里讲,此人上克父母,下克妻子儿女,乃终生劳碌不得饱食之相。
文俊问:“兴元,厂里近况如何?”老曹苦笑,说道:“样机出来了,已经通过有关部门鉴定,工艺先进性能良好,很有实用性,但要投产还缺资金。”文俊说:“有没有订货?”老曹说:“订货不少。”郑戈说:“既然有单位订货,就收预付款嘛!”老曹咳了一声嗽,说:“订货方答应给预付款甚至全款,但要求降低售价。这个产品利润本来不高,售价降低利润就更薄,关键是以后就不好提价了。”文俊沉吟了一下说:“我借点钱给你……”
老曹回绝了:“不,不!上次借的还没有还,咋好意思?何况现在资金需求量大。”
文俊说:“那你咋个办?”
老曹答:“我正在想法找一家大型企业作突破口,要他们在不压价的前提下先付全款,如果对方同意,全盘棋就活了。”
“吭吭吭”里屋又响起咳嗽声,老曹又慌忙跑进去。
文俊说:“兴元,你去照顾老人,我们走了。改天约个时间再聊。”
老曹出来很难为情:“简直对不起,姑妈这几天感冒了。”又对郑戈说:“认识你很高兴。”
郑戈笑笑,说:“你去忙。”本 书由ωωω。ūмDтхт。сοм提供下载
走出大院两人站着聊了一会儿,文俊问:“印象如何?”
郑戈如实答:“柳庄相法说得有道理,饿纹入口缺衣少吃。”
文俊笑了,说:“看了几本歪书胡说八道。”
“你不信?”郑戈认真地说,“柳庄相法写得清清楚楚,天庭饱满地阁方圆者主贵,他是三角脸倒起长,上宽下尖,人聪明但晚年苦寒,鼻尖如刀者主短寿……”
“算了,算了!”文俊笑道:“你不要做生意了,去当算命先生!”两人又胡说一阵才分手。
胡振和泥鳅分了手不晓得该上哪儿去。回家太早赌友还没有下班,外面转又觉无聊。刚才泥鳅揭穿了自己,又打跑了汪可碑,心里很不踏实。如果汪可碑到郑戈面前揭发,自己还有脸回公司上班?上班好歹每月两百元稳当,中间再做点手脚还可以多捞几个钱,再说公司自己入了三千元股还未收回,更痛苦的是,《锦花》问题一解决,公司很快就会发财!胡振追悔莫及,不该和倪国秋、倪国春两弟兄往来。记得最初仅仅在一起欣赏色情像带,后来在倪家兄弟的引诱、吹捧、挑唆之下,暗暗滋生了对郑戈不满。《锦花》出了事,在泥鳅鼓动下,萌生了偷副纸型卖给倪国春一个外号叫野狗的朋友,对方开价五万。当时胡振吹牛吹昏了头,说纸型和手续都在自己掌握中。倪国春催了几次,他只有推,说不着急慢慢来。后来汪可碑告诉他公司垮定了,得想法捞一把,还说凌水已经吃了一万,胡振一时冲动,就把郑戈打了四副纸型的事给他讲了。汪可碑正愁得发昏,正想方打条找钱。一听,心中大喜,立刻想到卖纸型,说干脆全部拿出去卖了。胡振说只知道在军印厂加工,但没有去过,不晓得能不能拿出来。汪可碑说你有工作证,又有介绍信咋会取不出来?胡振又说没得手续,汪可碑说偷,胡振不敢,汪可碑说可以伪造嘛,两人商量到这个程度,胡振又不干了。他担心事情的后果,骗取、伪造都是犯法的事,而且最后倒霉的是自己。所以两人天天见面天天商量,却没有结果。在街上转了一阵,无情无绪只有回家去。胡振心烦意乱到了家,女人小蔡正在做饭。然而令他吃惊的是汪可碑居然一本正经坐在写字台旁看书!胡振服了,觉得汪可碑的确不简单,起先才被打得报头鼠蹿,居然又厚着脸皮跑到自己家里来了。
汪可碑亲热地握住他的手,笑嘻嘻说:“等你半天才回来。”胡振爱理不理地说:“啥事?”汪可碑惊奇地说:“哎哟,胡兄弟,我们的生意还没有落实,你就忘了?”胡振哭笑不得点了烟,不理他。可碑说:“兄弟,做事咋能凭意气?我们再把细节商量一下……”“我不做!”胡振毛了:“你走!”汪可碑冷笑:“嘿嘿,你真的不干?好,我马上去找郑戈,把你勾结倪家兄弟的事全部揭穿,你想会是啥后果?”胡振气得脸苍白气得心口痛,抓了一个酒瓶:“你虾子不要欺人太甚!”汪可碑笑嘻嘻地说:“打!我今天来就是让你打让你消消气,我是骂不还口打不还手。”把双手抄在怀里坐下来,说:“请打!”胡振手举在半空砸不下来,半天长叹一口气问:“你到底要做啥子?”可碑说:“要与你共同发财。”胡振有气无力地坐下来:“好,听你的。”汪可碑笑了笑,说:“这就对了嘛,今晚我去找人刻编辑部的公章,你明天到编辑部去搞本便笺,几份空白介绍信。明天下午带公司介绍信去取纸型。”胡振说:“要去就一起去。”汪可碑说:“行,就这样定了。兄弟,发财就在眼前,你不能再犹豫。”胡振说:“如果明天《锦花》的事搁平了呢?”汪可碑说:“你这人咋回事?现在,公司、编辑部都与我们无关,我们干我们的事。”胡振还想说,汪可碑说:“不说了,你明天到公司晃一下,下午在兰心茶园见。”说完转身就走。
冬日的黄昏特别短,一眨眼天就黑了。郑戈在病房里逗兰兰耍了一会儿,叫梦如带兰兰睡,自己就回家。车子放好就到干妈家去。干妈正在吃饭,看干儿来了,就去把刚做好的香肠腊肉煮了一点,边吃饭边和郑戈摆龙门阵。干妈越见衰老,不到60岁头发全白,牙齿都快落光了,只是眼睛还有神,动作还稳健。干妈问兰兰的病情又问郑戈的生意,郑戈给她讲了,她嫌没听清楚,还要郑戈说,听了两、三遍也听得津津有味。直到腊肉、香肠煮熟,才去切。郑戈说去买点酒,干妈说不买,最近她心口痛泡了茴香虫的酒,通气散瘀,还放了很多冰糖,很好喝。把菜摆好,酒斟满,母子俩就慢慢喝,酒确实好喝,一点不辣很顺口。干妈喝了三杯,郑戈不准她喝了,叫她喝点汤。干妈坐在旁边专心地看干儿吃。腊肉、香肠都是川味,味道极好,很香,干妈说再吹半个月的干风,味道才好。郑戈说就这样已经好吃了。干妈说我的手艺还不行,哪儿赶得上你干婆婆做的腊肉、香肠,郑戈已喝八、九杯酒了,有了几分酒意,想听干妈讲古,就问:“干婆婆会做腊肉,我咋没有听你讲过?”干妈说:“有很多事,你当知青时想讲给你听,怕你不懂,上了班呢,你又成天不落屋,今天干妈高兴,兰儿的病又好了,我给你讲。”
我是民国十六年八月初一生的,我娘家在叙府(宜宾)北溪百花场。那儿离叙府只有十几里。我父亲是自流井的人,专做盐生意。有一年他贩运盐巴到昭通被棒老二枪了,连衣服都被剥干净,一路讨饭到了北溪。我的外爷只有我妈一个独女舍不得嫁出去,看他年轻力壮人聪明,就招郎上门。我父亲很能干又吃得苦运气也好,不到几年家里就很富了。我母亲心灵手巧,针线活,地里的活都干得好,尤其会做香肉、腊肠,色、香、味都巴适,家里亲戚邻居和十几里外的人都要找我母亲帮忙,每年从冬至开始,一直要忙到腊月初十才做完。生了我后,她得了病就不能再生了。我父亲骂我是丧门星,母亲却心痛我。我小时最喜欢是冬天,我把腊肉偷一块出来和邻居家娃娃在沟里洗干净,切得飞薄,用湿竹笺穿起烤,湿竹笺烤干了肉也熟了。嗨,那个味才叫香。
到了五岁那年,邻居的男娃儿都去读书了,我要去父亲不准,我就哭就闹,他打我,我还是要去。后来他出外做生意去了,母亲才让我上了学。我很聪明,私塾里兴背书,先背“三字经”,老师带几遍我就会念,第二天就会背了。临帖我也喜欢,回家就练写毛笔字,手脸都是墨,字也写得规规矩矩。先生说可惜是个女子,不然北溪乡要出大学生。大一点又教唐诗,我更喜欢诗,念几遍就会背了,后来又教诗的平仄、押韵、格律、对仗,渐渐我也能写诗了。当时我才九岁,老师喜欢母亲更喜欢,连父亲也对我好了。可惜好景不长,我10岁那年母亲病逝了。一年后,父亲又娶了后娘,这个后娘能干、漂亮,但心很毒。当时我大哥十六岁,二哥十四岁,父亲一走后娘就要虐待我们三兄妹,大哥大了不怕,常和她吵。父亲回家,后娘就一把鼻涕一把泪说我们忤逆。父亲也晓得后娘不对,只得带两个哥哥到自流井当学徒,剩下我一个人就更惨了。过了一年后娘生了小弟,父亲说请个佣人,她说家里有现成丫头,何必白花钱。于是我就成了小丫头,烧火、煮饭、打扫,背弟弟、倒尿罐。稍不留意就要挨打。北溪是我娘的老家,亲戚朋友很多,父亲每次从外地回来,长辈们都要替我打抱不平,话传到后娘耳朵里,后娘怕引起公愤,又见我十二岁了,才请了个佣人,我又才好过一点。书不能念了,就在家学针线活,纳鞋底缝衣服。偶尔赶场去买几本书回来看,我才晓得外面世界那么大,对外面有了好奇心,想出去看看。唉,干妈讲到这里,长叹一口气,说,这是命,这是命!戈儿,要是干妈不看书不识字,就不至于上当。干妈牵起围腰擦去眼角的上的泪。
郑戈怕她伤心说:“干妈,旧社会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我这儿有一千元,你老人家拿去想吃啥就买。我还有事,改天在来听你讲古。”干妈不要,郑戈说:“我的钱你不要,你要哪个的?我是你干儿,我还要给你养老送终。”干妈嘴都笑得合不拢,说:“戈儿,我不要你给我养老,你给我送终就是了。”郑戈把钱塞给她,干妈还不要,郑戈发气了说:“你不认我这个干儿子?”干妈立刻投降,说:“好,好,我收下。”
郑戈从干妈家出来已是深夜,繁星满天,白头霜已把瓦染白了,明天有太阳。
早晨,郑戈到医院把兰兰接回家已是10点钟了。赶到公司就接到小天的电话,说杨明在家乱打乱闹,约郑戈一道去看望。郑戈很着急站在门口等,看胡振来了只是点点头,汽车一到,上车便走。路上问小天,他也不清楚,只说是杨明母亲打的电话告诉他,说杨明在家胡闹,都劝不了。车直接开进大院,两人慌慌张张地进了屋。
客厅里,扬伯伯满面愁容地听军医说话,见了他们只点点头,伯母眼睛都哭肿了,只是不见兰姑。两人悄悄坐下听医生讲。医生说杨明的病是突发的反应性精神病,治好后一般不会复发,又举了一些例子。扬伯伯问送不送医院,医生说如果这两天继续发病,就要送精神病院治疗。医生走后,扬伯伯摇摇头,出了口粗气,问郑戈和小天:“他和淑华的事,你们清不清楚?”小天说:“不清楚。”郑戈想说,但担心扬伯伯对淑华产生误解,含糊地说:“只晓得一点。”
伯母说:“你们是杨明的好朋友,也不瞒你们,昨晚深夜一点过,淑华同寝室的女孩儿,下中班回来,发现淑华在哭又在吃安定,跑去通知保卫处,厂里派车把她送到医院急救,幸好吃得不多发现及时,经抢救已脱离危险。厂里送淑华到医院的同时,给我们也通了话,那时已凌晨两点,接到电话后兰姑就去了医院。杨明听了后……”讲不下去了,捂着脸伤心地哭泣。扬伯伯说:“你哭啥子嘛?”等伯母止住哭扬伯伯接着讲:“杨明听了这个消息就呆了,站在院子里不说话也不动,足足有半个小时,我们以为他只是伤心而已,就劝他回去休息,他突然指着我说:‘你是王跃石?!’又上来打我,幸好警卫人员上来才把他拖回家,过了一阵又跳又闹,说要杀王跃石,又要找淑华,后来医生来给他打了针,才躺下睡了。哎,我们家一晚上就出了两件事……”
扬伯伯刚讲完,伯母又嚎啕大哭:“天哪!明儿成了疯子,以后咋个办?”扬伯伯压抑着内心的悲痛说:“哭能解决问题?要紧的是弄清原因,医生才能对症下药。首先要弄清这个王跃石是干啥的,军区保卫部门已经和厂保卫处取得联系正在追查,这个家伙一定与淑华的自杀有关,你不要急,查清了再说嘛。”伯母止了哭仍然抽泣着。郑戈已大致明白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只是有的细节还不清楚。为了安慰老人,郑戈说:“扬伯伯,扬伯母,你们不要伤心,既然淑华已脱离危险,就算解决了一个问题,杨明这个病并不是平常说的疯子,这种病来得快也去得快,最多一个星期就好了,而且恢复正常后一般不会复发。”两个老人都盯着他,问:“你咋晓得?”郑戈说:“我的干妈在上个月也是受了强烈的刺激发了病,在精神病院住了一个星期就恢复了正常,直到现在也没有复发。”这番话无疑是一针镇静剂,两个老人也不那么紧张了。郑戈说:“杨明在休息,就不去看他,我和小天去看看淑华。”
郑戈和小天走到门厅,郑戈叫出扬伯伯,悄悄地说:“你老去杨明卧室找一封信,这封信是淑华写给杨明的,可能在信中能看出些问题。”扬伯伯听后,疑惑地看着郑戈,郑戈只好说:“这封信是淑华要我转交给杨明的。”
郑戈和小天走进内科病室,兰姑满脸泪痕坐在病床前,有两个姑娘站在一边。兰姑见了郑戈和小天,裂嘴想招呼,郑戈摇摇头走到床前,淑华虚着眼突然睁开了,嘴唇移动,发出细微的声音:“郑大哥……”淑华脸色灰暗两颊瘦削极度虚弱,郑戈心里很难受,低下头小声地说:“淑华,好好养病。”淑华眼睛眨着,表示听明白了,嘴又在动:“杨明……没有……来?”咋个回答,不能把杨明的事告诉她,飞快地转了几个念头,才说:“他昨晚没有回家。”淑华嘴又动:“真的?”郑戈点点头,淑华两眼望着屋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