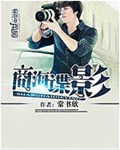商海情仇-第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吃一顿麻辣鸡块,说得我口水直流。”田敏咯咯直笑,郑戈说:“回来后,我和几个同学真的到馆子里吃了顿麻辣鸡块。”田敏嘟着嘴问:“你咋不喊我?”郑戈笑道:“你到哪儿去了都不晓得,咋个通知你?”田敏端起酒杯,说:“为麻辣鸡块干杯!”
田敏以前不喝酒,郑戈怕她醉:“慢慢喝。”
“嘿,你放心,现在的田敏不是十几年前的田敏,你不信?这瓶酒我们平分,”田敏柳眉上扬丹凤眼圆睁,“你以为我还是不懂事的小妹妹,摆出大哥哥的架子批我?”
郑戈笑笑说:“好,干了!”他隐隐感到田敏这十几年来过得不顺心。虽说串联时相处了两个月。和她单独谈话时间不多。只知道她父母都是北方人都是南下干部,家中只有她一个独女,父母都很钟爱她。
郑戈给她斟满酒,掏出烟问:“你抽不抽?”田敏见是“甲秀”,笑着说:“操得臭,吃‘甲秀’!”话刚出口怕郑戈怄气,“‘甲秀’烟燥,适合男人,我喜欢抽‘阿诗玛’”。摸出烟抽出一支叼在嘴上,郑戈把火递过去,田敏拉着他的手点了烟。
她的手白嫩丰腴,关节处一排圆圆的肉窝,手指很胖指尖却很细,指甲盖修得很短很圆,手掌很绵软。田敏刚吸了一口就呛得咳。郑戈忙舀了一勺汤,说:“抽不来就不要抽,来,喝口汤。”田敏喝了汤止住咳,笑着说:“心情好时抽一支,不好时也想抽。”郑戈拈了一夹菜放在她碗里,说:“多吃菜。烟就不抽了。”田敏说:“要抽,今天我很高兴,来,为你今天把我撞倒而干杯。郑戈说:“把你撞倒是你运气不好,咋能干杯?庆贺么?”田敏说:“这么多年没有见面,要是今天不撞车又咋能遇到你?你说该不该干?”郑戈只好和她干了第三杯。
田敏脸上泛起两团红晕,光洁的前额显得更白,更亮。她脱掉大衣搭在椅背上,洁白的颈项,圆滑的曲线令郑戈有些心猿意马。田敏感到有两道热辣辣的目光在身上游动,有点羞涩,掠了掠额前的头发问:“你咋不问问我的情况呢?”郑戈笑道:“男人应当尊重女人,女人愿意说的她一定会告诉你。”
“聪明,比以前还聪明多了,”田敏笑道,“可我了解你的情况。当年你下到柑梓,因打群架被关了一个月,后来你调到804厂上班,因病没有参加高考,再后来你就年慌慌张张结了婚……”
“你咋这么清楚我的事?”郑戈很惊奇。
“关心你嘛!”话出口田敏脸红了,“我听你的朋友讲的。”
郑戈问:“哪一个?”
田敏眨眨眼,故作神秘状答道:“那就不能告诉你了。”本 书由ωωω。ūмDтхт。сοм提供下载
郑戈不再追问,说:“你呢?这些年过得怎么样?”
田敏吸了口烟,目光有点呆滞。
一个活泼可爱,富于幻想的少女变成了一个要喝酒、要吸烟,有些颓丧的女人……
田敏把烟头扔在地上,苦笑道:“苦,活得累……死了两次都活过来了……”
郑戈心中一惊,“这女人死了两次!”心一热握住田敏的手,轻轻拍道,说:“过去的事,不想说就不要说了。”
田敏眼里闪着泪光,牙齿咬住嘴唇,胸脯急剧地起伏,眼泪淌了出来,慢慢靠在郑戈的肩上。郑戈有些慌乱,又不好推开她,只得僵直着身子坐在那里。
餐厅里客人渐渐多了。都在喝酒吃菜,笑谈豪饮,谁也没有注意角落里的郑戈和田敏。只有靠右边一桌坐着三人,贼眉贼眼地瞄着,瞄一下,又鬼鬼祟祟说几句,其中一中年汉子竟恶狠狠地盯着郑戈。郑戈在社会上混了多年,架打得不少,对几个二流子倒也不放在心上,冷峻的目光直射过去与那汉子对视了一阵,汉子掉过头与两个青年窃窃私语。
郑戈轻轻拍着田敏的肩,低声说:“不要伤心,有啥事以后讲,这儿是公众场合。”
田敏用手帕擦干泪水,不好意思地说:“对不起,本来高高兴兴的。来,我们喝。”说着又干了一杯,又去拿酒瓶,郑戈拉住她的手,说:“不能再喝了!”
田敏不听,用力夺过酒瓶倒酒,郑戈伸手一挡,酒杯落在地上,摔得粉碎。
田敏有些醉高声嚷:“我还要喝!”食客们都回头看,郑戈有点狼狈,随即又镇定下来,喊道:“结账!”
郑戈把大衣给她披上,扶着她向门口走去。“站住!”一声暴吼在身后响起,三个人大
步追来,郑戈回头问:“啥事?”
“你虾子胆子大,敢挖老子的墙脚!”汉子指着田敏说:“她是我的婆娘!!”
“嗡”地一声,郑戈脑壳大了,这下说不清了!真是运气霉喝水都塞牙齿。花钱办招待,摆了几句龙门阵就惹了一身骚。一转念,老子光明磊落怕个屁!说道:“朋友,你嘴巴放干净点,哪个挖你墙脚?”
汉子横眉竖眼地叫道:“抓个现行还敢嘴臭!”
田敏高声嚷:“胡说八道!哪个是你的婆娘?”
郑戈心一横“嘿嘿”冷笑,“婆娘都管不倒,你操锤子!”
汉子气昏了,骂道:“你狗日皮子发痒,给老子打!”
两个青年举起凳子冲上来,郑戈顺手抓起一张椅子,身子一侧两眼透出杀气,两个青年有些胆怯畏缩不前。
汉子哼一声,骂道:“白伙食,平时闹得凶,上阵就下软蛋!”“刷”地从腰间抽出一把藏刀。
田敏冲上来挡在郑戈前面高声叫:“倪国春,哪个是你的婆娘?!你太不要脸了!”
食客们围上来看热闹,餐厅负责人听说有人闹事,也急忙跑出来,严厉地问道:“你们干啥子?要打架到外面去!”
郑戈虎视眈眈地盯着汉子,那汉子提着刀恶狠狠地盯着郑戈。
田敏对群众高声说:“我叫田敏,在二轻局工作,我和这个人已经离婚三年多了,他还要纠缠,今天还提刀行凶!”
食客中不乏有正义感的人,一个六十多岁的大爷站在汉子面前指责道:“小伙子,婚都离了还纠缠不清,太不值味!”
一个中年男子劝道:“把刀收起来,一会儿警察来你就有麻烦。”
有人趁机起哄:“拉到派出所去,太不像话,吃顿饭都不清静!”
也有人惟恐天下不乱,胡乱嚷道:“打!打!打!看哪个是歪人,弄死一个少一个!”
餐厅负责人见人越围越多,怕影响生意,叫服务员打电话通知派出所。
汉子见众怒难犯,又怕警察来走不脱,也就收刀捡卦,怨毒地看着田敏和郑戈,咬牙切齿地说:“好!哪儿碰到哪儿发财!”边说边走,两青年也跟了出去。
郑戈很想追上去痛痛快快地打一架,但不清楚田敏与汉子之间到底是咋回事,气得脸发白手发抖,心里涌起杀人的念头。倒是田敏镇静,拉着郑戈的手从从容容走出餐厅。两人都不说话。郑戈心里闷得慌,但又不好说。田敏心里也很难受,让郑戈平白无故地受了冤枉气,还差点闹出人命,想说几句安慰话又说不出口。走了一截路,田敏小声说:“我回家了。”郑戈问道:“你住哪儿?我送你。”田敏说:“不送。”
“不行,我必须送你,万一那个二流子……”
“不怕,大不了一齐死!”
“胡说。”
“你走,”田敏关心地说:“你以后小心点,那个流氓一惯下黑手。”
郑戈冷笑一声,“你放心,这些烂龙我见得多,他不找我我倒想去找他,不给点教训他不晓得锅儿是铁打的。”
田敏忙劝:“不行,我的事与你无关,你千万不要介入。”
“由不得你!”郑戈瞪着眼,“你不要再说了,我送你走!”
田敏不再说话,两人蹬着车直奔金银街二轻局宿舍。一路上两人都沉默不语,夜风阵阵颇有寒意。到了宿舍,田敏说:“这是我父母家,我现在一个人住。”
郑戈说:“有事给我打电话!”
田敏猛然扑到他怀里轻声啜泣,郑戈有点紧张轻轻推开她,郑戈说:“别人看见影响不好。”田敏抬起头似笑非笑,说道:“假正经,你还记得在翻娄山关时我俩掉了队,晚上住在山上农民家,一床烂棉絮打伙盖,早晨醒来你把人家抱得紧紧的,手还放在人家怀里……”田敏羞红了脸又往郑戈怀里钻。郑戈木了,难道真有这回事?当年步行串联跋山涉水有时赶不到食宿站,就在老乡家住,几个人不脱衣服打伙盖一床被子是常事,但从没有和她一起睡过。时隔十几年,这么些年又坎坎坷坷风风雨雨,记忆很模糊了。田敏用手指戳了一下,嗔怪:“忘了?!
我就永远记得那个风雪加交的夜。”搂住郑戈不松手。郑戈被感动了,女人总是多情,男人总是健忘。
他怕自己失去理智,推开她:“我走了。”跳上自行车如飞而去。夜风送来田敏的声音:“我爱你!”
郑戈家住南门外鲁家巷。南大街还有些店铺在营业,一过南门大桥就很冷清了。今晚南门外停电,长长的街上黑黢黢的,只有尚未睡觉的住户的铺板缝隙透出煤油灯或蜡烛的光。北风刮过,刺人肌骨,郑戈有点冷。用力蹬着车,冒着严寒急急赶回家。
自从筹办公司半个多月没有回家了。打开门,屋里黑洞洞的。一股呛人的煤气扑鼻而来,郑戈连打几个喷嚏,掏出打火机摸索着点燃蜡烛,惨白的光照亮了这间破旧而狭窄的屋子。郑戈很疲倦却没有睡意。试了试保温瓶里水还烫,泡杯茶坐在椅上抽烟。里屋一阵唰唰的响,妻子梦如正给女儿兰兰提尿,兰兰哼了几声又睡了。妻子小声埋怨:“十几天不落屋,兰兰感冒了几天,今天才好点。妈说家里没得钱了,我爸来信说我妈得肝结石要开刀,叫我寄钱回去,还有……郑戈听得心烦,顶了一句:“念藏经!成天就说钱,钱,钱,钱,命相连!”
“嗨,你才怪咧,屋里老的老小的小,咋不用钱?你这个月一分钱没有拿回来,靠我三
十几元够用?”梦如火了,“你发啥子气?嫁给你五、六年没有买一件衣服,没有买一双皮鞋,我没有怪你;刮娃娃连鸡都没有吃一只,生兰兰也才吃了200个蛋两只鸡,我也没有怪你,今天一说家里没有钱你就发气。郑戈,你摸着良心想一下……”梦如声音有些哽咽。
郑戈平静下来细想确实不该发气,也就温地说:“梦如,不要怄气,我心里泼烦,等以后生意做起来就好了。妈那儿明天我给她二十元,你老汉儿那儿寄三十元去,家里给你十元暂时用着。”
说实话,女人也够可怜够辛苦,白天上班晚上带女儿睡,母亲病了还得去经佑。嫁给自己的确没有风光过一天,吃的粗茶淡饭,穿的是旧衣裳,常常为油盐柴米发愁。
余长林和胡振在公司里等到天黑,还不见郑戈回来,只有分头回家。长林是孝子,每天回家都要顺路去看望父母。父亲患肺气肿,一到冬天就不能下床,母亲患类风湿手脚极不灵便,每天和因患小儿麻痹残废了的妹妹在家粘火柴盒。母亲看长林回来,照例问,“吃饭没有?”长林没有吃,却顺口答道:“吃了。”妹妹抬起头笑嘻嘻地说:“哥,妈炖了羊肉。
”妈愁苦的脸上有点笑容,说:“你爸怕冷特地炖了点羊肉。”说着扶着桌子要起身,长林上前扶着妈的肩,笑道:“妈,我自己来,天气这么冷就不要粘了嘛。”
“唉”妈叹了口气,“反正没得事,一个月能粘两万个也有四十来元的收入。”妹妹说:“哥,你不晓得,这个活路还是李婆婆照顾我们,你以为谁都可以粘?”长林在沙罐里舀了半碗汤慢慢喝,妈慈爱地说:“这个家要全靠你,不把我儿累死了?你看,都瘦成这个样……”灯光下,妈脸色腊黄泪又涌了出来。
“嚎丧!”父亲暴吼一声,又说:“长林,你媳妇没得工作,也拿点火柴盒回去粘,好歹帮你一把。”长林喝完汤放下碗要走,妹妹说:“哥,过年给我买新衣裤,带我出去耍,你要记住呵!”妈举起手吓妹妹:“鬼女子,活路不想做,光想穿好的,洋盘!”长林摸着妹妹的头,说:“哥记得到。”
出了门,看看表才九点钟。心想,这么早回去也无聊,郑戈可能还未回家,就去找胡振。
胡振家住在南门外二巷子一个四合院里。住户大多是银行干部,胡振的父亲也是银行职员,胡振结婚后,父母就搬了出去,把房子让给了他。屋里灯火通明,胡振正和几个赌友“穿幺”。见长林来就高声叫老婆:“小蔡,泡茶!”自己依旧洗牌,边洗边问:“来不来?”长林摇摇头。
胡振叫道:“发牌了!压!压!压!最少五元,最多十元!”几个赌友掏出钱放在桌上。
小蔡对长林说:“喝茶。”拖过矮凳坐下说,“你看他,回家啥事不做就赌博,饭做好了端在面前都不吃,赌瘾大得很。”顺手拿来烟缸摆上一包烟,“你抽烟,你和胡振是老朋友了,劝劝他。”长林笑笑,小蔡看了看男人对长林小声说:“昨晚输了三十多元,弄得家里分钱没有,今天找我妈才要了三十元,他又赌,看来又要……”
胡振耳朵灵居然听到了,恶狠狠地骂道:“死婆娘,话多!”又问:“胖子,你几点?八点,二牛你几点?六点,小黑你几点?九点,呵哟,都是大点子,我完了……”胡振紧张地看自己的牌,嘴里念念有词:“一三六燃了,七点穿、穿三、三……”猛然大吼一声:“三!马
谷!通吃!”兴奋把牌往桌上一摔,把钱收了。又“刷刷”地洗牌,发牌,得意地盯了女人一眼,小蔡不敢开腔了走进里屋去。
长林拿本书,翻了几页提不起精神又放下。
“一二七,燃了,六穿……来个四,哎呀,一点!”
“二四五六七,呸!又无凑!”
“一三七五九,哎呀手气太臭了,无凑。”赌友们大呼小叫,赢钱的欢呼,输了的哀嚎,拍桌子打巴掌,闹得一塌胡涂。半个小时分出胜负,有两家洗白,胡振赢了八十元,脸上冒红光。二牛说:“我不输不赢打个太平。”黑牛苦着脸痛苦地呻吟:“日你妈,今晚有鬼!”胖子脸红筋涨地嚷道:“胡振,你娃不要得意,明晚上老子要来翻梢!”吵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