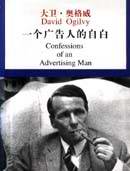��Ƥ��-��17����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á�
����������û���췢��һ����������顣�Ų�������ͳ�ֳ�����������ƿƳ�����ƽ��ѧ��ҵ��Ӣ�ĺܺã�����Ҳ���������μ���ͳ���ڲ����࣬�����桰�������ش����ĵ������鳤�������ռ��鱨ɱ����һЩ�ع���Ա����������ʼ����Ϊ�Լ���Ȼ��������ÿ������ҡͷ̾Ϣ��1949���ڹ����ְ������ӽ����ˣ�1950�괺�����������������ſ������Ǹ�Σ����������ְ�����ع����ֿ�������
��������1935�걱ƽ�ġ�һ�����š��˶���������Ҫץһ���������ĵع���Ա������ع���Ա���Ų��ŵ����ѣ��������ڻ�������������������Ժ���λ�ع���Ա�ڲ����ʡ��������ίԱ�������ίԱ��֪���Ų����ڳ��������������������������һ���ţ�֤����һ�����š��˶��Ų����й��������Ų��Ż���һ����ԪǮ������һ�������ָ�����������ͽ��10�ꡣ����������С��������ͨ���������������ݶ����롣��Ҳ�벻�������������⡣���˶�������������飬��һ�����������ˡ�
�������˶�������˵����������ָ�ס���ֺ�����ˣ����Ѽ��ӣ���һ�¡���
�������Ҫ�����⣬���������큸����һ�Ѽ����ļ�����������ӱȽϴ��������д�Ҵ���ʹ�á��ֵ�����С�飬������˳��ã�Ȼ���Ų��Ž��˹�ȥ�������ż������Ը����Ҵ�����һ���Ѫ��������������ʱ���ڿ����������˼����Ҳŷ��֣�����ȥ�����ļ������������������ô������������⣬���������䡣��ʱ��Ҷ������ˣ�һ������Ҫ��ɱ���Ͻ������������������������г�ȥ��û���������������ȥ��ҽԺ����ҽԺ�������Ų���ͷ������ѩ�Ĵ���������Ǵ�Ұ��������ˡ��ر����ң����Ƴ������ҵ��鳤�������ҡ����Բ�Ҫ���¡����������Ƴ����ң���λش�
���������������Ų��ţ�������������������ʲô�ô��������������Լ���ʹ�࣬�Դ��Ҳ���á���
�����������������Ҵ����ӣ������������֡����Ų���վ����˵��
�����������Ӿ��ܽ�����˼�����⣿��Ĵ������ӣ���֪������ô���ˡ�ʲôҲ���ô������侲����һ�룬��ͨ����̸����
���������������ҵ�����С���ӣ���ʼ���ʣ���ǰ�����ϣ��Ų��ų���ʱ��������������𣿡�
��������û����Ц�ˡ�
�������㵱��С�鳤�����д��˵�Ȩ�������ٴ��ˣ���Ҫ����������²���������飬ƫƫ��������С�顣�㻹Ц�أ���
����������������û�취���Ժ��ٱ������ˡ���
���������Ǽ��ӵ���������˼�����⡣����ôѧϰ�ˡ���
�����Һ��������������ֻ��20���꣬ɽ��С���ӣ�һ���Ļ����ߵĸɲ���������������ܿ죬�Դ��Ų�������£�����Ϊһ���������ͻ��������������û�������죬���Ǻͷ�ϸ��Ľ����˼��䡣ʹ��Ҷ���������Ӿ�����������˵�������Ĵ����ȴ������������á����������������ĸɲ����Dz������������硣��һ����ʹ����16���ˣ���һ���е����������ǵ���ů�����
�����ո�ƽ������Ϣ��������Һܸ��ˡ����ڼ�ŶԴ��˵����������ףƽ����ţ���������Լ���Ǯ���⣬����ɲ�����
�������ͬ�����ɡ�����������������ʾ�����õ�����������ͬ�⡣����16���ˣ�����12���⡣�Һ��д�������Ǯ�Ƚ϶ࡣ��������������һ���⡣���������˶࣬�е���û�����
�������˼��죬����ѶԱ�Ѹ߽�ͺ���������ˡ��ֹ��˼��죬����������Ԣ����8����Ҳ�ӻ��˳��������ֻʣ���д��������к���˳ɡ���ع衡����IJ�����6���ˡ�
������������ˣ�սʿ��Ҫ���������ᣬ���Ҹ����Ŀ���Ҹ����DZ���һ�ο�壬����С����ÿ�������ҵ����ǵ�����ȥ�����ǣ���������ǽ�Ϲ����������Ӳ������ҡ���ʱ������Ե�Ҳ���ҳԡ�������Ҳ���ݡ����˵Ц��Ҳ���رܡ��Ҹе��������Һ����ţ�˼���Ϸdz����ɡ�
�����Ҷ��д���˵���������꣬������������һ������������������ձ��ϻ����úá���
������Ҷ�ͬ�⣬���д��������IJ����ҳ�Ǯ��������⣬�����˰��ƣ����ﻨ���ס������������������ʾ�ģ����Ҳ��Ⱦƣ�����Ҫ��һ�㣬����������ɣ��ұ�֤������£��Ų��������������еġ������ˣ����Ʋ��ࡣ�����������DZ����˰��ơ�
����12��31�����磬�ҵ���������⣬���IJ��ջ𡣳��������ˣ�һ�������⣬�ԵĴ���������������ǹ��úܺá��º��Ҳ�֪��������û�й��ã�һ��սʿ����˵�������dzԵúã���ɲ�֪���������˶��������㵽����ȥ���⣬�������Ų˵�������Ŀ�������������������������˼�˵������ô�ܵ������õ�������˵��Щ���˶��DZȽϽ����ġ��˼���˵��������ô����Ҳ�Ƿ��ˡ���ôһ˵�����������ˡ������������Ƕ��Ŀ�������ֻ�����š����Ǵ��Ҳ�е���ʹ�졣�������ġ���
�����Ҹе����ѹ������öԲ�����������һ������Ҫ�����Ⱦƣ�̫�����ˡ��һص���һ˵����Ҷ��е��������Լ�����Ҿ��������������飬��������һ�ɲ���
��������������Ƕ��ص��˳��������֡�
����һ�죬���Ƴ�����̸��һ������ֵ����������¡������ң����д�����д������ҳ�IJ��ϣ���˭��д�ģ���
����������������д�ġ��ҵ���˼�ǣ������˹����־ͳ�С�ʲô���Ҳû�н�����Ӧ���Զ���дһЩ���ϣ���ȡ��������
�������ѵ�����û��ͼ��Ŀ¼����д��һЩͼ��Ŀ¼���������Ȿ�飬�����DZ��飬������ᣬ������ᡪ����Ū�Լ���ѧ���أ�һ������Ҳû̸���������˸������ᷴʡ����Ҳ����ʶ�Լ��������Dz�ú�Զ���Ժ��ٲ�Ҫ�������ˣ������Լ���������ʶ�ɡ���
��������ͨʱ���Ҷ��д���˵����������Ա����һ��ܿ������Ӳ�̸����Ҳ�����㣬������Ҳ����������������ȥ���á�Ӧд���ϣ�����̸�����������⣬̹�����������������ȡ�Dz��еġ�ÿ��ֻ��һЩ�飬дЩ�ռǣ����������ġ�Ӧ����������
���������д��������ҵĻ�д��һƪ����ҳ�IJ��ϣ���Ϊ����ʮ���䡱����Ҫ�ǽ�ź�������һЩ������������ᣬժ��������ë��ϯ�Ļ��������������������д����ҿ���һ�£��Ҹе�������ʶ̫�����Ϊ�ǣ����DZϾ���д�����ˣ���˵���ԣ����ͳʸ�������������ܵ��˹��Ƴ����������д���һֱ��֪������£�����Ϊ�Լ���ݲ���д�úܺ��أ���ʵ���ܺã����ߺܲ��á�
�������Ź��Ƴ��ֲ����ҵ�Բ¥¥�ϵ��ĺżȥ��������
������һ��ο��Ģ����ˣ�������һ���ڲ������ۣ���һ����ͭɫ�ľ�ձñ�����ϴ�һ�����ӡ������ڳ���������һ�棬����1948�����죬�ڳ������촦�����Ź�����С����������˵�ͷ��û��̸ʲô�������ˡ�����һ��Ļ������û�����������������������ˣ����ԣ�������һ�����Ҳû�У�����ʶ���á�
�����ο��ĵ���������ͨ���س�����ͳ����Χ��һ���Ƿ��Ը��꣬���κεط����ó���ͷ�������̸�������ղ�˵ţ��һ��û�������Ļ��ƹ���
����������֮����������Ǹ����Ҹ������Լ��������������Ҹ�ʲô�ģ���˵С�������ʣ������IJ��֣���
������˵�ڶ��촦�������¾仰һ���ǣ������Ǵ����Ź�������ʶ������Ȼ����������˵�ġ���Ц��Ц������˵��������˾���ı������Ҳ��ʶ����
����������Ŀ����Щ���������������ѣ����ij��١��������ڷ�������Ҳ���е�λ������֪������ʲô�ˣ�Ҳ��֪�����촦�����붽�쳤��ʲô��ϵ������֮���������������ܿ���Ϊʲô���Ҵ�ʮ�żǨ���ĺż�أ���һ����֪������DZ������ģ����������·�������װ���ô���ù�������Ա���۾���
�������±��飬�����ĺŵ��鳤������������������ˣ��������л�����ɡ�������Ȼ�dz�����Ӱ��Ƭ����ְԱ���ڿ��Ϳƹ������������ֱ���������ʱ��Ҳ�����з�����������ɡ�
������ͷһ�λᣬ��˵�������������ҽ���һ��������ְҵ���óƺ����Ա�ѧϰ����
����ÿ���˶����ҽ����ˣ��ο���û��˵���Ǿ�ͳ����ֻ˵�������Ǽ�����ͨ���س�����1947��ֻ����һ���£��Ժ���˵����������С���
������ô������ʵ����û��֨����
��������Ȼ˵�������ڳ�Ӱ���Ϳƣ��Ƿ������Ƭ�ӣ��Կ��͵ġ���ÿ���糿������ϰ��ש���м���������һ��������˵���dz���һ��שͷ��ɣ��ҵ���ί�������������ˣ���ʵ�����ǿ���Ц�ġ���
�������Ͽ��ᣬ�ο��ĺ���Ϲ����ʲô��Ҳû�У����һ�˵��������ʶ��ѧ˼�����˽���ɱ��ѧ˼����û�иɡ�������Сѧͬѧ������ô��ɱ���أ���
�������˶Զο��ĵ���֪���ò��������˵������������ȫ�����ϣ�������ο���Ҳ�����⡣��˵��һ�����Ҷ���ƭ���ˣ��㻹����ƭ��������
����������˵���е��ܾ��ȣ���Ц��һЦ��
�����ο��ij�ȥд��������ϣ�����ֱҡͷ���ƺ���ʲô�����¡���С��һ���ӹ�ƣ�����һ�����������������Ҳ�������
����һ�����磬����ѶԱ���ң����ο��������Ǹ�С���𣿡�
�������ǵģ����ֲ��ã�����ࡣ��
���������ⲻ�١����Dz��Ǿ�ͳ����
�������Ǿ�ͳ�����ǻ��ɡ�����ô�����ģ���
��������˵��1946����������������ʡ��ϯ��������ζ���ͳһ����ίԱ�����Ӷӳ����Ժ�͵�����ʡ�����飬�ֵ���ͨ���س���һֱ��������š���
�����������Ǻ�˵����ƭ������1946����������ͳһ����ίԱ������Ӷӳ����Ǿ�ͳ��������ͷ����ǿ����ȥ�ġ�û�������ϵ����촦������ӹ�Dz����ܵġ�����������֪����ʵ����˵�������ȥ�ģ������벻����ǿ����������ϵ���ڿ���ʱ�ڵĻ����������Ҳ���塣����С�����˵�������λ���˾��ʲôҲû�иɣ���Ҳ�����˲������ŵġ��ҿ���һ���ǽ������⣬�����������Ŀ��ӡ����Ҹ�������ѶԱ�������ڶ���������ϵ�����������ҵ�˭������һ��ʹ�������ٳ�����ԭ�Ρ�
�����ڶ����緹�������˶ο��ģ���������������������������͡�һ��¥�����ݵķ��˶��������������Դ������в���֮����
�����ҶԹ��Ƴ�˵�����ο��IJ����Ͼ�ͳ�������û�һ���������ܳ��ϡ���
�������Ƴ�˵��ͷ���Լ����������Ƴ��������Ѷο����ᵽ���������ο�����������վ�������룬���ڿ����������������ϡ�
�������Ƴ��ʣ����ο����������̹����ô���ˣ���
�������ҵ����ⶼ̹���ˡ���
�������Ҹ����㣬�������ﲶ��ľ�ͳ�����е��ǣ��ü��١����Ƶ��ٽ����Ÿ������İף��м�������࣬����ʲô����Ҳ��������ǿ�����ӣ���ʲô�˲����㻹��Ƥ�������治֪Ȥ����
���������Ǿ�ͳ�ٽ������ο���żȻ��˵������ôһ�仰��
���������Ǿ�ͳ�ٽ����ã���̹�ͺá�ֻҪ����̹�ף��������⣬���ǻ�ӭ����������д�ݲ��ϣ�ʲô�ط�����ʲôʱ�����ٽ�����һЩʲô�����
������1945��4�½���ʡ��ϯ���������������ҵ����ҹ��ݣ�����һ���ң�����һ���ٽ�רԱ����
�������Ǻ��������Ҵ�û����ô������һ���ٽ���ֻ�в���Ϥ���ҵ��˲���������ƭ����������Ȼ˵���ٽ����ͽ������ٽ�����ɡ�
���������Ƴ����ң������Dz����ٽ�����
������˵�����������ٽ�����û�г��������ٽ���Ҫ�������´���ǩ�˴��Ҳ�������һ������ɸ��ٽ����Dz����ܵġ���
�������ں��ڷ�����Ҽ�ٽҷ���ÿ���˶������һЩ���������ӻ����ص��������ο���˵��ҲҪ�������������ڳ�����ŵ�ʱ��һ֧����ǹ������Ժ�е�ú����Ҽ��ڳ��������֡����š���
�����Ұ���������ӳ����������������˵�����ο������ǵ��ң�����ȡ�֣���Ҫ��������
������һ�죬�Ҳ����ݡ���ҶԶο����������˵������˯��������������ʿ�����ο���һ������⡣�ο������ִ������ӣ������֡��һ���֮����˵���£���������ʿ��������ʿ��д�����顣��ʿ���Զο���˵��������Ը����Ǵ��㲻�ɣ�����֣��Ҿ�Ҫ���㣬�س���ʡ��Ҳ���У���
�����Ҷ���ʿ��˵�������У����˲��ԣ����ǿ���������
����ͬ�ݵķ��˶Զο��Ķ�ʮ�ַߺޣ��������ƶȡ���˵��������������������̨�ף��Ǵ��ˣ���֪�������Ǽٽ�����ʵ���������ﻹͬ�����ء���һ���һ�������������
�����ҶԴ��˵���������Լ���ʡ�ɣ���Ҫ�������а����ˡ���
������������Ȼ�İ��ӣ���Ҳ��ν����˽⡣�����ǰ�����ڹ��������β�������������У����ָ��Ա���μӹ����������ţ���ź��ڱ����μ��˹������ֵַ�������Ӱ��Ƭ�������������שͷ�ᡱ������Ψ�����Ǵ�������ڼ顣�Һ�ע����������ϵ������ȥ���ϼ������е������岿�ӣ��е��ڱ���ѧϰ���������Ѷ��ڱ���������û������ϵ����������ӹ�����ѶԱ����������ѶԱ�����о���һ�Σ��Ҵ�����Ȼ���ŵ����š������ռ����Ҳ������з����������ݡ���˵��������ʷ�������⣬�������лû�С������ֽ��飬��������������������������������¶���������Ӧ�õ������˽�����һ���������������л��ָ���������ڱ����������鱨�������ŵ�����������ȥ�š��������������Ҫ�������ǵ��ż㣬����ʲô������д�ģ������룿����ʲô��ѧ�ֶΣ���
��������ѶԱ��ͷ����Ϊ��˵���е�����
�����Ұ��켸������С�飬�ҵ�С��¥�����IJ�������С��IJ��ϡ���һ�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