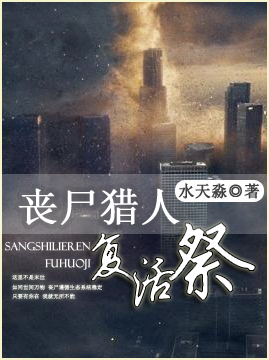复活-第2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为您效劳,不是指幕后活动,是指写状子。”
“谢谢您,那么您的酬劳……”
“我的助手会给您一份誊清的状子,他会告诉您的。”
“我还有一件事要向您请教。检察官给了我一张到监狱探望这人的许可证,可是监狱官员对我说,要在规定日期和地点以外探监,还得经省长批准。真的需要这个手续吗?”
“我想是的。不过现在省长不在,由副省长管事。可他是个十足的笨蛋,您找他是什么事也办不成的。”
“您是说马斯连尼科夫吗?”
“是的。”
“我认识他,”聂赫留朵夫说着站起来,准备告辞。
这当儿,一个又黄又瘦、生着狮子鼻、奇丑无比的矮小女人快步闯进房间里来。她就是律师的妻子。她对自己的丑陋显然毫不在意,不仅打扮得与众不同,十分古怪——身上的衣服又是丝绒又是绸缎,颜色鹅黄加上碧绿,——而且她那头稀疏的头发也卷过了。她得意扬扬地闯进接待室。和她同来的是一个高个子男人,脸色如土,满面笑容,身穿缎子翻领的礼服,系一条白领带。这是个作家,聂赫留朵夫认得他。
“阿纳托里,”她推开门说,“你来。你看,谢苗·伊凡内奇答应给我们朗诵他的诗,你可得念念迦尔洵①的作品。”
聂赫留朵夫刚要走,可是律师的妻子同丈夫咬了个耳朵,立刻转过身来对他说话。
①迦尔洵(1855—1888)——俄国作家。
“对不起,公爵,我认得您,我想不用介绍了。我们有个文学晨会,请您光临指教。那会挺有意思。阿纳托里朗诵得好极了。”
“您瞧,我有多少杂差呀”阿纳托里说。他摊开两手,笑嘻嘻地指指妻子,表示无法抗拒这样一位尤物的命令。
聂赫留朵夫脸色忧郁而严肃,彬彬有礼地向律师太太感谢她的盛情邀请,但因无暇不能参加,接着就走进接待室。
“好一个装腔作势的家伙”他走后,律师太太这样说他。
在接待室里,律师助手交给聂赫留朵夫一份抄好的状子。谈到报酬问题,他说阿纳托里·彼得罗维奇定了一千卢布,并且解释说他本来不接受这类案件,这次是看在聂赫留朵夫面上才办的。
“这个状子该怎样签署,由谁出面?”聂赫留朵夫问。
“可以由被告自己出面,但要是有困难,那么阿纳托里·彼得罗维奇也可以接受她的委托,由他出面。”
“不,我去一趟,叫她自己签个名,”聂赫留朵夫说,因为能有机会在预定日期之前见到玛丝洛娃而感到高兴。
四十六
监狱看守到了规定时间在走廊里吹响哨子。铁锁和铁门哐啷啷地响着,走廊门和牢房门纷纷打开,光脚板和棉鞋后跟发出啪哒啪哒和咯噔咯噔的响声。倒便桶的男犯在走廊里来回忙碌,弄得空气里充满恶臭。男犯女犯都在洗脸,穿衣,然后到走廊里点名,点完名就去打开水冲茶。
今天喝茶的时候,各个牢房里群情愤激,纷纷谈论着一件事,就是有两个男犯今天将受笞刑。这两个男犯中有一个是年轻的店员瓦西里耶夫。他很有文化,由于醋劲发作而杀死了自己的情妇。同监犯人都很喜欢他,因为他乐观、慷慨,对长官态度强硬。他懂得法律,要求依法办事。长官因此不喜欢他。三星期前,有个看守殴打倒便桶的男犯,因为那个男犯把粪汁溅到他的新制服上。瓦西里耶夫为那个犯人抱不平,说没有一条法律允许殴打犯人。“我要让你瞧瞧什么叫法律”看守说,把瓦西里耶夫臭骂了一顿。瓦西里耶夫就回敬他。看守想动手打他,瓦西里耶夫就抓住他的手,紧紧捏了三分钟光景,然后拧着他的手叫他转过身,一下子把他推到门外。看守告到上边,典狱长下令把瓦匹里耶夫关进单身牢房。
单身牢房是一排黑暗的仓房,外面上了锁。这种牢房又黑又冷,没有床,没有桌椅,关在里面的人只能在肮脏的泥地上坐着或者躺着,听任老鼠在身边或者身上跑来跑去,而那里的老鼠又特别多特别大胆,因此在黑暗中连一块面包都无法保存。老鼠常常从囚犯手里抢面包吃,要是囚犯一动不动,它们就会咬他们的身体。瓦西里耶夫不肯蹲单身牢房,因为他没有罪。几个看守硬把他拉去。他拚命挣扎,另外两个男犯帮他从看守手里挣脱身子。看守们都跑拢来,其中有个叫彼得罗夫的,以力气大出名。犯人们敌不过,一个个被推进单身牢房。省长立刻得到报告,说发生了一件类似暴动的事。监狱里接到一纸公文,命令对两个主犯,瓦西里耶夫和流浪汉聂波姆尼亚西,各用树条抽打三十下。
这项刑罚将在女监探望室里执行。
这事昨天傍晚全体囚犯就都听说了,因此各个牢房里的犯人便都纷纷谈论着即将执行的刑罚。
柯拉勃列娃、俏娘们、费多霞和玛丝洛娃坐在她们那个角落里,已经喝过伏特加,个个脸色通红,精神振奋。现在玛丝洛娃手头经常有酒,她总是大方地请伙伴们一起喝。此刻她们正在喝茶,也在谈论这事。
“难道是他闹事还是怎么的?”柯拉勃列娃说到瓦西里耶夫,同时用她坚固的牙齿一小块一小块地咬着糖。“他只是替同伴打抱不平罢了。如今谁也不兴打人哪。”
“听说这人挺好,”费多霞插嘴说,她抱着两条长辫子,没有扎头巾,坐在板铺对面一块劈柴上。板铺上放着一把茶壶。
“我说,这件事得告诉他,玛丝洛娃大姐,”道口工说,这里的他是指聂赫留朵夫。
“我会对他说的。他为了我什么事都肯做,”玛丝洛娃笑吟吟地把头一晃,回答说。
“可就是不知道他几时来。据说马上要去收拾他们了,”费多霞说。“可不得了”她叹了一口气,又说。
“我有一次看见乡公所里揍一个庄稼汉。那天我公公打发我去找乡长,我一到那里,抬头一看,他呀……”道口工就讲出一个很长的故事来。
道口工故事讲到一半,就被楼上走廊里的说话声和脚步声打断了。
女人们安静下来,留心听着。
“他们来抓人了,那些魔鬼,”俏娘们说。“这下子会把他活活打死的。那些看守可把他恨透了,因为他总是不肯向他们低头。”
楼上的响声又沉寂了。道口工继续讲她的故事,讲到他们在乡公所仓房里怎样毒打那个庄稼汉,吓得她魂不附体。俏娘们却说,谢格洛夫挨过鞭子,可是他一声不吭。随后费多霞把茶具收掉,柯拉勃列娃和道口工动手做针线活,玛丝洛娃则抱住双膝,坐在板铺上,感到十分无聊。她刚想躺下睡觉,女看守就跑过来叫她,说有人探望,要她到办公室去。
“你一定要把我们的事告诉他,”玛丝洛娃正对着水银一半剥落的镜子整理头巾,明肖娃老婆子对她说,“不是我们放了火,是那个坏蛋自己放的。有个工人也看见了,他不会昧着良心乱说的。你对他说,让他把米特里叫来。米特里会原原本本把这事讲给他听的。要不然也太不象话了,我们平白无故被关在牢里,可那个坏蛋却霸占人家的老婆,在酒店里吃喝玩乐。”
“真是无法无天”柯拉勃列娃肯定地说。
“我去说,我一定去对他说,”玛丝洛娃回答。“要不,再喝一点壮壮胆也好,”她挤挤眼,补充说。
柯拉勃列娃给她倒了半杯酒。玛丝洛娃一饮而尽,擦擦嘴,兴高采烈地又说了一遍“壮壮胆也好”,然后摇摇头,笑嘻嘻地跟着女看守沿长廊走去。
四十七
聂赫留朵夫在监狱的门廊里已等了好久。
他来到监狱,在大门口打了打铃,然后把检察官的许可证交给值班的看守。
“您要找谁?”
“探望女犯玛丝洛娃。”
“现在不行。典狱长正忙着呢。”
“他在办公室里吗?”聂赫留朵夫问。
“不,他在这里,在探望室里,”看守回答,聂赫留朵夫觉得他的神色有点慌张。
“难道今天是探监的日子吗?”
“不,今天有一件特殊的事,”他说。
“怎么才能见到他呢?”
“回头他出来,您自己对他说吧。您先等一会儿。”
这时,司务长从边门出来。他穿一身丝绦亮闪闪的制服,容光焕发,小胡子上满是烟草味,厉声对看守说:“怎么把人带到这儿来?……带到办公室去……”
“他们对我说,典狱长在这儿,”聂赫留朵夫说,看到司务长也有点紧张,不禁感到纳闷。
这时候,里边一扇门开了,彼得罗夫神情激动,满头大汗,走了出来。
“这下子他会记住了,”他转身对司务长说。
司务长向他使了个眼色,意思是说聂赫留朵夫在这儿,彼得罗夫就不再作声,皱起眉头,从后门走掉了。
“谁会记住?为什么他们都这样慌慌张张?为什么司务长对他使了个眼色?”聂赫留朵夫心里琢磨着。
“不能在这儿等,您请到办公室去吧,”司务长又对聂赫留朵夫说。聂赫留朵夫刚要出去,典狱长正好从后门进来,神色比他的部下更加慌张。他不住叹气,一看见聂赫留朵夫,就转身对看守说:“费陀托夫,把五号女牢的玛丝洛娃带到办公室去。”
“您请到这里来,”他对聂赫留朵夫说。他们沿着陡峭的楼梯走到一个小房间里,里面只有一扇窗,放着一张写字台和几把椅子。典狱长坐下来。
“这差使真苦,真苦,”他对聂赫留朵夫说,掏出一支很粗的香烟来。
“您看样子累了,”聂赫留朵夫说。
“这差使我干腻了,实在太痛苦了。我想减轻些他们的苦难,结果反而更糟。我真想早点离开,这差使真苦,真苦哇。”
聂赫留朵夫不知道什么事使典狱长感到特别苦,但他看出典狱长今天情绪非常沮丧,惹人怜悯。
“是的,我看您是很苦的,”他说。“可您何必担任这种差使呢?”
“我没有财产,可是得养家活口。”
“您既然觉得苦……”
“嗯,老实跟您说,我还是尽我的力做些好事,来减轻他们的痛苦。要是换了别人,决不会这么办的。您看,这儿有两千多人,都是些什么样的人,真是谈何容易得懂得怎么对付他们。他们也是人,也惹人可怜。可又不能放纵他们。”
典狱长讲起不久前发生过的一件事。几个男犯打架,结果弄出人命来了。
这当儿,看守领着玛丝洛娃进来,把他的话打断了。
玛丝洛娃走到门口,还没有看见典狱长,聂赫留朵夫却看见她了。她脸色红红的,精神抖擞地跟着看守走来,摇头晃脑,不住地微笑着。她一看见典狱长,脸上现出惊惶的神色盯住他,但立刻镇定下来,大胆而快乐地向聂赫留朵夫打招呼。
“您好”她拖长声音说,脸上挂着微笑,使劲握了握他的手,这跟上次大不一样。
“喏,我给您带来了状子,您来签个字,”聂赫留朵夫说,对她今天见到他时表现出来的那副活泼样子,感到有点奇怪。
“律师写了个状子,您签个字,我们就把它送到彼得堡去。”
“行,签个字也行。干什么都行,”她眯缝着一只眼睛,笑嘻嘻地说。
聂赫留朵夫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折拢的纸,走到桌子旁边。
“可以在这里签字吗?”聂赫留朵夫问典狱长。
“你到这儿来,坐下,”典狱长说,“给你笔。你识字吗?”
“以前识过,”她说,微笑着理理裙子和上衣袖子,坐到桌子旁边,用她有力的小手笨拙地握住笔,笑起来,又瞟了聂赫留朵夫一眼。
他指点她该怎么签,签在什么地方。
她拿起笔,用心在墨水缸里蘸了蘸,抖掉一滴墨水,写上自己的名字。
“没有别的事了?”她问,忽而望望聂赫留朵夫,忽而望望典狱长,随后把笔插在墨水缸里,接着又放在纸上。
“我有些话要跟您说,”聂赫留朵夫接过她手里的笔,说。
“好,您说吧,”她说,忽然象是想起了什么心事或者想睡觉,脸色变得严肃了。
典狱长站起来,走了出去,屋子里剩下聂赫留朵夫和玛丝洛娃两个人。
四十八
带玛丝洛娃来的看守在离桌子稍远的窗台上坐下。对聂赫留朵夫来说,决定命运的时刻到了。他不断责备自己,上次见面没有说出主要的话,就是他打算跟她结婚。现在他下定决心要把这话说出来。玛丝洛娃坐在桌子一边,聂赫留朵夫坐在她对面。屋子里光线很亮,聂赫留朵夫第一次在近距离看清她的脸:眼睛边上有鱼尾纹,嘴唇周围也有皱纹,眼皮浮肿。他见了越发怜悯她了。
他把臂肘搁在桌上,身子凑近她。这样说话就不会让那个坐在窗台上、络腮胡子花白、脸型象犹太人的看守听见,而只让她一个人听见。他说:“要是这个状子不管用,那就去告御状。凡是办得到的事,我们都要去办。”
“唉,要是当初有个好律师就好了……”她打断他的话说。
“我那个辩护人是个十足的笨蛋。他老是对我说肉麻话,”她说着笑了。“要是当初人家知道我跟您认识,情况就会大不相同了。可现在呢?他们总是把人家都看成小偷。”
“她今天好怪,”聂赫留朵夫想,刚要说出他的心事,却又被她抢在前头了。
“我还有一件事要跟您说。我们那儿有个老婆子,人品挺好。说实在的,大家都弄不懂是怎么搞的,这样一个顶刮刮的老婆子,竟然也叫她坐牢,不但她坐牢,连她儿子也一起坐牢。大家都知道他们没犯罪,可是有人控告他们放火,他们就坐了牢。她呀,说实在的,知道我跟您认识,”玛丝洛娃一面说,一面转动脑袋,不时瞟聂赫留朵夫一眼,“她就说:”你跟他说一声,让他把我儿子叫出来,我儿子会原原本本讲给他听的。‘那老婆子叫明肖娃。怎么样,您能办一办吗?说实在的,她真是个顶刮刮的老婆子,分明是受了冤枉。好人儿,您就给她帮个忙吧,“玛丝洛娃说,对他瞧瞧,又垂下眼睛笑笑。
“好的,我来办,我先去了解一下,”聂赫留朵夫说,对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