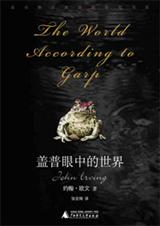盖普眼中的世界-第2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反应:他们可能还以为是在防范事态“失控”,虽然这种防范很少成功过。
怒气冲冲,又喝多了啤酒、胆大气壮的酒鬼们,好容易爬上了象背,准备离开停车场——当然是嘻嘻哈哈,闹成一团——但不小心便撞上了其他的大象及东西。因为这群醉鬼的象酒精效应发作,步履笨重、醉眼蒙眬、东倒西歪、自以为是了。它的长鼻子左摇右晃,像一截没安装好的义肢。它的步伐是那么不稳定,最后它撞上了电线杆,将它拦腰撞成两截,高压电线缠在它的大脑壳上——它当下毙命,骑在它背上的婚礼来宾也死了。
波尔太太,请相信我:我不认为这件事“好笑”。但路上来了个挨饿的印度人。他看见所有婚礼来宾都在哀悼他们的朋友,以及朋友的大象:很多人哭号,撕破身上华丽的衣服,打翻了精美的食物与饮料。他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混进婚礼,趁客人不留心,偷一些上好的食物与饮料,带给他挨饿的家人。第二件事则是开始大笑,笑那些客人以这种方式把自己和大象送进鬼门关,笑到肚子痛。跟饥饿而死比起来,这种集体死亡的方式想必显得很好笑,起码也很快速。但婚礼来宾不会这么想。他们已经认为这是场悲剧,他们已经在谈论“这次悲剧事件”,尽管他们或许会容忍“肮脏的乞丐”出现在会场——甚至容许他偷他们的食物——但他们绝不能容忍他嘲笑他们死去的朋友和他们的大象。
8第二个孩子、第二本小说、第二次恋爱(10)
婚礼来宾因乞丐的行为而勃然大怒(因为他的笑声,而非他偷窃或一身破烂),把他淹死在一个已故的醉客拿来喂大象的啤酒桶里,他们认为这样就叫伸张正义。我们看这是一则阶级斗争的故事——当然也非常“严肃”。但我宁可把它当作一出有关天灾的喜剧:不过是一群人愚蠢地试图“主导”一个复杂程度超过他们控制能力的情况——一个兼具永恒与琐碎性质的状况。总而言之,有大象那么大的东西夹杂在里头,情况可能更糟。
我希望,波尔太太,我已说清楚了我的用意。不管怎样,都谢谢你抽时间写信给我,因为我乐于聆听我的听众——即使是恶评。
“狗屎脑袋”敬上
盖普做事最容易过头,他把每件事都搞得巴洛克式的繁复,他相信夸大;他的小说也走极端。盖普永远不会忘记他在波尔太太身上的失败;她常令他忧虑,她对他及时回复的信写来的回信,令他更加不悦。
亲爱的盖普先生:
没想到你会不辞麻烦给我回信。你一定有毛病。从你的信中看得出,你很有自信,我想那是好事。但你的话在我看来,大部分都是垃圾跟胡说八道,我不希望你再给我解释任何事,因为那很无聊,而且侮辱我的智力。
艾琳·波尔敬上
盖普是个自相矛盾的人,就如同他的信念一样。他对别人很慷慨,但他很没有耐心。该给每个人多少时间和耐性,他自有一套标准。
他可能会不厌其烦地体贴,直到他决定体贴够了为止,然后他就转个身,换一副截然相反的面目,大声吆喝起来。
()好看的txt电子书
亲爱的艾琳:(盖普写给波尔太太)
你该停止看书,或者你该看得更用心点。
亲爱的狗屎脑袋:(艾琳·波尔回信)
我先生说,要是你再写信给我,他就把你脑子打烂。
菲兹·波尔太太敬上
亲爱的菲兹与艾琳:(盖普立刻反击)
滚,你们去死吧!
于是他的幽默感没有了,他也撤回了对这世界的同情。
在《葛利尔帕泽寄宿舍》中,盖普多少在喜剧与悲悯之间制造了共鸣。这则短篇小说并未贬抑其中的角色——不论是刻意营造来讨喜的可爱,或任何其他打着树立观点旗号而做的夸大。它刻画人物不滥情,描写他们的哀伤也不显低俗。
但现在盖普似乎丧失了说故事的能力。他的第一本长篇小说《拖延》——在他看来——坏在被他并未真正参与的法西斯历史装腔作势的重量拖累。他的第二本长篇小说坏在想象力不够——换言之,他觉得想象得不够远,未能超越他自己相当平凡的经验。《戴绿帽的第二阵风》没花他太多力气,似乎就是一场“真实”而相当平凡的经验。
事实上,盖普自觉被幸运的人生(海伦和他们的两个孩子)填得太满。他自觉写作能力面临一种相当罕见的瓶颈:以自己为主的写作。但当他望向身外非常远的地方,就只看到装腔作势。
他的想象力让他失望——“感官犹如微弱星火”。每当有人问起他的写作进展,他想出一个简短、残酷、模仿可怜的艾丽斯·傅莱契的答案。
“我停己了。”
9永远的丈夫(1)
盖普家电话簿的黄页上,婚姻栏(Marriage)的位置距木材栏(Lumber)很近。木材接下来是机械工厂、邮购、潜孔工程、枫糖、航海仪器,接着就是婚姻与家庭咨询。盖普发现婚姻栏时正在找木材;他在木作方面有几个无关紧要的疑问,但婚姻吸引了他的目光,勾起了几个更有趣、更值得深思的疑问。好比,盖普从来没想到,婚姻顾问的数量竟然比木材厂还多。但他想道,这一定跟你住的地方有关。换作乡下地区,岂不是木材跟大众生活的关系更密切吗?
盖普结婚已将近十一年了;这期间,他几乎用不到木材,更不需要婚姻顾问。盖普之所以对黄页上一长串名字感兴趣,与私人问题无关;而是因为他花很多时间试着想象,有工作是什么感觉。
有基督教咨询中心和小区牧师咨询服务;盖普想象有群热忱的牧师,总把他们肥厚干燥的手掌扣在一起。他们说出来的句子圆滑湿润像肥皂泡,好比“我们不敢指望教会对您这样的私人问题提供多大的协助。每个人必须找寻自己的出路,他们必须保持个别性;但根据我们的经验,很多人都把他们各自的个别性寄托在教会上”。
摸不清头脑的夫妇坐在那儿,希望谈论同时达到性高潮的问题——那是神话,或真有其事?
盖普注意到,有不少神职人员投入咨询;有路德会的社会工作部、有一位德韦恩·孔兹牧师(有“证书”的)、一个叫露意丝·雷格的“全灵牧师”号称是美国婚姻与家庭咨询局的成员(该局也颁发她“证书”)。盖普拿了支铅笔,在所有跟宗教团体有关的婚姻顾问旁边打了圈号。盖普相信他们会提供相对比较乐观的咨询。
受过较“科学”训练的顾问会采用什么角度,盖普比较没把握;他对这种训练的内容也一无所知。有个持“临床心理学证书”的,还有个只在名字后面列着“临床,M.A.”,盖普知道这几个字可以代表任何东西,甚至可能毫无意义。这人可能是社会系的研究生,或念过商学院。有一个人自称“理学士”,但他可能读植物系。有人自称“哲学博士”——主修婚姻吗?有人自称“达克脱”(Doctor),但看不出是医院的大夫或一般所谓的博士。谈婚姻咨询,谁比较强?有人擅长团体治疗;还有人野心不大,只做“心理评估”。
盖普挑了两个他感兴趣的。一个是达克脱罗斯洛克,——“自我评价工作室;接受金融卡”。
另一个是M.聂夫——“限预约”,名字后面只有一个电话号码。资历见不得人,或者极端傲慢?可能两者皆是。盖普想道,如果我需要顾问,我会先试聂夫。达克脱罗斯洛克和他的金融卡、自我评价工作室,一望即知是骗子。但聂夫是很严肃的;他有理想,盖普看得出。
翻完婚姻栏,盖普又在黄页上流连了一会儿。他翻到土木业、孕妇装、垫毯翻修(只列了一家,而且是外县市史迪林的电话号码;正巧是盖普的岳父恩尼·霍姆,他替人整修摔跤垫,当作嗜好,也赚点蝇头小利。但盖普脑子里压根儿没有他的老教练;他顺着垫毯翻修,接着看到床垫栏,没认出恩尼)。再来是丧葬陵墓、切肉工具——“见锯公司”。够了。这世界太复杂。盖普又翻回到婚姻栏。
这时丹肯回来了。盖普的大儿子已经十岁,个子长得很高,遗传了海伦纤细精致的轮廓和黄褐色的杏眼。他跟海伦一样肤色略深,承袭了母亲的好皮肤。他从盖普继承的则是容易紧张、顽固和自哀自怜的习性。
“爹?”他道,“我到劳夫家过夜好吗,很重要的。”
“什么?”盖普道,“不行。什么时候?”
“你又在读电话簿了?”丹肯问父亲。他知道,每当父亲把电话簿当小说读,就像睡午觉一样得叫醒他。他常阅读电话簿,主要是找名字。盖普小说中的角色姓名都是电话簿里找来的;每当他文思停滞,就会翻电话簿找更多的名字;他会再三修改角色的名字。盖普旅行时,进到汽车旅馆房间里第一件事就是找电话簿;他通常都把电话簿偷回家。
9永远的丈夫(2)
()好看的txt电子书
“爹?”丹肯说;他假定父亲还停留在翻阅电话簿的怔忡当中,分享他笔下虚构人物的虚构人生。事实上,盖普也早忘了他今天查阅电话簿是基于与小说无关的动机;他忘了木材,只想着聂夫好大斗胆,以及婚姻顾问是份什么样的工作。“爹!”丹肯说,“要是我晚餐前不打电话给劳夫,他妈妈就不答应我去他们家了。”
“劳夫?”盖普道,“劳夫没来啊!”丹肯嘟起嘴巴,翻着眼珠子;这是海伦的习惯,丹肯也有跟她一样好看的脖子。
“劳夫在他自己家。”丹肯道,“我在我家,我想去他家过夜——跟劳夫一起睡。”
“明天要上学,不行。”盖普道。
“今天星期五,”丹肯道,“耶稣啊!”
“不要这样讲话,丹肯,”盖普道,“等你妈下班回来,你自己问她。”他在拖延时间,他知道;盖普不信任劳夫——更糟的是,丹肯去劳夫家过夜总让他提心吊胆,虽然丹肯已不是第一次去。劳夫年纪比较大,盖普对他满腹猜疑;还有,盖普不喜欢劳夫的母亲——她晚上出门,听任两个男孩独处(丹肯说的)。海伦有次说劳夫的母亲“不自检点”,盖普一直对这字眼很着迷(这种外型的女人对他别具一种吸引力)。劳夫的父亲不住家里,所以劳夫母亲“不自检点”的外貌,因为独居的关系而更诱人了。
“我不能等妈回家,”丹肯道,“劳夫妈妈说她晚餐前就得知道,否则我就不能过去。”晚餐是盖普的职责,想到晚餐他就分了心;他不知道现在几点了,丹肯放学回家好像没个固定时间似的。
“劳夫常过来住夜,”丹肯道,“我也要去他家。”做什么呢?盖普很想知道。喝酒,抽大麻,折磨宠物,偷窥劳夫太太邋遢地Zuo爱?但盖普知道丹肯已经十岁了,很理智——也很谨慎。这两个男孩也许只是喜欢在同一栋房子里独处,不要盖普高高在上对他们微笑,询问他们需不需要这个那个的。
“何不打电话问问劳夫太太,看她是否可以等到你妈回家,再告诉她你能不能过去?”盖普问。
“耶稣,‘劳夫太太’!”丹肯呻吟道,“妈只会说:‘我没问题,去问你爹。’她每次都这么说。”
聪明的小子,盖普想道。他被困住了,差点就脱口而出,他其实是害怕劳夫太太的香烟会在睡梦中燃着她的头发,在夜里把孩子们烧死。盖普再没什么好说的。“好吧,去吧!”他闷闷不乐地说。他甚至不知道劳夫的妈妈抽不抽烟。他就是第一眼就不喜欢她,而且他猜疑劳夫——除了那孩子比丹肯大,在他想象中因此就可能以极可怕的方式带坏丹肯之外,没别的理由。
盖普对他妻子和儿子喜欢的人大多都不信任;他有种迫切的需求,不让他想象中的“所有其他人”,接近世间寥寥无几的他心爱的人。可怜的劳夫太太并非遭他偏颇幻想诬陷的第一个人。盖普想道,我该多出去走走。他想,要是我有工作——自从不写作以来,他天天动这种念头,天天在那儿反复沉吟。
世上几乎没有一份工作能吸引盖普,当然也没有一份他合格;他心知肚明,他根本谈不上工作资格。他可以写;当他写作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写得很不错。但他想出外工作的一大原因是他想多了解别人;他要克服自己对他们的不信任。有份工作,起码可以逼他跟人接触——平日若非迫不得已跟别人打交道,他宁可待在家里。
说起来,原先也是为了写作,他才不考虑出外找工作的。但现在为了写作,他又觉得需要工作。我已经把可以想象的人都用光了,他想道,这也许是因为他喜欢的人本来不多;何况他也太多年没写到自己喜欢的东西了。
“我走啰!”丹肯大声对他说,盖普回过神来。孩子背了一个鲜艳的橘色登山背包;一个黄|色的睡袋卷好捆在背包底下。两个颜色都是盖普挑的,为的是能见度佳。
“我送你去。”盖普道,但丹肯翻翻眼睛。
9永远的丈夫(3)
“妈把车开走了,爹,”他道,“而且她还没下班。”
当然,盖普傻笑。然而他见丹肯打算骑脚踏车,便朝门外喊道:“为什么不走路,丹肯?”
“为什么?”丹肯火大了说。
这样你的脊椎骨就不会被疯狂的青少年驾驶撞断,心脏病突发的醉鬼也没机会把你从马路上撞飞,盖普想道——那时你美好、温暖的胸膛就会碎裂在人行道上,你独一无二的头颅在你坠落地面时四分五裂,有些混蛋会把你像水沟里寻获的宠物一般裹在旧地毯里。然后那些住郊区的呆子就会出来猜是谁家的(“我猜是榆树街和道奇街转角那栋绿白两色的房子”)。然后就会有人开车送你回家,按门铃,对我说:“呃,抱歉。”指指沾满鲜血的后座,问:“是你家的吗?”但盖普只说:“好吧,去吧,丹肯,骑脚踏车。小心点!”
他看着丹肯过马路,踏上下一条街,转弯前先张望马路两侧(好孩子;看他小心地打手势——但也许这只是做给我看的)。这是一个安全的小城市里安全的郊区;宽敞的绿地,每家都独门独院——大部分是大学的员工,偶尔有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