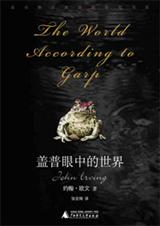盖普眼中的世界-第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私生子的愤怒与爱:盖普眼中的世界 作者:'美'约翰·欧文
译序虚构与记忆(1)
张定绮
约翰·欧文历年来发表的评论与演讲中,始终坚持,好故事是好作品的必要条件。他给自己的定位是个说故事人,他只在意如何把故事讲好,引人入胜。他笔下的人物有时性格不近情理、言行乖张,但读者不会认为这种人不可能存在;他描绘的情节经常匪夷所思,但我们不会说这种事不可能发生。
欧文认同的宗师是十九世纪小说大家狄更斯,秉承报章连载小说的流畅灵动,在社会言情的框架上掌控读者的情绪。“作家的任务就是身历其境地设想每一件事,使虚构也能如个人记忆般栩栩如生。”再加上生命的反省与圆融,欧文就确定了他文学家的地位。而且还特别值得称道的是,欧文的文字别具一种诡异的幽默感,能够把悲哀至极的场面,写得滑稽突梯,让读者笑中带泪,甚至哭笑不得,进而留下深刻的印象。
就文学形式而言,《盖普眼中的世界》前后呼应密切、四平八稳。书中至少呈现了三种不同的世界:马可·奥勒留眼中的世界、班森哈维眼中的世界,以及盖普眼中的世界。奥勒留是古罗马皇帝,也是后世景仰的哲学家,电影《神鬼战士》里那位知人善任却看不破人心险恶,被阴狠毒辣的儿子杀死篡位的皇帝就是他。他眼中看到一个悲观、消极、凡人无力改变的世界:“人生在世,一生不过一瞬,生命变幻不居,感官犹如微弱星火,肉体无非蛆虫饵食,灵魂乃不安的漩涡,命运一片黑暗,名誉难以捉摸。到头来,有形肉体似水循环复始,灵魂尽成梦幻泡影。”这段话被盖普多次引用,书中托盖普名义创作的短篇小说《葛利尔帕泽奇宿舍》,就是这种世界观的阐释。
《班森哈维眼中的世界》是另一篇书中书,也算在盖普名下,书里第一章全文照录,内容充满狂乱、暴力、愚昧、猜疑、疏离、无助。无论如何防范,悲剧总在最近的阴影里窥伺下手的机会,所有的人到头来都是命运的输家。不论如何强壮、机警、美丽、富有,都改变不了“一片黑暗”的命运;爱欲情仇“尽成梦幻泡影”,看不到妥协或救赎。它是盖普处于人生最低潮时期完成的作品。
“在盖普眼中的世界里,我们都患了末期绝症。”这是全书最后一句话,仿佛是盖棺论定。但《盖普眼中的世界》发展到最后一章《盖普身后事》,消极的色彩已淡化,大部分谈的都是盖普理想中的世界——虽然他自己无缘生活在其中(根据书中提供的数字,盖普出生于一九四三年底,死时三十三岁,他的命案大约发生于一九七七年初,《盖普眼中的世界》首次出版于一九七八年,却谈到他死后二三十年间发生在所有钟爱的人身上的事,这些事只能解释成作家盖普的临终之梦)。这一章的节奏明显地比较舒缓、祥和,对人生中无可回避的各种失望与伤害,采取比较宽容的立场;角色学会放下愤怒、自残,用比较豁达的态度迎接超乎个人意志力控制的阴错阳差和欲念拖磨,不再挣扎得遍体鳞伤。欧文在故事的大架构上,以精纯的文字,细腻真实地铺陈生命中的成长与学习,读完有股破茧重生的畅快。
ⅱ
盖普的故事非但没有在盖普死的时候就结束,甚至正值《盖普眼中的世界》出版的二十周年,欧文在一九九八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寡居的一年》中,假角色之口提出他的创作观,书中一位成名作家在新书发表会上宣称:“我的小说不讲观念——我没有观念要表达。我从角色开始写……一本小说不企图解释任何事,就只是一个故事。”他这样的强调,令人格外觉得有趣,因为《寡居的一年》在很多方面都可视为《盖普眼中的世界》的翻案。两书的主要角色同样几乎全都是作家与编辑、拈花惹草的父亲和一群苦闷的弃妇、父母为了弥补在车祸中失去的儿子而生育的女儿、年长妇人与年轻男孩通奸、根据欧洲嫖妓经验写的书、追踪与保护涉嫌谋杀的女子的警察、强暴受害人壮烈的复仇行动,甚至对“听不见的声音”、“不想出声的声音”背后隐含的危机感夸大的阐释……重复出现的元素不胜枚举,使人无法相信这仅是巧合。但这两本书却又真的是讲两个截然不同的故事。
译序虚构与记忆(2)
这么一来,欧文这番声明就有了自相矛盾的双重意义:一方面,两本书都真的只是为说故事而说故事;另一方面,却又是强调故事性比什么都重要的佐证。其实欧文在《盖普眼中的世界》第十章里,已经做了很好的示范。他给孩子讲床边故事,一个故事可以有无数个版本,只要听众提出质疑,讲故事的人就随时修改:“盖普玩这种把戏从来也不厌倦,但海伦早就觉得烦。他总是等她问:哪个部分?哪部分是真的,哪部分是编的?然后他会告诉她无关紧要;她应该告诉他,哪部分她不相信,然后他就去修改那个部分。她相信的部分都是真的;她不相信的部分都得改。如果她全部都相信,那就全都是真的。他是个棘手的说故事人。如果真相适合故事,他会毫不尴尬全盘讲出来;但如果真相妨碍故事的发展,他也会毫不犹豫把它改掉。”
对欧文(以及盖普)而言,“真实”决定于听到的人是否相信。我们生活在今天八卦、假消息充斥的世界里,天天有《罗生门》上演,早已见怪不怪。欧文高明的是:对他而言,“变动不居”不仅是人生的真相,也是一件趣味无穷的玩具和阅读乐趣的来源。
ⅲ
1慈济医院(1)
一九四二年,盖普的母亲珍妮·费尔兹,在波士顿的电影院里,因杀伤一名军人而遭逮捕。当时日本刚轰炸过珍珠港,社会大众对军人特别包容,而且忽然间,所有人都变成了军人,但珍妮仍坚持对所有男人(尤其是军人)的劣行绝不宽假。她在电影院里接连换了三次位子,但每换一次,那个军人却反而凑得更近,最后她被迫紧贴在散发阵阵霉味的墙角,正放映新闻短片的银幕,也大半被柱子遮住,这么一来,她打定主意,绝不再起身换位了。但那名军人却再一次挪过来,凑坐在她身旁。
那年珍妮二十二岁。她进大学没多久就办了退学,转入护校。她很喜欢护士工作,并以名列前茅的成绩毕业。她是个运动健将型的年轻女郎,脸蛋总是红扑扑的;头发又黑又亮。母亲总看不顺眼她走路大摇大摆,手臂甩得高高的,像个男人婆;她的臀部瘦削结实,背影也像男孩。珍妮觉得自己的Ru房太大;过于醒目的双峰,常使她觉得自己活像一个“容易到手的烂货”。
她才不是那种人。事实上,她之所以决定从大学退学,就是因为发现父母送她上韦斯利,主要目的无非是让她找个好家世的男人交往、结婚。韦斯利是她两个哥哥推荐的,他们向父母保证,韦斯利的女孩很受看重,在婚姻市场上行情看俏。珍妮觉得她的教育只不过是一种消磨时间的高级手段,好像一头母牛,一辈子就等着插人工授精管。
号称她主修的是英国文学,但在她看来,班上同学唯一想学的就是套牢男人的手腕,她弃文学改习护理,一点也不觉得可惜。她认为护理知识可以马上派上用场,而且学护理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动机(后来她在那本著名的自传里,批评护士爱对医生卖弄风骚的时候,她已经不做护士了)。
她喜欢护士制服的简单不花哨;上衣可以掩饰她高耸的胸部;舒适的鞋子颇能配合她明快的步伐。值夜班时,她还可以读点书。她一点也不怀念那些大学男生,你要是不听他们摆布,他们就闹情绪,摆哭丧脸给你看,要是听呢,他们就跩上了天,不把你放在眼里。她在医院里碰到的男人以军人和上班族居多,这些人表达他们的企图比较坦率、不做作;你要是肯给他们一点甜头,他们再看到你时,多少还有点感激的意思。但忽然之间,所有的人都从军去了——通通变成那副大学男生自以为是的德行——珍妮就再也不跟男人打交道了。
“我妈妈,”盖普写道,“是匹独行狼。”
费尔兹家族靠卖皮鞋起家,不过费尔兹太太娘家是波士顿望族,姓威克斯,嫁过来时也带了点钱。费尔兹家族经营鞋业有成,多年前就不住在鞋厂里了,他们搬到新罕布什尔州狗头港一栋铺木瓦片的滨海大宅。珍妮不值班就回家住——主要为了讨母亲欢心,也为了证明给这位家主婆看,她的谈吐与道德水平丝毫没有退步,因为母亲总说她“当护士是作践自己”。
珍妮经常在波士顿北站跟哥哥们会合,一块儿搭火车回家。他们遵守费尔兹家训,每逢搭火车从波士顿去缅因州,一定坐车厢右边,回程时一定坐左边。这是老费尔兹先生的意思,他也承认车厢这一边的风景难看无比,但他坚持,每一个费尔兹后裔,享受自由自在、丰衣足食的生活之余,必须饮水思源,面对供给他们优渥生活的丑陋财源。费尔兹鞋业的总批发仓库设于哈维希尔,当火车驶离波士顿时,它位于车厢右侧,回程时则在左侧,挂着一面高高的广告牌,画一只迎面踏来的大工作靴。硕大无比的广告牌,君临铁路调车场,无数条铁道的缩影反映在鞋厂窗户里。那只气势慑人、直逼而来的大脚下方,有这么几行字:
费尔兹体贴足下
无论在工厂
在田野!(译注:“田野”原文fields,与费尔兹为同一词。所以这句广告口号以“费尔兹”始,也以“费尔兹”终,这,大概就是它最大的特色。)
费尔兹也生产护士鞋,每次女儿回家,费尔兹先生都会送她一双护士鞋;珍妮积了总有一打。而一口咬定女儿离开韦斯利是自毁前程的费尔兹太太,每当女儿回家,也都会送一份礼物。费尔兹太太给的是一个热水袋,至少她是这么说的,珍妮也是这么相信的——她从来连包装都没拆开过。母亲总问:“亲爱的,我上次给你的热水袋还在吗?”珍妮会思索一下,估计自己多半把它忘在火车上或扔掉了,于是答道:“可能弄丢了,妈妈,不过真的不需要再给我了。”费尔兹太太就把藏着的包裹拿出来,硬要女儿带走;里头装什么东西在药房包装纸下完全看不见。费尔兹太太会说:“拜托,珍妮,多加小心。千万要用它啊!”
1慈济医院(2)
身为护士,珍妮觉得热水袋实在没多大用处;她以为这玩意儿无非是种予人心理慰藉的旧式道具,让人窝心,却也蛮可笑。但总是有几包这种东西,会被她带回波士顿慈济医院附近租赁的小房间。她把它们搁在壁柜里,里头已塞满了一盒一盒的护士鞋——也都还没有拆封。
她觉得跟父母很疏离,每每念及他们在她小时候多么悉心照顾她,然而,一到某个特定时刻,就忽然中断亲情,开始对她有种种要求,不禁百思莫解。好像人都被要求,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吸收足够的爱,然后在更长的时间、更严酷的环境里,完成某些义务。珍妮离开韦斯利,选择护士这么平庸的职业,就等于是打破循环,自绝于家人,他们也都好像不由自主地逐渐断绝了跟她的联系。对费尔兹家族而言,如果珍妮去当医生,或念完大学,设法找个医生嫁,就会恰当得多。她每次跟哥哥、母亲、父亲见面,彼此都觉得不自在。大家都有股愈来愈陌生的尴尬。
珍妮想,所谓家人,想必就是这么回事了。她想,如果自己将来有小孩,即使他们长到二十岁,也一定要像他们两岁时一样疼爱他们;他们到了二十岁,说不定还更需要你。两岁需要什么?医院里,小婴儿是最好伺候的病人。年龄愈大,需索愈多,也就愈发没人理、没人疼。
回想自己的成长过程,珍妮觉得像生活在一艘大船上,却不曾看过轮机室,更不懂里头搞什么花样。她喜欢医院的方式,一切都简化为进食:东西吃了是否有益,吃下肚会到身体哪儿去。小时候她从没见过脏碗盘;事实上,她一直以为,女佣清完桌面,就把碗盘都扔了(这是她获准进厨房之前的事)。牛奶车每天早晨送瓶装牛奶来,珍妮总以为那辆卡车也把当天要用的碗盘送来——那声音,玻璃瓶乒乒乓乓碰撞,跟女佣在紧闭的厨房门后头、清洗碗盘时弄出的声音很像。
珍妮五岁时才第一次见到父亲的浴室。她是有天早上,尾随父亲古龙水的味道而找到地头的。她发现一座蒸气腾腾的淋浴间——以一九二五年的标准而言,算是非常现代化——专用的小便器,一大排跟她母亲的梳妆用品截然不同的瓶瓶罐罐,珍妮还以为找到的是一个偷偷在她们家居住,多年未被发觉的神秘男人的巢|穴。事实也确实是如此。
医院里,每件东西的去向珍妮都一清二楚——她也逐渐明了每样东西毫不稀奇的来源。但在她自小长大的狗头港,家里每个人都有专用的浴室、私人的房间,每个人专属的房门背后,都挂着专属的镜子。医院里不重视个人隐私;没有秘密这回事;想照镜子,就得跟护士要。
珍妮小时候获准独个儿去探索的神秘所在,就只有地窖和每星期一例行装满蛤蜊的大陶缸。珍妮的母亲会在周一晚上在蛤蜊上洒玉米粉,每天早晨再拿用管子引进地下室来的新鲜海水冲洗。到了周末,蛤蜊都养肥了,沙也吐净了,每只都肥到原来的壳装不下,伸出淫猥的肉柱,懒洋洋地浮在盐水上。星期五晚上,珍妮帮厨子拣蛤蜊;碰触肉柱不会缩回去的,就是已经死了。
珍妮要来一本介绍蛤蜊的书。她阅读各种有关蛤蜊的知识:它们如何进食、如何生殖、如何成长。这是第一桩她完全了解的事——它们的生活、性、死亡。狗头港的人类可没那么容易理解。珍妮在医院里弥补了失去的时间;她发现,人类其实不比蛤蜊更神秘,也并不会更有吸引力。
“我的妈妈,”盖普写道,“对很多微妙的差别都麻木不仁。”
蛤蜊与人之间至少有一个显著的差别,她应该能分辨,那就是多半的人多少都有点幽默感。问题是,珍妮没什